漫长的古犹太人流散历程
“流散”Diaspora,原为希腊语,dia意为“穿越、经过”,sperien意为“撒播种子”。这个词语最初用于特殊历史情境——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的历史。约公元前6世纪,巴勒斯坦北方的巴比伦帝国征服了当时的犹大国,摧毁了第一圣殿,强迫犹太人离开圣城耶路撒冷,把一部分人囚禁在巴比伦城做奴隶,流亡数十年之久。之后波斯王居鲁士(King Cyrus,585 B.C-529B.C)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他同意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返乡,但有一部分并没有回归故土,而是留在散居地成为 “外来的”、“不归属”的犹太群落。两次犹太战争(公元70年、公元135年)后,大批犹太人作为奴隶被带到罗马,犹太人主体离开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从此,犹太人就开始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向全世界各地流散的漫长过程,这就是“犹太人大流散”(Diaspora)。后被扩大用来形容类似处境的其他犹太人,就是离开巴勒斯坦土地之外,但是仍然保留犹太文化的移民,或海外犹太人聚居之地。随着后殖民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的关注,流散文化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引申出了广义的族群大移居、离乡背井聚居(但仍保有传统文化)的族群等含义。
“Exile”和“Diaspora”两个词语,都有流放、流亡及离开本国、离乡背井之义。区别在于“exile”有被动意味而“diaspora”究其本意含有积极主动之态。原希腊语中也有“散播种子”之义,可见犹太人把这种流散解释为一种主动的文化活动,借此将犹太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圣经的一道神谕,更是将犹太人的流散打上了宗教的印记。耶和华对犹太人的先祖亚伯兰(后按上帝旨意更名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世记》12:1-3)上帝与亚伯兰定约,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来到“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随后又离开迦南,出埃及,四处迁徙。圣经的描述使犹太人的流散成为了一种使命,也是一种宿命。1948年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大量犹太人回归故土,但是曾经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后裔没有尽数回到他们向往已久的国家。犹太人近两千年无土无国,饱受折辱、驱逐却不放弃其民族身份与信仰,不可不谓之奇迹。
刻意与客居地文化保持距离的犹太民族
犹太人自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赶出家园后,就一直居无定所,漂泊他乡。由于世人的偏见、敌意和种族迫害,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屡遭迫害和杀戮。在世界性的反犹浪潮中,即便是背井离乡,犹太人也几乎未得到片刻的安宁。反犹历史就是一部屈辱、恐怖、残忍的血腥史。最为我们熟知的二战期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人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种诉诸暴力的文化排斥对于流散族群来说并不少见。而有着坚定信仰的犹太民族在流散生活中极力保持其文化独特性而刻意与客居地文化保持距离。1516年,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铸造枪炮的工厂内,使之与外界隔绝。这种经验后来被各国仿效,在城市设立犹太人专住的隔离区—— “隔都”。犹太人情愿住进隔都区,这样可免于与外族混杂,也便于保持犹太人独有的风俗习惯和保障生活的安全。著名布拉格文学家,犹太人卡夫卡,终其一生都未离开隔都。最初的隔都可以说是文化冲突的缓冲地带,是流散中的犹太人因无法适应流动、杂异的边缘生活而为自己建立的有故乡原型的避难所。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磨合,犹太文化与客居地文化不断接触、融合,以至于相互采借、纳取。最终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走出隔都,有形的圈地逐渐消失,无形的隔膜却不可避免,犹太人想要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属性,总是或多或少会与异质文化有所碰撞,即使已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承认的犹太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主人公的好友,也是他的传记作家齐克说:“雅典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更高的生存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雅典,同时对耶路撒冷充满敬意。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说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拉维尔斯坦》, 索尔·贝娄著,译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P167)在这里,雅典代表整个西方即客居地,而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朝圣之所,无论犹太人散居在世界何处,都难以忘怀其永远的精神故土。在小说的结尾,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族之根的回归——拉维尔斯坦最终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抛弃你的血统,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身份。”“犹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深感兴趣——感兴趣于他们的正义原则。”(P172)
多元文化身份的犹太人
犹太人,又称犹大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这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名称并不能涵盖和诠释如今犹太人的身份。现代我们通常认为犹太人包括以下三类人: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人(无论其是否信仰犹太教);具有古代犹太血统的人(有时候包括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母系血统的人);虽不具备任何犹太血统但正式皈依犹太教的人。但是这三点都不足以对犹太人的身份进行严格的界定,甚至在很多时候看起来矛盾重重。首先犹太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与外族通婚,已经不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因此从血统和家庭的角度来判断已经不够严密。其次,没有信仰或改宗信其他教派的犹太人也自古有之,更何况犹太教从来就派系林立,各行其法。因此想要给犹太人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是不可行的,从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犹太人文化身份的特点。每个犹太人身上至少都有两种文化身份,即犹太人身份和居住地文化熏染下的客民身份。在各种身份中,仍将犹太身份放在首位,一方面是他们对民族性重视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迁居地的民族同化,靠的是他们对犹太经典的信仰以及在信仰指导下对传统的坚持。犹太人只认同上帝的世界,将现实世界视为不真实、充满苦难的异己世界;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排犹情绪使他们并不可能真正融入主流文化,而始终保留着一种疏离感。同时犹太人自身有悖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历史上流散的生活方式而明显地表现出疏离于主流文化,难以融入其中的情绪。
犹太人在流散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历了深重苦难,受到歧视、驱逐与屠杀,被隔绝于世界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之外。但是他们仍坚忍顽强地存活下来,没有因外界的排斥或客居身份而被完全同化。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经验的犹太人作为异质文化的负载者和实践者,其身份意识中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因素,也有他民族的文化因素,表现出复杂的文化情感和独特的文化立场。历史上犹太人改宗皈依异教,或放弃语言与民族身份的不在少数,但即使犹太人在流散中表现出了身份焦虑和困惑,最终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非常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特征为己所用,同时又能保证文化母体中关键的要素不变。这就使他们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既能保持青春活力,又反过来以本身的魅力吸引和影响着其他族群。正是犹太文化超强的生命力和活力,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也唤起了其他民族的危机感,这种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的结合方式刺激着犹太文化历久弥新。而犹太文化一直维持的状态,被刘洪一教授总结为“散存结构”。(《犹太文化要义》,刘洪一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71—89)
多元文化的冲突融合
流散是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散居族群在寄居地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抉择、身份困惑与认同等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给个人和族群带来的主要是身份的困惑。失去身份,个体生存会因此失去内在根基,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因此一种潜在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侵扰着新一代移民。空间距离的改变使得文化个体与地域、种族乃至肤色的传统联系,都会出现一定的动摇。身份认同受到挑战,文化身份的确认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过程中特定个体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异域生活的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这种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存状况。在此情境下,人们对自我意识的反思是必然的。“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和多重的。” (《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王宁著,《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所谓身份(status),一般指的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和着眼点,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文化身份在一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形成,其构成的客观因素是复杂的。然而一旦形成,就会在无形中对这个族群和个体造成深远的影响。文化身份的定位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则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定文化身份的带头下仍然含有人类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如性别冲突和认同矛盾等。身份认同成为流散群落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创造了国际性文化新格局,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文化交流从同质间的内部交往到全球化语境下异质文化间的互动,这种“跨文化”的前提为文化视野的开拓提供了条件。它的特点是“不是对差异的否定,而是在共享人类属性的背景中寻求长远的一种坚持:有效地生活在本土和全球中,并分享一种‘全球地方化’(globalized)的文化。这将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流行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大众文化》,约翰·斯道雷著,选自保罗·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P295)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身份、民族等传统受到新观念的巨大冲击,支离然后重构。科技与经济的发达使人类在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离开“本土”、“本国”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新的社交和群聚方式逐渐使人们改变过去狭隘的实践模式与思维方式。流散是对传统意义上民族与文化的割裂,也是现代意义上民族认同与文化交往的一种重构,犹太人的流散及其身份认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旅游文化系,讲师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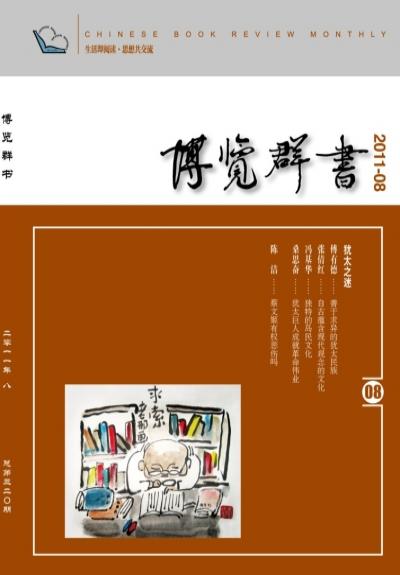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