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关于盛世中华的记忆是在1840年戛然而止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胡绳先生将近代中国的受辱史描述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但对于这一重要历史转折的“他者叙述”即来自西方亲历者的有关叙事,我们接触甚少。
在这段屈辱史里,圆明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国人最难以承受之痛。2010年是这场劫难之后的第150个年头,中西书局将亲历战争的西方人的回忆进行集中,编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法军参谋部中校、地形测绘部总指挥杜潘(他在撰写该书时化名为“瓦兰·保罗”)所撰写的《远征中国》(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即是其中的一本。
在《远征中国》之前
1860年,是“清朝立国以来内外交困危机空前的一年”,而杜潘的《远征中国》也正是记述这一年的故事。
1860年夏,太平军再度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尽得以苏州为中心的苏浙富庶之地,使得这一年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此外,西南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亦如火如荼。可以说,这时的大清国遍布造反者的身影。
外患与内忧同样严重: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法、美三国借“修约”问题向清廷发难之时应对失当,直接导致英法于1857年借“亚罗号”与“马神甫”两个事件向中国开战。
战端一开,清廷速败,《天津条约》作为城下之盟而诞生。但一年之后,清廷与英法又因“换约”问题相互龃龉,清朝官员的虚与委蛇被英法认为是对《天津条约》的否定。于是,英法自恃船坚炮利,以野蛮行径硬闯大沽口,未料遭遇清军僧格林沁顽强抵御,损失惨重。清军遂取得“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三联书店2006年版,P200)
英法军队惨败的消息迅速传至欧洲,英法皆朝野大哗。于是,在1860年的夏天,一支由“英法两国110艘军舰、17700名陆战部队”组成的庞大军队进抵北直隶湾,杜潘所谓的“远征中国”即由此真正开始。
从大沽口到圆明园的“远征”
1860年7月11日,杜潘第一次参与战事,他指挥了对大沽口沿岸的侦察。(P44)此时,塘沽守将僧格林沁意识到了威胁的迫近,他“饬令南岸马队官兵,轮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以杜夷人登岸,并饬大沽各营暨北塘侦探官兵时刻严防”。此时的咸丰皇帝不愿开战,他同时严令僧格林沁“不得先启衅端”。
8月1日,联军在北塘登岸,未遇任何抵抗。(P59)联军随后占领北塘村,进抵白河炮台,仅遭受过一次清军马队的袭扰。此时,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上奏“夷人分股攻扑新河,马队不能支持,退守唐儿沽”,这时咸丰皇帝才意识到战事的不可避免,他随即在一天后下令僧格林沁“严守唐儿沽击退英法入侵并设法转圜”。(《第二次鸦片战争(四)》,P461-464)
又一天后,唐儿沽炮台(杜潘记为白河炮台)失守。据杜潘所记此役联军赢得甚为轻松,“中国军队的反击是绵软无力的”(P72),经杜潘统计,联军付出的代价不过是“法军1人死亡,8人受伤,英军的伤亡也差不多如此”。(P23)但僧格林沁当日向朝廷的奏报却称“清军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第二次鸦片战争(四)》,P466)
8月21日,英法联军对大沽炮台侧翼的石头缝炮台发动进攻。此为战端开启后最为激烈的一战。清军极为奋勇,法国人德巴古赞称“自从我们和他们打仗后,中国军队肯定还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和顽强地抵抗过”,连杜潘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也是很顽强的”。(P87)无奈清军火药库被击中爆炸,指挥作战的直隶提督乐善当场阵亡,最终溃败。在杜潘战后的统计中,联军被认为遭受了“相当可观”的损失,法军“40人被杀,160人丧失战斗力”。(P95)石头缝炮台的失守使僧格林沁再无心坚守大沽口。于是,“经营三载,耗帑数十万,安炮数百位的大沽炮台”轻易落入了英法联军之手。(P92)
8月23日,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咸丰皇帝派出钦差大臣桂良与英法交涉。在军事威迫之下,桂良不得不答应了英法全部要求。当桂良与英法特使达成初步一致的时候,战争似乎结束了。但意外很快出现。英法使团随后不顾桂良劝阻,径自带兵进京。咸丰皇帝遂饬令桂良“不必再与议和”。这一行为激怒了联军,杜潘认为桂良仅仅是为争取时间让清僧格林沁布防,对此,杜潘的表述是“以为已经结束或者行将结束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了”。(P109)
在联军进至距通州不远的河西务村时,怡亲王载垣接替失信于英法的桂良,作为新的全权大臣重新求和。英使巴夏礼提出亲见皇帝递交国书的要求,造成了谈判的又一次破裂。随后,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使团截拿、囚禁,联军遂认为自身陷于清政府的圈套之中。(P118)杜潘也在《远征中国》里以“阴谋论”概述中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外交行为,在他看来,英法特使“轻易地给予了清廷使者过多的信任,这种仓促大意的信任在之后的那次经历中,给联军中的很多人造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P109)
9月21日,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与联军决战于通州以南的八里桥。虽然在这场战斗中,僧格林沁部队表现得极为英勇,特别是几个挥舞旗帜指挥步兵的清军统领,给杜潘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军事技术上的不对等让清军彻底溃败,与此相对的是“法军死3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P132)
僧格林沁兵败的消息震动了到北京城。咸丰皇帝委任恭亲王奕訢收拾局面,自己则逃向热河。北逃路上的咸丰皇帝很是凄惨,据《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銮舆不备,扈从无多,是日,上仅咽鸡子二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数行下。”与清廷仓皇出逃相对应的,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的幸福。在杜潘的笔下,这幅场景被详细地展现了出来:
9日是计划中出发进京的一天。法军的营地里出现了一幅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奇特、最热闹的画面:帐篷内外都堆满了各式各样、世上最珍奇的物品,这些在一天内所获得的财宝让士兵们陷入了无尽的幻想之中;一通鼓声驱散了他们的幻想,只见士兵们一个个如天真的孩子一般,显得缺乏远见,并有破坏者的天性,他们丝毫没想到行军的劳累,就在背包里塞满了丝绒绸缎,好像只要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的亲友。而那些带不走的东西让他们感到恼怒,于是那些东西都被打碎了、撕烂了或者弄脏了。到处都是豪华的家具、丝绸以及用金丝线绣制的皇家裙袍,还有就是满脸要和这些宝物说再见的可怜表情。至于银元,由于数量极多,我们考虑到它们巨大的重量只好基本上视而不见。因此,不止一名士兵用价值大约480法郎的一块银锭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P151)
几天后,英军焚毁圆明园,而杜潘《远征中国》的旅程也在圆明园的浓烟中落下了帷幕。
如果从多个角度审视这段战争史,我们不难发现,清军事实上并不能对英法联军构成军事上的威胁,但僧格林沁等前方将领却为咸丰皇帝杜撰出清军英勇作战、不断予敌重创的假象。严重的信息不对等和咸丰皇帝自身的性格,造成了清政府的决策总是处在反复之中,每每在最后时刻放弃和议。而清军螳臂当车的抵抗不仅加深了国家的灾难,也使得英法可以不断增加条约条款,等到咸丰帝真正明白没有战胜之机时,和平已经只能借助“无条件投降”了。
人质危机与圆明园之殇
在现存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证明英法联军曾以占领或毁坏圆明园作为战略目的。而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混乱无序的抢劫更可以说明这里本不属于他们的目标——否则就该有一个明晰的抢劫计划和行动了。那么,点燃圆明园的火种究竟是什么呢?
杜潘提出了两层烧毁圆明园的理由:一是“报复说”,即因为巴夏礼使团被关押在此,受尽“嘲笑和凌辱”,因而“应该通过摧毁圆明园来实现复仇”;二是“胁迫说”,即英国人通过烧毁圆明园来逼迫清廷尽快签署条约,而不是一直“拖到严寒的冬季”。(P164)
“报复说”也见于其他当事者的叙述中:翻译官德里松在1860年10月21日致其母亲的信函中写道:“为了对我们可怜的伙伴的被谋害作报复,我们焚烧了皇帝在圆明园的宫殿使之夷为平地。”在西方历史学者的眼里,逮捕巴夏礼使团的行为“抛开道德不谈,仅就这一计划而言,是一个集愚蠢、残忍于一身的糟糕的策略”。(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P293)“报复说”也是中国历史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通过转引美国国家档案文献和相关著作,证明额尔金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非法拘禁巴夏礼及虐待战俘的行径”,郭廷以也认同这种观点,即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是“作为对清朝皇帝的直接惩罚”。
逮捕巴夏礼使团是由恒祺和僧格林沁具体执行的。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基于两个误判:一是咸丰帝对巴夏礼使团职责的误判。作为先遣使团,巴夏礼使团最主要的目的是与钦差大臣载垣议定和约。杜潘详细记述了这个使团的构成,包括特使、军事参谋、军需官、财务官、翻译官、随军神甫、记者以及士兵等,并且提及这个使团是要为两支军队“准备补给”。(P116)如果这个关于构成的记载基本确凿的话,那它的确更像一支兼办外交和后勤事务的队伍。咸丰皇帝却始终认为这是一个以军事侦察为目的的特务使团。他断定使团“名为议和,实则豫伏以兵要盟地步”并将此谕告载垣,同时也将此意谕告僧格林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P67-68)载垣和僧格林沁即依此谕旨实施了他们的抓人行动。
第二是对巴夏礼身份的误判。清廷官员误以为巴夏礼为洋人首领,但事实上,巴夏礼只是使团的中文秘书,仅仅因其通晓中国之事,额尔金又不愿与清廷官员过多纠缠,所以才屡次把巴夏礼推上前台罢了。
巴夏礼被扣的当天,光禄寺卿胜保即致函建议“令被擒英人作书止英军前进”,但巴夏礼面对载垣时“惟不肯认错,言词桀骜,实属可恶”。两天之后,巴夏礼被押解至刑部,随即就有大臣请杀巴夏礼,并且得到了咸丰帝“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的朱批。但一天之后,也就是八里桥决战当日,僧格林沁向军机处提出了“借巴夏礼等为转圜之计”,想来这与他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有关。在收到僧格林沁的请求后,军机处立即上奏咸丰帝,咸丰帝也随即改变了前日的想法,表示同意。(同上书,P84-110)此后,留下巴夏礼借以转圜的呼声成为主流。
在巴夏礼被扣12天之后,迫于英法将要攻打北京城的巨大威胁,咸丰下旨“先将巴夏礼放还借此转圜相机议和”。但此时的奕訢并没有释放巴夏礼,并自欺欺人地照会巴夏礼,“使知羁留该酋,原为商办合约起见”。(同上书,P161)直到10月8日,也就是在被扣留20天后,巴夏礼才最终被释放,在一起被俘的39人中,只有18个人活了下来。(王开玺:《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P65)回到己方阵营后,巴夏礼等人极尽渲染之能事,为众人描述出一个清廷用酷刑囚禁他们的故事。在今天学者的认真考证中,巴夏礼等人的受虐之说无法成立,但人质回来时因被绳索捆绑而造成的伤痕,却成为了蛊惑人心最好的工具。杜潘即看到人质们“手腕和腿上都有一圈圈带血的伤口,这说明中国人对他们施加了酷刑”。(P162)
由此看来,咸丰皇帝的误判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而奕訢毫无作用的延宕又进一步加深了这场危机。我们当然不可否认英法联军的贪欲、残暴以及战争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是圆明园之殇的元凶,但清廷对于巴夏礼使团极失当的处置,也应为圆明园的被毁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些与联军为伍的中国人
1860年从大沽口到北京的战事可以被视作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因为从整个中国的版图来看,北方是英法联军对清廷作战,南方清廷却与英法联军联合,以“借师助剿”之名共同对付太平军。而即使在北方这场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也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了清廷一边。甚至可以说,英法联军的侵华作战在许多方面借助了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远征中国》中多次出现中国人与英法联军进行交易的记载。在抵达芝罘之后,中国人“在利益的诱惑下”与英法联军进行粮食交易,“一个充盈着各式天然食品的市场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法国人)的营房旁边”。(P32)6月3日,满载法军军用物资的“快帆皇后”号在澳门附近海面失火,法军军服大量被毁,杜潘提到“多亏了中国裁缝的仿造才能,衣物的匮乏很快得到了缓解”。(P34)在八里桥战役的第二天,法军进入通州城,杜潘记载法军发现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到许多的运输车辆……用来拉车的马匹和骡子同样也不缺少,数量非常多”(P136),为法军提供车辆和高质量牲口的商人,同样只可能来自中国。
同时,作为侦察部队负责人的杜潘曾经两次借助了中国向导的力量。第一次,他们帮助确认了“直门山村是不设防的”(P42);第二次,中国向导则在行走中“突然停下脚步,然后跪倒在我们(法军)面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说这座炮台周围埋有地雷”。(P62)
在英军炮兵身后,还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P31),除却运输,他们也参与作战,并且表现英勇。在石头缝炮台之战中,这些中国苦力被命令跳进炮台下的壕沟中搭出人力浮桥,杜潘记载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中国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P84)
在法军洗劫圆明园之后,一些中国人因为饥饿而来到我们(法军)士兵们身边,像仆人一样跟着他们。为了获得几片面包,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把自己的长发辫系在士兵们的背包的纽扣或者脊带上,他们背着很重的行李却毫无怨言,一直紧跟着自己老板的步子。(P151)
虽然杜潘出于美化侵略战争的目的,在上面的描述中加入了许多杜撰的成分,但在民族国家认同尚未形成的近代中国,普通民众会认为战争只存在于朝廷与英法军队之间,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么出现这样的行为并不在情理之外。更何况,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就算不得是同仇敌忾的了。
不可否认,杜潘的《远征中国》是一部带着强盗传奇色彩的作品,对于侵略战争的歌颂使其在道德意义上不具有太多的价值。而杜潘所认为的法军这次“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冒险经历之一”的战争,早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侵略之一被载入史册。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远征中国》为我们展现的历史图景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多的角度去审视那场灾难,特别从当时中国军政当局在战争和外交中的种种表现,以及在战争中与联军为伍的人,对我们全面审视那一段历史,并探究这场灾难之成因的复杂性,是可以有很多启示的。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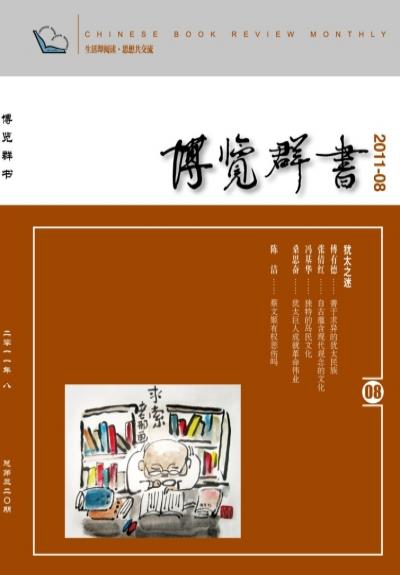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