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与禅让,是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记载中的重要主题。就事件的发生来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以及战国时期燕国君主哙禅位于臣下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的故事。
有关禅让的评论,自战国时代起即纷纭杂呈,墨子虽未明确提出禅让,但其尚贤学说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与禅让十分接近;孟子一方面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但另外一方面又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肯定天在世袭或禅让事件中的主导作用,他甚至还严厉抨击了燕王哙的禅让;庄子则置身事外,说古代的贤哲即便将王位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是不屑一顾的;法家韩非子则明确表明根本没有禅让,断然否定了禅让的存在。传统文献中有关禅让的记述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而出土文献中又有令人称奇的内容。1998年刊布的《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2000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篇皆围绕禅让而展开论述,《唐虞之道》篇已然形成有关禅让的完整理论阐述,而《容成氏》篇则宣称凡古代有德行的帝王皆行禅让,无一例外。
毫无疑问,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在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围绕禅让而起的学术研究不计其数,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禅让起于墨家考》,文章指出禅让学说与倡导尚贤的墨家思想最相契合,而与固持“亲亲尊尊”理论的儒家理论似有不小的距离。此说一出,赞同者有之,反驳者亦有之,而有关禅让的研究从此源源不断。总体而论,中国学者对于禅让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展开:一,禅让学说的学派归属及其思想来源;二,禅让学说所反映的时代状况及其思想状况。
应当说,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多专注于禅让本身,而对禅让的对立面世袭关注较少,也尚未考虑到将之放置于一个结构中,在结构中观察禅让、世袭这一矛盾对立体所体现出的意义。美国学者艾兰教授著《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是一本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考察世袭、禅让的著述。由于这样一种理论的运用,使得作者具有不同以往的研究视角,由是揭示出禅让与世袭这一矛盾体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的观念方面的意义。因此,该书不独是历史史实的考察,更是观念史研究方面的典范。
结构主义非常注重整体的观念、对立的观念以及转换的观念。在考察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时,艾兰教授发现在众多叙述王朝更替的理论抑或传说中,存在着一种结构,而世袭与禅让构成了这一结构中的主要矛盾对立体。无论有关王朝更替的论述多么简略,无论其叙述方法如何转换,世袭与禅让却总是隐含其中。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大量的“历史遗存物和事件碎片”,但是并非没有脉络可寻。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哲学论著中,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常常作为同一主题的例子并置而加以讨论:例如都是开国君王的大臣,周之太公望和商之伊尹经常被并置在一起;又如都是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和商纣也常常一起被论及。这些人物又可能与其相对的人物进行比较,如太公望与周灭商后拒绝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相对比,或者桀、纣与商汤、周文王相对比。又比如,在这个结构之内,某位作者论述了尧舜禅让,也会说到舜禹禅让;如果他说尧举舜于田亩,他也会说汤荐伊尹于庖厨。因此,在结构之内,看似纷繁复杂的种种因素其实自有其清楚的系统,自有其一以贯之之道。
那么,结构中的系统是否隐含着意义,这个意义又是什么?艾兰教授指出结构中的系统表明了论说者是借用一种经由他们组织好的故事来表达哲学思想或者进行政治论争,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表达政治见解和社会态度的方式,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变革的方法,他们借由讲故事、说道理来平衡、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变革、矛盾冲突。因此,各种各样的叙述,其重要之处在于具有社会功能。
在国内以往有关禅让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分析某学派的具体主张是什么,当然也十分注重考察学派思想与所处社会之间的关联。不过,国内的学者并不着重于分析古代学者是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故事中的因素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换言之,国内学者更关注学说本身,而国外学者注意到了讲学说、讲故事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正是论述方法的不同,故事中不同因素的剪裁才最终达致其所要得出的结论。因此,不仅仅是某一学派的具体思想十分重要,他们如何思考、如何阐述,他们一贯的思路是什么,同样特别重要。
结构主义的理论无疑有助于作者缕析古代论述者的逻辑及揭示其中的深意。例如,艾兰教授指出,在诸多有关舜的描述中,可以肯定的是舜继承尧之位,并不仅仅象征对世袭原则的违背,同时也象征着在世袭原则和美德、禅让之间的一种调和。具体来说,舜在文本中与丹朱、许由形成对照,丹朱按照世袭原则应当获得王位,但他又由于“惟漫游是好”而失去了继承资格,许由在美德方面无可比拟,但却是没有世袭意义上的正当性而拒绝接受王位的隐士。舜在文献中的描述却是介于两者之间,他是尧的女婿,虽说不具有血缘联系,但有姻亲关系;他又是明德之人,是应当获得王位的人。因此,舜背离世袭原则接受禅让,在观念上,起到了调和矛盾的作用,即调和了以许由为代表的无世袭的美德与以丹朱为代表的无美德的世袭这两个冲突原则。
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作者不但发现了论述者的逻辑,也发现了论述者或各学派观点之间存在着更为精致的关联。例如,同样是讲述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让,一种模型中的因素是“尧舜让,汤武争”(《庄子·秋水》),将禅让与武力夺权对立起来;一种模型被描述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将上述帝王皆视为违反世袭的罪魁。而在另一种模型中,并不考虑古代帝王尧舜禹、夏桀商汤、商纣武王的原有地位,以及他们所本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而是引入第三方力量,同时也是决定性力量——民众或者天,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政权——这就是孟子的主张(《孟子·万章上》)。引入“民”的因素或“天”的因素,新的统治者因此而具有政权的合法性,不必再背负接受禅让而违背世袭制(如舜和禹)或推翻前朝天子获得权力(如汤、文王)而背离世袭制的恶名。在这里,“天”或“民众”的引入同样也起到了调解矛盾的作用。
作者反复申论,有关古代王朝更替的传说,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转化——世袭与禅让、君王与大臣、大臣与隐士、摄政与叛逆,根本地,其表现为授政以德与世袭统治之间的矛盾。而这些传说如同神话一样,具有调解社会内部冲突的功用,具体来说,就是血缘氏族和公共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思想家所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结构不单单存在于思想者的逻辑中,它在现实中也有所体现。历史上那些看似荒谬的禅让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折中、调和的色彩。例如“在前王朝时期,接受了禅位的统治者故意将王位让给其他什么人,以缓解违背道德和接受原本无权拥有的王位所带来的相关恶名。在诡计无数的战国时代,与此种拒绝王位的方式相联系的礼仪的价值是显然的。说客们建议君王在完全确认大臣会拒绝的情况下让位给某个大臣以获得尧让舜那样的美名,而这个大臣也由此获得了如同许由那般的好名声”。显而易见,燕王哙将君位禅让于子之,即属于此类,燕王哙博得禅让的美名,而子之亦收获高名。又如王莽,他曾着意效仿古代帝王,其意义即在于通过古代帝王的禅让传说将其篡位合法化。掌握政权后,他成为年幼的孝平帝的摄政者。在他摄政期间,《汉书·帝王本纪》将他与伊尹、周公相提并论。在说到他迫使自己的儿子自杀时,《汉书》更将他的行为与周公摄政时处死自己的兄弟管、蔡相比附。但在他登上王位后,这些类比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汉书》不再谈论王莽,而只说舜、禹。因为此时需要的模式不再是摄政,而是非世袭的继位。因此,在王莽的例子中,既可见古代禅让观念的影响,又可见汉代史学家的论述逻辑。
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艾兰教授研究了各个学派、各个思想家论述禅让的方法及其内在逻辑,也分析了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更替中的观念交织情况以及对现实中人们的影响。这部著述称得上是一部结合细节分析与宏大论题的杰出著作。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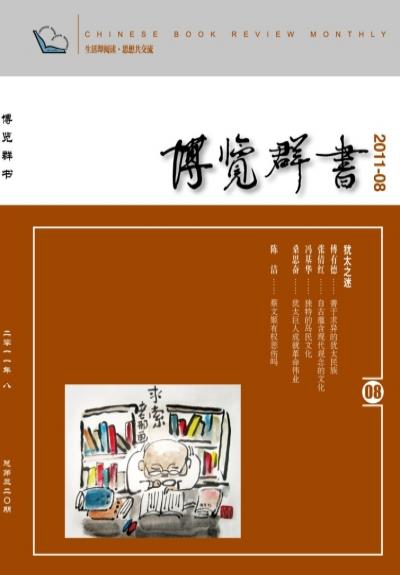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