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美国核物理科学家寒春(原名琼·辛顿,杨振宁的大学同学),定居中国62年来,把毕生的智慧创造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养牛事业。她1921年出生在美国,是美国“曼哈顿计划”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但看了1945年美国为了迫使日本法西斯投降,投在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造成平民百姓的惨状的纪录电影和照片,她觉得再也不能为杀人武器效力了。1946年,她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来到革命中的中国,献身和平事业。
这,不禁让我想起诺贝尔,想起苏特纳。我是从联邦德国电影《世界的心》了解他俩的。诺贝尔为和平建设发明了炸药,可因政客将它使用于制造炸弹毁灭人类而极度悔恨。曾做过阿尔弗雷特·诺贝尔秘书的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少女时代崇尚战争。当新婚丈夫阿图尔(Arthur)男爵牺牲于“一战”战场后(第二个丈夫也死于战争),贝尔塔幡然悔悟,写下了《放下武器!》等小说,并于1891年创立了奥地利和平主义组织,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苏特纳夫人尽管跟诺贝尔相处短暂,但终身书信往返。诺贝尔把和平奖加入诺贝尔奖项的决定,也是深受这位奥地利女作家的影响(苏特纳本人也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电影凝练浓缩地塑造了贝尔塔·苏特纳从战争狂到和平卫士的人生历程。晚年她依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频频奔波,最终逝于飞奔维也纳的列车上。影片特写镜头显示她安详平和的面容,画外音是列车上两个女乘客的对话:
“她临死痛苦吗?”
“不。她睡着了。”
忘了扮演贝尔塔·苏特纳的那位演员的名字。她不仅以酷似的外貌,更以杰出的演技,突破了人物从少女到老妇巨大跨度的表演难度,让那颗“世界的心”历经半个世纪还在我胸腔跳动。影片里,某个静静的夜晚,诺贝尔叩开了贝尔塔的单身宿舍的房门,虔诚地向她表达爱意。可惜后者因心存逝去丈夫阿图尔的影子而婉谢。诺贝尔黯然神伤。离去的诺贝尔,牵着他的狗,默默地渐行渐远,一直走向银幕深处,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孤独男人和一只狗的黑色剪影。——由此漫溢出来的小布尔乔亚的淡淡忧伤,至今难忘……
目睹战争残酷而热爱和平,早成人类共识。尽管从全球范围看,战争从未停歇,国与国间,政党与政党间、集团与集团间的利益角逐,时不时会引发火药,涂炭生灵。但毕竟跨进了21世纪一十年代,各国统治者头脑清醒多了。各色“恐怖分子”是21世纪人类的顽敌,也引起了世界的警觉与防范。是否可比较乐观地估计:持久和平是有望的?
和平应该是有望的。因为和平在每个人心里。深入人心的东西是有望的。德国一位作家曾这样评价《安妮日记》:“几百万人的声音被压下去,而这个低低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悄悄话……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因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是在纳粹屠杀下写给和平写给人性的!
从正直的作家、艺术家到平民,心底藏着和平。巴别尔在描写苏波战争的《骑兵军》中写到,骑兵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因师长夺了他的爱马而愤然退党、退伍,他向政治委员狂喊:“毙了我吧!”他容忍不了专制和欺诈,因为在他和作者巴别尔的“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异曲同工,雷马克在《凯旋门》里,写了拉维克复仇杀了盖世太保哈克之后,他放眼四周,是一个极为恬静的夏天的早晨:白杨、开满矢车菊的田野、新烤面包的香味、小学校里传出的儿童歌声、洗好的衣裳在风里飘动、燃烧过的田野开始返青……这就是拉维克所有行动的最终目的:和平!据扬·德尔达同名小说拍摄的捷克电影《沉寂的防御工事》中,1945年5月布拉格查理大桥掩蔽体里,抵抗战士粮尽弹绝。纳粹进攻的枪炮声竟也戛然而止,四周一片寂静。女战士哈琳娜抬头,蓦然看到了一束盛开的丁香花,希望的微笑瞬间绽开在她脸上。观众心里也随之敞亮:胜利了!和平有望!萧洛霍夫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据此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结尾处,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红军战士索科洛夫,抱着那如风中杨柳般颤抖着的孤儿小男孩(他俩将从此相依为命)的描写,这战争残酷现实中展示的人性的温暖,不比炸弹更强大?
真正具有震撼力的,不是杀人武器,而是和平与人性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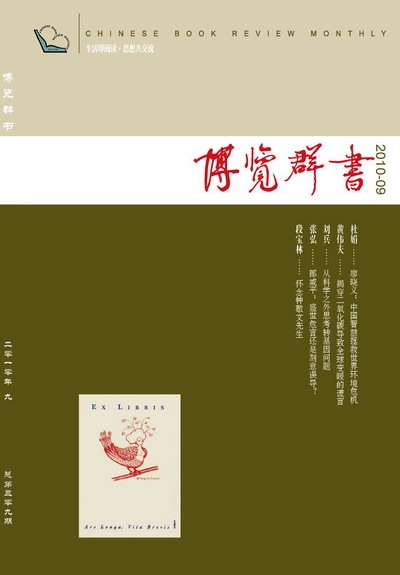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