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双语词典源流的学者常提起《一切经音义》和《梵语千字文》。
最近偶然读到周一良先生的文章《中国的梵文研究》(收入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才知另有一些文献与兹相关。
周文说佛经翻译事业开始于后汉,至宋而歇。唐代为翻译佛经的鼎盛期。玄奘等通梵文,也通印度方言。翻译的行当有“译语”、“证梵文”、“证梵义”之分。中国僧人研究梵文的著作分“悉昙”和“字书”两类。“悉昙”属于梵文拼音书:“现存这类梵文拼音的书,有唐山阴沙门智广的《悉昙字记》和北宋时印度僧人法护和中国僧人惟净合编的《天竺字源》七卷。”
据周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记载,郑樵著有《论梵书》三卷,可惜不存。“想来也是论悉昙的。《通志六书略》里有‘论华梵’三则,大都讨论梵字。”周先生喜欢郑樵所谓“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并因此说他“对梵文有相当了解”。
关涉梵文的字书,“梁代宝唱有《翻梵语》,共十卷。把经典里译的梵字抽出来……注以汉译。”周先生说此书与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近似,但不算梵汉字典。我们溯源的人,大抵算它双语词典的相关书籍。
9世纪中叶日本一个和尚把《梵语千字文》带回东瀛。据周先生说1773年有刊本:“在这刊本的后面,附有《梵唐消息》,也是一部字典,包含310个常用字。”此前1732 年有刻本《梵语杂名》,是由一个叫圆仁的和尚带回日本而保存至今的。
“大正藏收有《唐梵两语双对集》,题作天竺僧人……撰。……还有一部《唐梵文字》,包括1117个字。”也在公元9世纪,西藏僧侣编了一部《梵藏字典》,“元代传入内地,蒙古喇嘛和汉族僧人又加上了蒙文和汉文。”1853 年俄国人把它带回圣彼得堡大学。1915年日本人以《翻译名义大集》为名刊印。
周先生的文章长达14页,信息异常丰富。对梵音在僧人那里为何如此重要之类的问题详有论述。我的话题只涉及双语词典溯源,因此就不再展开引了。
另因同一话题阅读梁晓虹等著《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版),发现我等双语词典溯源者,于《一切经音义》的信息方面著文也嫌含糊。徐复老先生为梁书所写的“序”或可解惑,因此照抄一段如下:“玄应、慧苑、慧琳、希琳等既为佛门高僧,精通印度声明,亦为训诂大家,广阅儒典,精究文字诂训,故无论玄应《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还是希琳《续一切经音义》,均能广引文字、声韵之书,注释训解,援引群籍,证据粲明。故佛经音义不仅为佛门信徒读经所需,亦为历代文字、声韵、训诂学者所珍视。”徐文还提及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一书。
梁晓虹另有著作《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版),也是我等双语词典溯源者开拓视野的读物。
徐时仪著《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2月版)第187 页引陈炳迢《我国民族语言对照词典简史》一文里的话,或可证明本文说我等含糊的提法。陈文认为“我国现存最早收有梵语词汉译的,是北齐沙门道慧的《一切经音义》、唐沙门慧苑的《华严经音义》、玄应的《一切经音义》等佛典辞书。”
徐先生说:“实际上北齐沙门道慧的《一切经音义》今已不存。根据现有史料,梁释宝唱撰《翻梵语》一卷,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唐释义净撰《梵语千字文》,列举了约千来个词,此书可以看作是梵汉对照读本……此外,还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礼言集的《梵语杂名》。这两部书已略类似字典。《唐梵文字》同《梵语千字文》差不多。《梵语杂名》按照分类先列汉文,后列梵文。据此,可以认为我国双语词典的雏形至迟在唐代已产生。”
徐先生的这本专著61万字,739页。
坊间另可得于亭著《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可资参阅。于著28.9万字,30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本文编辑 陈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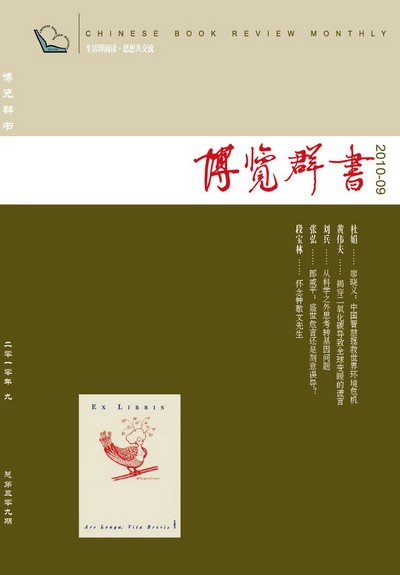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