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次写蒋复璁(字美如,号慰堂)老师,是1990年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斯机构(Smithsonian)作研究。文章发表在台湾《新生报》。转眼间,20年过去,那家报纸已经没有了。
蒋老师在台湾做过中央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我上他的课,是史学系的博士课程。他教我们“版本目录学”,地点在故宫博物院宿舍。学期结束,他都要请我们吃饭,那是一件大事。
大约30年前,蒋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谦虚”。当时我对这句话,没有什么了解。但是这种话少有人说,也就印象深刻,记到现在。30年后,这句话我有了体会,对老师更加佩服,更有无限的感念。
在中国,儒家一直是知识界的主导学派;知识分子自然也多所遵循其传统教化。儒家的基本形象,大概可以用“温良恭俭让”几个字形容。这几个字可以代表孔子的形象,也可以代表儒家的形象。换句话讲,儒家是以谦恭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著称。但是,《史记》上却记载,两千五百年前当孔子见老子的时候,老子劈头就说他“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孔子回去对他的学生说:今天我看见龙了!表示他对老子的佩服。
老子为什么说孔子骄傲呢?儒家不是在行为上要求谦虚有礼吗?老子的说法必有其深义,他绝对不是说孔子的言行举止骄傲;如果他说孔子的言行举止骄傲,那是与孔子形象完全相反的事情。老子在说什么呢?
儒家由孔子开其宗。孔子个人有一种气味,而影响到整个儒家风格;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在社会上蔑视习惯礼数,所谓的没有礼貌;而是骄傲地面对自己的存在及命运。在老子的立场,他认为这种态度完全不实际,没有用,所以他说“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说孔子骄傲,是说孔子面对自己的存在及命运时不谦虚;是说孔子以为主观和客观可以相对抗,理想和现实可以相对抗的态度不谦虚。老子出于一片好意,表示不要活得太辛苦了。孔子也受教,但是他做不到!否则他也不必说老子是龙;龙代表千变万化、可望不可及。
孔子到了一定年龄,个性也有所改变。例如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司马迁也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可见50岁以后的孔子,渐渐知道天命难违;知道主、客观间的互动与妥协,是人生常态。《易经》是强调主、客观变化,而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相反的学问。孔子注意《易经》,表示他对存在与命运的骄傲有了转变。他开始对存在与命运有了谦卑的感觉,他终于了解老子要他谦虚是什么意思。他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那句话,非但谦卑且有忏悔的意思。孔子不再年轻气盛。
虽然如此,辛苦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然是儒家的主轴精神。子贡是这样,所谓“赐不受命”;孔子家乡的人也是这样,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后世的孟子、荀子以至世世代代的儒家信徒都是这样;对于个人的存在不谦虚、对于命运不谦虚。这种不谦虚,孟子表现得最激烈,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老子说孔子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骄傲。以个人而言,“我”之于社会中,何其渺小;抱持着绝对的高人一等心态,与整个社会相计较,何其痛苦?以社会而言,若是人人都怀抱“舍我其谁”的心态,相互纷争,社会何其混乱?这种骄傲不是为人处事上的、礼貌上的骄傲;而是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自尊的表现。这种心态若是不得控制,便走上狂妄自大的路;所谓“狂简”。这是老子批评孔子的原因,也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信徒的痛苦根源。
儒家自汉代起,成为中国的法定学术。印度佛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有好多派别,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以佛教的立场而言,那种差异称之为因缘说法。而各种派别间,最能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的,自然要说到禅宗。
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的说法,除了天台、法相、三论、华严四门以外,密、净土、律、禅是专门讲如何解脱修行的法门。这四个解脱修行法门中,禅宗最能够与中国原有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同时因为禅宗不讲鬼神,与其说它是宗教不如说它是哲学。这种介于宗教与哲学间的思想,很受中国知识分子青睐。魏晋清谈,固然可以说已有禅宗影子,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谈禅更是普遍。宋代理学混合儒、释、道三家,那释的部分不涉鬼神,便以禅宗为主。明代王阳明建立心学,也是名义上遥接孟子“求其放心”之旨以为儒学延续,实际上禅味十足。否则王氏末流泰州学派,也不会得“狂禅”之名了。
禅宗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大,而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要将禅宗与其它宗派作个比较了。禅宗所以不像宗教,因为它非常强调自修,也就是认为人可以因为修行而成佛。唐代六祖慧能到黄梅见五祖弘忍时候,二人的对话,把禅宗的风格表露无遗。五祖说:“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立刻顶他一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六祖这句“惟求作佛”把话讲得很清楚:不做和尚,不做罗汉,不做菩萨,只要作佛;其它都是“余物”——剩下的东西!这种精神的涌现,似乎又见儒家孟子那种“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的凌厉气势。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更是能够和“惟求作佛”千古辉映,不过一个要成圣,一个要作佛。
就宗教而言,要作佛虽然是大气魄,但是要作佛是苦的。这个苦处并非过程辛苦之苦,而是它与宗教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驰。宗教很简单,它的存在目的是予人安慰;通过对于一种未知而不得求证的信仰,让全能者赐予保护与希望。但是要作佛,却是通过修行,让自己变成那个虚无飘渺的全能者。既然要做全能者,可以因为修行而变成全能者,那么,所有全能者能够给予人的安慰,便都因此而消失了(因为,自己即是那个想象中的全能者)。这是禅宗作佛之苦,它的苦与儒家那种要成圣的苦一样:因为对存在与命运的骄傲,导致现实上与精神上的磨难。
宋代禅宗五派之一,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禅师在《四料简》上说得好:“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禅宗修持加上净土宗修持,好像老虎有了角一样厉害)什么意思呢?原来净土是要上西天,而礼拜阿弥陀佛的。延寿禅师希望禅子们除了一心作佛之外还要念佛礼佛,希望禅子们除了自参自修外,还要对佛菩萨表示一定的尊敬,表现一定的谦卑。进而明白人定胜天固然不错,但是天助自助又未尝不好?除去自我修持,让佛菩萨加持、帮助有什么不好?既然信佛,何必拒佛于千里之外?去掉这种无意义的骄傲与固执,才是成佛之道。
孔子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永明延寿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是儒家与禅宗领袖的真心法语,无上忏悔。然而,千年过去了,儒家依然慷慨激昂,禅宗依然慷慨激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因为慷慨激昂而苦恼。因为,面对存在及命运时的不谦虚,是一种最大的苦恼根源。
蒋老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谦虚”,是一种深刻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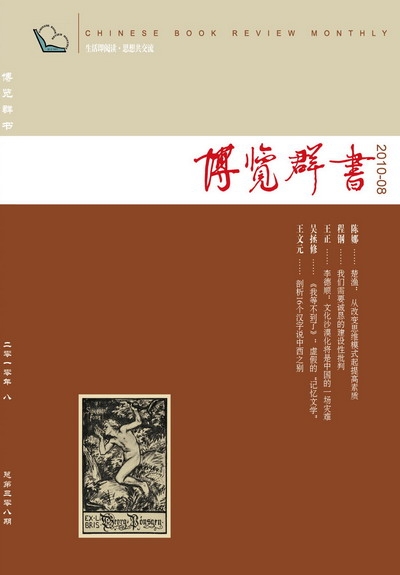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