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中学语文的我们都会分析句子成分,懂得中心词分析法。比如我们打开一篇新闻报道,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当地时间10月31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在韩国庆州和白会议中心举行。”我们能够找出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会议”、谓语“举行”,一下子抓住句子的主干:会议举行。然后,我们会找到句子的附加成分——时间状语“当地时间10月31日上午”、地点状语“在韩国庆州和白会议中心”、主语的定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主语加定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偏正短语,我们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来观察它内部的结构关系:
第一层,“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是定语,“会议”是中心语。
第二层,定语部分可以第二次切分为定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心语“第一阶段”。中心语“会议”是一个词,不能进行第二次切分。
第三层,“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切分为定语“亚太经合组织”、中心语“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可以切分为定语“第一”、中心语“阶段”。
第四层,“亚太经合组织”可以切分为定语“亚太”、中心语“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以切分为定语“第三十二次”、中心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我们看到,这个多层嵌套的定中结构的偏正短语可以被层层切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分别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它们之间都存在符合句法规则的搭配关系(上面的四层分析都是定语和中心语关系,往下还可以继续细分,为节约篇幅,我们略过)。那么,分析句法结构时,是否分出来的组成部分有意义且能搭配就是合理的呢?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有两种分析方式:一种是“父亲的父亲”是定语,“父亲”是中心语;一种是“父亲”是定语,“父亲的父亲”是中心语。“父亲的父亲”即祖父,不论“祖父的父亲”还是“父亲的祖父”,其所指都是曾祖父,两种分析法在意义上是等值的。那么,从句法规则上来看二者是否等值呢? 陆俭明先生认为,句法分析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必须对同类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这个例子和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多层嵌套的复杂定语的例子有所不同。开头所举例子中的定语部分包含专有名词、数量短语、偏正短语等,分别从会议的主体、会议的序列、会议的性质、会议的进程等不同方面对“会议”进行了限定,词语之间的紧密关系比较明确。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很难说是前面两个“父亲”更关系紧密还是后面两个“父亲”关系更紧密。怎样才能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呢?
“父亲”是一个指人名词,首先陆先生对指人名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分为六类:带姓的姓名或称呼(A)、不带姓的名字或小名(B)、论职位的职务名称 (C)、不论职位的职务名 称(D)、表示亲属或师友等关系的称谓(E)、人称代词(F)。
然后陆先生对这些指人名词进行排列组合,观察两个指人名词相互组合、三个指人名词相互组合、四个指人名词相互组合、五个指人名词相互组合乃至N个指人名词相互组合时的情况,结果发现,指人名词相互组合形成的偏正结构,其内部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六种指人名词都可以在偏正结构第一个名词的位置出现;如果前一个名词位置上是F,相邻的后一个名词可以是F以外的任何一种指人名词;如果前一项是除F以外的任何一种指人名词,那么相邻的后一项只能是B、D或E。前一项名词总是制约着后一项名词的选择,从语义上看,相邻两个指人名词之间存在着领属关系,不相邻的两个指人名词之间不一定有领属关系。例如“王科长的秘书的弟弟的爱人”,相邻的“王科长”和“秘书”、“秘书”和“弟弟”、“弟弟”和“爱人”之间存在领属关系,而不相邻的“王科长”和“弟弟”、“王科长”和“爱人”、“秘书”和“爱人”之间都不存在领属关系。
接着陆先生又对指人名词相互组合形成的偏正结构的内部构造层次进行了分析。句法结构的扩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替换性扩展,即用一个较长的成分替换原结构中较短的成分。如“会议举行”可以通过替换扩展为“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一种是组合性扩展,即原结构作为一个组成成分跟另一个新的成分相组合,从而形成一个较长的新的句法结构。如“会议举行”可以通过组合扩展构成“会议在韩国庆州和白会议中心举行”。语言事实证明,指人名词相互组合形成的偏正结构是通过组合扩展形成的,因为如“我的同事的爱人”显然不是由“我的爱人”通过替换扩展而来的,而是“我的同事”通过后加“爱人”组合扩展而来的。从理论上说,指人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的前一项名词总是制约着后一项名词的选择,可以通过后加型组合进行无限扩展。再看“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这个例子,显然,其中第一个“父亲”制约 着第 二个“父亲”,是第二个“父亲”的领属定语;如果强行拆分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看似领属关系也成立,但不符合指人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中前项名词制约后项名词的选择这一普遍规则。也就是说,尽管“爸爸的爷爷”与“爷爷的爸爸”在语义上是等值的,但从句法结构的规范性来看,二者的构造层次并不等值,前者符合指人名词组合的层级规律,后者则不符合规律。
最后,陆先生对两种不同的层次分析语义上等值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这完全是一种巧合。就像当我们对一个复杂算式进行四则运算时,一定要按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来运算,否 则就不会得到 正确答案。为什么有时不按规则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仅仅是有条件的偶合。如1×3+4,1先乘以3再加4和先3加4再乘1都能得到正确答案7,但后一种算法是错误的,如果乘数不是1,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汉语没有语法。比如北京人打招呼的常用语“吃了吗您呐?”也可以说成“您吃了吗?”“快点儿走吧! 时间不多了。”也可以说成“时间不多了,走快点儿吧!”学习了陆先生关于“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分析,相信我们都会感受到,汉语不仅有语法,而且有着非常严密的语法规则,只是需要像陆先生这样的研究者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去挖掘、去发现。
怎样去挖掘、去发现日常语言中习焉不察的规律? 陆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科学的分析范式。如现代汉语的疑问语气词到底有几个?“啊、吧、呢、吗”都可以出现在疑问句的末尾,是不是就都是疑问语气词呢? 陆先生指出:判断一个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不是疑问语气词,绝不能根据语感,而要看它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这一点又必须能在形式上得到验证。验证的办法是比较,那就是从疑问句和非疑问句,从这种疑问句和那种疑问句之间的最小对比中,来确定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根据这一原则,陆先生通过大量语料的细致对比,从形式上论证了现代汉语中的疑问语气词有两个半:“吗”“呢”和半个“吧”。“啊”虽能出现在疑问句末尾,但它在疑问句里不起负载疑问信息的作用,所以不能看作疑问语气词。
当然,一般人可能不会像语言学家一样去探究隐藏在语言背后的规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陆先生的字里行间感受逻辑的力量,感受论证的严谨,感受问学的快乐。在《吴县老东山话里的“阿VP?”疑问句》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和百岁高龄老母亲的一段很生动、很亲切的对话(为了方便,我们把原文中用国际音标表示的方言直接改成了普通话词汇):
我:姆妈,我来哉。母亲:俭明,倷又来开会哉。身体阿好?我:好,倷看!母亲:马真阿好呀?我:俚阿蛮好。母亲:陆征阿好呀? 我:阿蛮好。母亲:葛么小熊呢?我:阿蛮好。母亲:俚得阿常打电话来?我:常打,两三个礼拜一趟。母亲:葛么陆征得小囡阿好呀?我:俚得才蛮好。母亲:大家才好真好。马真,我是晓得俚身体一直勿大好,葛么俚现在身体到底阿好呢?我:勿宁骗倷,俚蛮好,倷放心好了。
这段对话读来让人感觉非常温暖,老母亲对儿子一家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就是这样很家常的一段问候,陆先生发现其中包含了三种“阿 VP?”(VP表示动词性结构)疑问句形式。
刚入门的语言研究者常常苦于找不到研究课题。读了《陆俭明文集·第一卷描写篇》,你会发现语言研究的课题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就蕴藏着无数语言研究的课题。如当我们手上拿着一个苹果来问孩子时,既可以说“这是什么?”也可以说“这个是什么?”当孩子回答时,也是既可以说“这是苹果。”也可以说“这个是苹果。”那么,这二者有没有区别,区别之处又在哪里? 陆先生就写了《“这是……”和“这个是……”》一文,对二者的使用场合、用法差异进行了厘清。
从语言教学中,或者从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也可以发现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外国留学生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大堆意见”“吓了一大跳”可以说,“一小堆意见”“吓了一小跳”为什么不能说。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陆先生对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写了《现代汉语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
总之,只要学会观察,勤于思考,始终保持问题意识,就能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深入探究,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陆俭明文集·第一卷描写篇》共收录了陆俭明先生对现代汉语的独特的语法现象、词类、具体词语、代表性句法结构和句式等进行分析描写的论文共39篇。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59年,最晚的文 章发 表 于2020年,写作时间跨度长达60余年。更难能可贵的是陆先生已经90高龄,至今仍对学术研究葆有无限激情,笔耕不辍,时有新作。学术使他的人生更充实、更厚重,人生使他的学术更鲜活、更辉煌。这种学术和人生交相辉映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陆俭明文集·第一卷描写篇》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阅读,或者发现思考的方法,或者激起研究的兴趣,或者得到豁然开朗的答案。就像“爸爸的爷爷”和“爷爷的爸爸”这样平常的语言结构,也许你从来没想过里面居然隐藏着一条严密的语言规则,而且其富有逻辑的论证你也很容易读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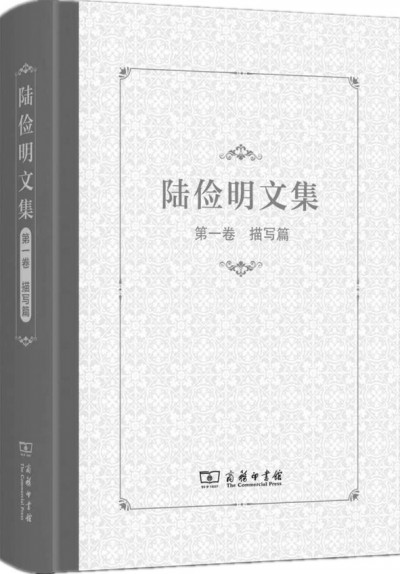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