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我应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ZiF,以下简称“中心”)的邀请,在那里度过了八周的愉快时光。其间,我跟来自德国、美国和东亚的学者们一道,共同讨论“自主动力”(Eigendynamik),也就是那些在社会内部不断自我延续、循环生长的过程,看到等级秩序、临场文化与共识取向如何在不同文明中制造出一种自我维系的力量。
中心到处可见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影子:他的雕像、著作、遗物以及他晚年在这里生活与讨论的照片。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常常想起埃利亚斯的人生和思想。埃利亚斯关心的“文明的进程”,其实也正是关于社会如何在无形中生成、延展并驯服自身的动力。他笔下的长时段变迁、日常生活与宏大结构之间的张力,和我们在中心探讨的“自主动力”隐隐呼应。正是这种呼应,让我感到:学术并非抽象的理论堆砌,而是穿梭于记忆、经验与思想空间之间的一种对话。
那一天,中心的食堂没有开门,我们便移步到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生简餐厅(Cafeteria)吃午饭。饭后,大学的两位历史学教授提议带我看看他们的主楼,我欣然应允。竣工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学主楼大厅宽敞明亮,它以单体形式统揽几乎所有的学术功能。除了教室与会议室,还散落着小卖部和餐馆,仿佛在学术与日常之间架起了一条自然的通道。其中,一家名为 Univarza的土耳其餐馆格外惹眼。走近时,空气里飘荡着烤肉与香料的气息,伴随着师生们热烈的交谈声。土耳其老板迎上来,笑问我们要点些什么,我们只是摇头,说随便看看。两位教授边走边谈起校园往事: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埃利亚斯常常在这家餐厅用餐。那时,他作为中心的常驻学者,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学术印记。恍惚间,这些熟悉的走廊、饭堂与喧闹声,似乎都被他的身影所覆盖——学术不仅遗留在书页与概念里,也在生活的气味与日常的场景中延续。
埃利亚斯晚年选择在这里安顿下来,潜心研究、生活,与师生互动。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屋顶洒下,此时此刻,我们仿佛与那段历史重叠——看见半个世纪前的埃利亚斯也在相似的光线下经过此地。他在比勒费尔德的日常点滴,已化作校园里思想与空间交织的传奇篇章。
重返德国的智者
埃利亚斯1897年出生于德意志帝国的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青年时期的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法兰克福大学任职。1933年纳粹上台后,这位犹太裔学者被迫流亡英国。在异国他乡,埃利亚斯度过了漫长岁月,直到57岁时才在莱斯特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eicester,今莱斯特大学)获得第一份稳定的教职。他的重要著作《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der Zivilisation,1939)和《宫廷社会》(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1933)最初问世时反响寥寥,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再版后才逐渐引起学界瞩目。学术声誉的高涨让年逾古稀的埃利亚斯重新受到故国的邀请。1971年4月,比勒费尔德大学新成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是仿照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在德国建立的第一所同等性质的高等研究院——在尚设于雷达城堡(Rheda Castle)的临时地址举办了首届“作者研讨会”,专门围绕埃利亚斯的思想展开讨论,以示对这位历经劫难的学者之敬意。来自各领域的研究者济济一堂,对埃利亚斯的代表作和理论进行了热烈交流。此次别开生面的聚会标志着埃利亚斯与比勒费尔德的初次结缘。
1972年10月,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南面的东条顿山森林(Ostteuteburger Wald)脚下,“跨学科研究中心”正式落成。中心除了研究室、研讨室、会议室、食堂之外,还建有驻站研究员的公寓。此后,中心又多次邀请埃利亚斯参与学术活动。1978—1979年度,他作为常规成员参与了历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主持的“哲学与历史”跨学科研究项目,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切磋讨论。1980—1981年,他再次受邀加入文学教授威廉· 福斯坎普(Wilhelm Voßkamp,1936-)组织的“早期近代乌托邦的功能史”研究项目。在中心工作期间,埃利亚斯深深迷恋上了这里的环境与学术氛围。他把这里誉为国际学术界的“世外桃源”——宁静而又激荡思想的一片乐土。1979年跨学科研究年结束时,这位博学长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下! 自1978年底起,他成为中心迄今唯一的常驻研究员,一直在此工作和生活,到1984年10月才依依惜别。在比勒费尔德的这些年里,他倾注心力撰写了多部著作,并多次热情参与研究中心的项目研讨,为各项学术活动贡献智慧。
埃利亚斯的学术贡献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1980年6月22日,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卓越成就。在主楼大厅举行的颁授仪式上,满头银发的埃利亚斯从系主任手中接过证书,台下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1986年,在比勒费尔德大学提名推荐下,他被授予联邦德国功绩勋章(骑士指挥官十字级),由联邦议院议长代表总统颁发。
1984年深秋,87岁的埃利亚斯在中心举行的欢送会上正式告别了他倾心投入的比勒费尔德学术之家。当天学校领导和同事齐聚一堂:校长、著名数学家卡尔·彼得·格罗特梅耶(Karl Peter Grotemeyer,1927-2007),中心主任、著名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普林茨(Wolfgang Prinz,1942-)以及社会学系主任约翰内斯·伯格(Johannes Berger,1939-)等人亲自为他送行。这一刻,校园里见证了一个学术时代的落幕,也铭记下思想与情谊交织的动人篇章。
在中心的日常生活
埃利亚斯在比勒费尔德的日子平静而充实,生活起居透着学者的自律与情趣。每天清晨,他都会来到中心内的小型室内游泳池,舒缓地游上几圈,以强健的身心开始新的一天。
一位当年与他比邻而居的青年学者回忆说,埃利亚斯独居于此,起初对于他人的照顾颇为谦让,但在邻居开车代他采购周末生活用品的提议下,他终于欣然接受了这份好意。很快,两人养成习惯,下午常结伴沿着研究中心后方通往条顿山森林的幽静小径散步——这也是我在中心期间最爱去散步的地方。据说,在林间漫步时,埃利亚斯神采奕奕地与同伴谈天说地。从自己的坎坷人生到对世界局势的见解,他侃侃而谈,话题既有学术洞见,也夹杂着人生智慧。他酷爱大自然的宁静与树木的清香,这成为他繁忙工作之余让思想沉淀发酵的土壤。
埃利亚斯的起居室布置朴素而别具情调:书架上摆放着他收藏的非洲木雕小雕像,茶几上总是不缺一盘饼干——游泳和漫步归来,泡一杯茶、搭配几块饼干,成为他日常的小小仪式。流亡岁月的历练并未磨灭他的好奇心和人文情怀;相反,他始终关切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人类如何学会合作共处,又为何屡陷冲突与暴行。这种执着的思想探求贯穿在他日常生活的点滴中。
在比勒费尔德期间,埃利亚斯并不与世隔绝。除了静心著述,他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思想火花。在中心或大学里,他不定期举办研讨课和专题讲座,每一次都有众多师生慕名而来,场场座无虚席。学生们用心倾听这位学术长者的真知灼见,常常在会后围着他提问探讨。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睿智的谈吐,让年轻学者们如沐春风。知情者形容埃利亚斯“温和随和却坚定执著”,在学术原则上绝不动摇,而待人接物又谦逊友好,这种难能可贵的风范令身边人由衷敬佩。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师生也珍视这位迷人的思想者——他的长期驻留,不仅培养了一批热情求知的听众,更为校园平添了一种兼容并包、追求卓越的学术气质。
校园里的记忆与痕迹
今天,当你走上中心大厅的上层回廊,便可见埃利亚斯的头像陈列在静静的一隅。这尊雕像以青铜铸成,安放在木质基座之上。雕像没有刻意修饰面部,而是以粗犷的线条与深刻的凹凸呈现出岁月的痕迹:微微下陷的双颊、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眼窝,使得整张面孔显得凝重而内省。额头的起伏与面部的不对称,又带来一种近乎不安的真实感,仿佛在提醒观者:这不是理想化的学者肖像,而是一个不断思索、饱经时代冲击的人。这是雕塑家格尔达·鲁宾斯坦(Gerda Ru⁃binstein,1931-2022)于1977年创作的作品。鲁宾斯坦出生于柏林,又长期在英国进行创作。这尊雕像正好折射出这种“交汇”:一位犹太裔雕塑家为一位犹太裔社会学家立像,而两人都与英国有深厚的渊源。雕塑背后的墙上写着埃利亚斯在《丹吉尔之旅》(Von der Tangerreise,1987)中的一句话:“这些人是多么奇怪,我自己是多么奇怪,而我们在一起又是多么奇怪。”《丹吉尔之旅》是埃利亚斯在非洲之行之后所写,用以表达他面对两种不同文化的感受与反思:它反映出一种双重的陌生感——对他者的陌生,同时在他者眼中也被视作“他者”。上面的这句话不仅是旅行中异文化经验的感叹,更像是对人类处境的凝视。自我与他者的交错、熟悉与陌生的并存,正是埃利亚斯社会学思考的出发点。而我们此次在中心讨论的“自主动力”,其实也在探问类似的问题:个体与群体如何在互动中不断生成动力,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出社会的秩序与变化。如此看来,埃利亚斯的凝视与今日的研究主题,跨越时空地呼应着彼此。
站在雕像前,最令人难以忽视的是那双空洞却专注的眼睛,它们似乎并未注视某一个人,而是穿透眼前的空间,凝视着更深远的社会图景。与背后墙上的引语相映照,这尊雕像不仅塑造了一张面孔,更塑造了一种姿态——思想者的凝视,既投向他人,也反观自身。
雕像旁的玻璃展柜中陈列着埃利亚斯在比勒费尔德期间出版的著作,以及他生前喜爱的若干物品——泳镜、木雕,甚至他钟爱的饼干盒,都在其中,仿佛在细述这位“人类学者”昔日的生活片段。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中心有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讨论室——这是唯一一间以人物命名的房间,足见他在此的地位与影响。
埃利亚斯离开后,他的思想遗产通过多种方式在比勒费尔德延续和发扬。大学方面在多年后专门设立了“诺伯特·埃利亚斯奖学金”,资助来自非洲国家的青年研究者来中心访学——我驻站的这段时间里,一直能看到非洲年轻学者的身影。这一举措既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也寄寓着他的学术关怀:埃利亚斯一生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而通过支持非洲学者,他的影响跨越文化疆界,在全球层面促进着知识的交流与合作。今天,在比勒费尔德大学的校园里,到处可寻埃利亚斯留下的痕迹:无论是中心大厅永远凝视前方的塑像,还是社会学系珍藏的那张名誉博士证书,都在默默述说着他与这片土地的不解之缘。正如历史学家科泽勒克所言,埃利亚斯在比勒费尔德度过的这些岁月堪称他人生与事业的“黄金秋天”,不仅丰硕了他的个人成果,也滋养了校园的学术土壤。
思想与空间的余响
比勒费尔德大学宏伟的主楼横跨约30多万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连体校园建筑之一。这座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建筑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设计理念:建造者的目标不是打造一座供炫耀的“象牙塔”殿堂,而是建设一间用于思想交锋的作坊;它不应沦为冰冷刻板的功能箱体,而要成为孕育高度敏感交流过程的环境。这样的空间理念在埃利亚斯的故事中得到了印证——当这位阅尽沧桑的思想者漫步于校园,当他在课堂、研讨厅和林间小道上与人对话,抽象的思想便通过具体的场所得以生根发芽。今天的主楼大厅依然熙来攘往,墙壁上的海报与不同语言的交谈声交织,好似昔日学术对话的回声。一旁的Univarza餐厅里飘出浓郁的咖啡和异域香料味,赋予这座钢筋水泥结构以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一方校园空间,正如当年一样,包容着多元的文化与思想。在这里,人们于餐桌边交换观点,在走廊上偶遇讨论,从课堂辩论一路延伸到午后咖啡的闲聊——思想的种子在无数日常场景中传播、生长。
我不禁想到,埃利亚斯当年或许也曾像我们一样,在忙碌的研究之余步入校园的餐厅或者咖啡角,与同事闲话家常,观察年轻学生们意气风发的神情。也许并无惊天动地的时刻,但正是这些寻常的日子,累积起了他在比勒费尔德的独特篇章。当我们走出主楼,回首凝望那熟悉的大厅,仿佛还能听到时空深处传来的低语:建筑犹在,林木依旧。思想的足迹早已化入这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之中,成为空间的一部分。思想与空间互相濡染,荡漾出历久弥新的回响。埃利亚斯的启示也正在于此:伟大的思想并不滞留于象牙高塔,而是深植于日常,在特定的空间中萌芽、生长、开花,并最终融入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时间长流相互交织,愈久弥香。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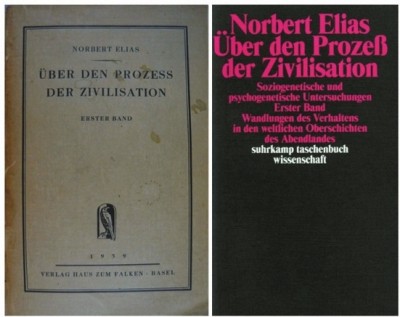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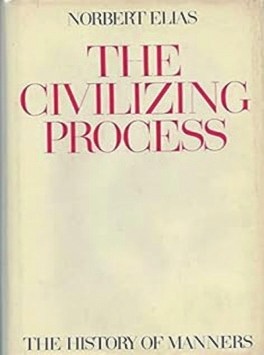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