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海饼干的长篇小说《凤起》是一部记忆之书、创伤之书与疗救之书。小说以几代女性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真实与艺术地再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史、抗争史与新生史,并由此展开对历史和人性的深沉凝视与持久凝思。
故事的主人公是血脉相连的四代女性:“我”太姥姥槐花、姥姥郐玉珍、母亲夏桐花、“我”(李凤衣)。小说中其他一些女性,如太姥姥槐花的母亲、姑奶奶、女佣翠林、王影男、王红丽、孙芙蓉、黄相文、女儿郑爱伊等,她们的故事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四代女性的形象。小说的叙事时间横跨近百年,从20世纪30年代至当下的21世纪20年代初。人物的成长空间,从旧中国的山东高密乡村到新中国不同时期的东北城市、部队大院,再到江南城镇等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部作品以女性为主体……想以此来呈现近现代女性坚韧、聪慧、鲜活的形象”,“我一直希望文学能照进现实,以我熟悉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写部长篇小说,以此作为我活过的佐证。”由此来看这部《凤起》,是一部作家的记忆之书,带有很强的自叙传色彩。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认为,记忆是书写的孪生姐妹。我们从“活过”一词中,似乎感受到作家的某种辛酸、无奈与不甘,所以要用文字倾诉她曾经的记忆,一如海外华人女作家张翎所说的,她“是为了自救才写作”。这部小说,何尝不是作家海饼干的一种“自救”的产物呢? 因为,这份记忆里不仅仅有爱与温暖,更有着痛与创伤,而后者是小说的底色,也让这部小说充满精神的厚度。
首先,小说再现了百年中国女性的创伤之痛,是一位“70后”女作家对百年中国女性创伤的再思录。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经历各种创伤,尤其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女性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创伤叙事成为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女作家笔下更是如此,如庐隐《海滨故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张爱玲《金锁记》、宗璞《红豆》、张洁《五字》、铁凝《玫瑰门》等等。海饼干的这部《凤起》亦是如此。美国当代创伤理论的代表学者多米尼克·拉卡帕拉将创伤分为“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两种。其中,“历史性创伤”主要指人为的历史性事件,如大屠杀、种族隔离等,而“结构性创伤”主要指超越历史的失落,如母子分离、自闭等。他认为,“历史性创伤”可以或者部分地得到解决,但“结构性创伤”却不能改变或治愈。由此来看这部小说,这两种创伤在这些女性身上均有着深浅不一的体现。前者如日本侵华战争让郐玉珍一家流离失所、“我”在少年求学时期曾一度被同学霸凌、“我”的战友黄相文和儿时伙伴王影男被杀。但小说中女性经受的创伤更多却来自后者,其伤害性更大。小说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因爱的缺失造成的孤独感。比如槐花在丈夫郐木死后的绝望、桐花因丈夫李白术一生为人处世的“游戏人间”而大伤脑筋、“我”缺少父母之爱终日保持沉默。二是对生育的恐惧。小说中因家族遗传等因素,郐玉珍、夏桐花和“我”怀孕时都出现巨婴现象,让她们对生育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即便到“我”怀孕时医疗技术已很发达可以做剖宫产,但“我”依然感到恐惧,“颤抖着被护士抬上推车”。
其次,小说勾画了百年来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面对“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几代女性采取的态度和处理问题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总体而言,大致可归为三种类型:盲从型、隐忍型与觉醒型。盲从型主要指第一代和第二代女性。“认命”是这种盲从态度的集中表现。如在第二章“玉珍篇”中,当郐木死后,槐花和三个女儿被槐花的母亲和哥哥任意处置——槐花被逼改嫁、玉珍年幼嫁人、碧珍文珍做了童养媳——虽然槐花和玉珍都有本能的反抗,但很快默认了这种安排。当母亲槐花被逼改嫁后,小说有四处写到了15岁少女玉珍的“认命”。隐忍型以第三代母亲桐花为代表。一方面历史的负累在她身上依旧强大,一些言行延续着前两代女性的重负,如在婚恋上不敢与高中暗恋的同学走到一起,而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嫁给了李白术,婚后对于丈夫的种种荒诞行为也只能忍气吞声;但另一方面,她毕竟是受过教育的新中国女性,有着一定的主见,如通过自学中医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受人尊敬“夏大夫”。这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觉醒型以第四代女性“我”为代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女性,对自身的身份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从求学、入伍、婚恋等方面尽管还受制于外在的诸多因素,但“我”的独立性较之前辈大得多,如在婚恋上迥异于她的前辈们,和相爱的人走到一起,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写作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作家。这四代女性对自身创伤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百年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嬗变历史。这种嬗变之路,也是百年中国女性从“物”到“人”的蜕变之路。当然,由于历史的因袭,即便是第四代女性身上,也依然保留着她们前辈身上的历史负累。
再次,小说还试图叩问造成人类创伤的历史与人性的因素。我们看到,小说中作者除了重点书写四代女性的创伤外,也着力描写了男性的创伤和历史的创伤。就男性的创伤而言,他们身上也有着“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如钱富贵的三个儿子两个死于抗战一个死于内战、夏寂的被杀、李白术终生怀才不遇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小说中的男性大都以孱弱与病态的形象出现,如郐木的肺病,李半夏的哮喘,李邱鹏的自杀,李南星的软弱等,他们身心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病”。另外,“半夏”“白术”“白芷”,不仅是小说中男性之名,也是一些中药材名,但终究这些药治不了他们的“病”。因此,小说中疾病和药材的隐喻,表明百年来中国男性亦是伤痕累累的,他们和女性的创伤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
为了更好地表现记忆与创伤,作家在艺术上也做了多种探索。如以人物统领叙事的结构安排,多种灵活的叙事视角,生动传神的人物刻画,诗意与散文化语言等等,都为小说增色不少。当然,小说也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在个别人物年龄上的矛盾与混乱,典型的是夏德义的年龄,小说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一些表达是互相矛盾的。另外,作为一种叙事伦理,如何让创伤和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作品中似乎并未过多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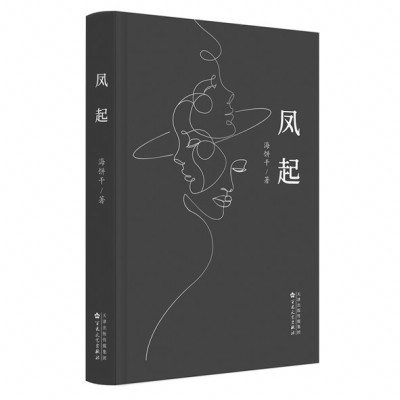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