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
诗学在东西方均有悠久历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诗学为诗人的创作制定法则与规范,同时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衡量与评判标准。从西方来看,浪漫主义以降,诗人的天赋与个性受到强调,诗歌创作的法则与规范不再受到重视,诗学的属性也发生了转变,由此前的规约性质逐渐转变成描述性质。诗学不再以制定写作规则为己任,而是对文学与写作本质展开思考,诗学批评也不再借助诗学规则来评判诗歌优劣,而是借助诗学提炼的方法与拓展的途径来对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展开分析。不过,尽管诗学的属性在历史中发生了转变,在所有文学研究途径之中,诗学始终是一种与文学本身保持直接、密切关系的途径,由于这种直接性与密切性,即使在研究多元化、向外转的今天,诗学仍然在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法国诗学——无论是古典诗学还是现当代诗学——是西方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法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深具法国学术研究特性,对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法国学者在诗学、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为反思我国的文学研究提供镜鉴。出于这样的考虑,《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在四十余万字的篇幅里,系统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法国诗学研究成果。这样一项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学界是首创的,就我所知,法国学界也还没有一部类似的研究著作。在我看来,这一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至少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廓清了“当代法国诗学”的内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任何研究在开始之前,都要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框定自己的讨论范围,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为之后的交流对话锚定出发点。“当代法国诗学”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为了对其进行界定,曹丹红从“当代”“法国”“诗学”三个关键词入手进行思考,认为其诞生于1970年,因为这一年,法国瑟伊出版社创办《诗学》杂志,同时推出“诗学”丛书,均由热奈特和托多罗夫负责。《诗学》杂志和“诗学”丛书之后成为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这一学科的基本面貌。五十多年过去,《诗学》杂志与“诗学”丛书依然保持着生命力,为法国乃至国际诗学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也为全面考察当代法国诗学提供了可能性。《当代法国诗学研究》所参考的文献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即来自《诗学》杂志近200期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诗学”丛书创办至今出版的113部专著。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研读与分析,曹丹红归纳出当代法国诗学的基本特征,并提炼出几个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写作本质研究”“文学类型研究”“风格研究”“叙事研究”“虚构研究”等,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构成了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第二,《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准确把握了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与根本任务。看到“当代法国诗学研究”这一课题,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当代法国诗学与传统法国诗学的区别在哪里? 这也是这部著作首先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曹丹红认为当代诗学,尤其是21世纪法国诗学主要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边界的拓展,包括研究对象的拓展(不再局限于纯文学,不再局限于文本媒介),研究方法的拓展(不再局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结构主义)等。第二个特征与前一个特征密切相关。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拓展令今日诗学有可能也有必要超越本学科的传统做法,向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逻辑学、语文学、认知科学等借鉴理论与方法,在此过程中,诗学的跨学科程度加深。实际上,当代法国诗学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于其他学科中,跨学科融合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常态。就此而言,《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在一种宽阔的视阈中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探索与实践。
当然,跨学科研究所涉及的视角与方法的多元性隐藏了一种风险,它有可能令研究偏离目标、失去中心。曹丹红对这种风险有着清醒的意识,因此在兼顾研究方法多元性的同时,她始终紧抓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也就是诗学的本质属性与根本任务,由此展开对诗学的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的探索。就其本质来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诗学就是一门致力于探索“文学性”的学科,历代的诗学研究者都尝试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正是这种对“文学性”的不断追问构成了诗学的存在理由与价值。跟随这根阿里阿德涅之线,我们看到,尽管从亚里士多德至今,“诗学”一词的外延与内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自始至终,它的使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最初致力于对悲剧与史诗创作过程的考察,到如今着力于对不同文学类型基本特征的描写,贯穿始终的,是诗学对文学作品之诞生、“未来之书”之创作的条件的探索,即使为文学创作制定规则已不合时宜,诗学仍坚守发掘文学潜力、促进文学更新的初心。实际上,《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将对文学“可能性”或“潜在性”的探索视作诗学与其他文学研究的最根本区别,这是这部著作提出的一个重要且中肯的观点。
第三,《当代法国诗学研究》试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一点特别通过著作第七章“诗学批评研究”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孔帕尼翁将文学研究分为理论、批评与历史三大内容,又指出“谈文学理论不能不谈修辞学和诗学”。从孔帕尼翁的分类来看,诗学属于文学理论,同时在与批评实践、与文学史的区别中确立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诗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是截然分离的关系。在“诗学批评研究”一章中,作者就如何理解诗学与批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一方面,文学批评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实践活动,要令其摆脱随意性和印象主义,批评者需要采取一定的批评方法,而诗学的任务之一正是批评方法的建构;另一方面,诗学同样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批评方法的建构不是研究者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来自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因此很多形式或结构研究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实践。作者进而指出,诗学批评以诗学建构的模式与方法观照作品,为理解作品带去新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推动对当代作家的批评,也有助于深化、更新对经典作家的认识。
不过,将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并非易事,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正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致命伤。为解决这一问题,曹丹红勇于探索,尝试进行了批评实践,借鉴诗学理论与方法对加缪与莫迪亚诺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进行了考察与分析,通过自身的批评实践,表明了诗学批评在调和理论与实践、揭示作家写作艺术与作品风格特色等方面的可能性,也直观地展示出诗学在今日文学研究中的功能与价值。
第四,《当代法国诗学研究》试图在研究中引入一种历史视野,在我看来,这可能是这部著作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也是其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正如诗学与批评的关系,诗学与文学史的关系也是彼此依赖、不可分割的。历史视野体现于这部著作的多个方面。首先,对当代法国诗学的研究结合了对其“师承”的剖析。理论虽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但它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代法国诗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样受到前人理论的影响。因此著作专辟一章,探讨了当代法国诗学的理论来源,对亚里士多德、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诗人瓦莱里等人的诗学探索及其对当代法国诗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对这一影响的剖析奠基于坚实的证据之上。例如在谈俄国形式主义对当代法国诗学的影响时,作者通过呈现一系列历史事件与人物互动,具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俄国形式主义进入法国、对法国文坛产生影响的过程。这种讲求证据的考据态度与方法体现出作者为学的严谨性。
其次,历史视野也体现于这部著作对诗学理论历史流变的呈现。历史流变并非《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但这一铺垫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对历史流变进行考察,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对理论在历史中的接受情况进行考察,这种接受有时会涉及翻译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影响一般而言是通过各语种的译本产生的。在法国同样如此,从17世纪第一个法译本问世至今已涌现多个法译本,不同译本对亚里士多德关键概念的翻译不尽相同。《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尤其对一部特殊的译著——杜邦洛克、拉洛两位法国古典学者于1980年在“诗学”丛书中出版的重译本《诗学》进行了考察,在译者对核心概念的翻译与阐释中呈现了重译本《诗学》与当代法国诗学走向之间的相互影响。再如谈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就无法忽略托多罗夫编译的形式主义文论《文学理论》,可以说如果没有托多罗夫的译介活动,就不一定会有之后结构主义诗学的诞生。
这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克服“望文生义”的毛病。的确,只有搞清楚理论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理论的真正内涵,把握其针对性,评价其价值与功效。历史的、比较的视野可能是受到了研究对象的影响,正如曹丹红所言,近年来,“诗学与历史的边界也越来越呈现多孔隙的特征”,一种历史的诗学观逐渐确立,令21世纪的诗学研究区别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诗学研究。在我看来,这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也得益于作者在硕博士阶段所受的翻译与译介研究的训练,由于充分意识到语言转变、语境转换可能带来的异质性因素及其影响,作者在理论研究中多了一份审慎,这也赋予《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的撰写一种反思维度。
总而言之,《当代法国诗学研究》是一部具有系统性、探索性、开创性和反思性的理论研究著作,期待这部著作的出版填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引发学界的关注与争鸣,共同推动国内外文学批评实践,助推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的发展。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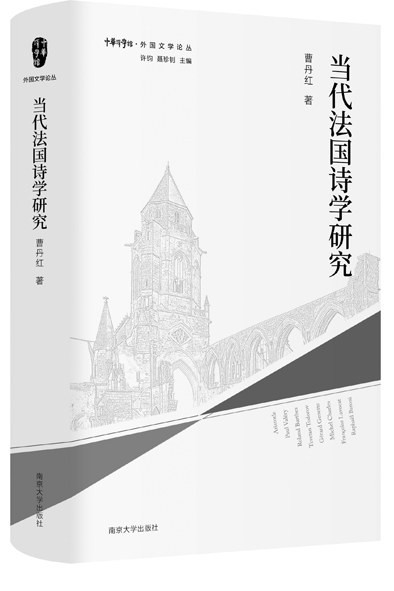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