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
在一些和技术史有关的学术圈子里,芒福德(Lewis Mumford)名头颇大,他的这本近百年前的旧著得以新版,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笔者初识芒福德,还是在《自然辩证法概论》那本指定教参中。书里提到,芒福德对巨技术、人为规划的巨型城市怀有恐惧,主张规模适度、与自然和社区保持平衡的“有机城市”,引起我很大共鸣。亲历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的大拆大建,我对当代“一线城市”的孩子深表同情——他们根本无从想象,我小时候的城市生活是如何“有机”。这些思想,据说主要体现在1960年代芒福德的后期思想中。但在这部《技术与文明》(初版于1934年)中也有端倪。
从历史到哲学:一部巨著的二元结构
这的确是一部巨著。李约瑟尝言,再好的学术著作,为顾及读者体验,也不应超出“能躺在浴缸里舒适阅读”的厚度——但他自己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没有任何一册符合这个标准。
首先须指出,本书诞生于一个特殊时期——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它所引起的社会痛苦,伴随的种种野蛮行径和法西斯的抬头,无疑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一个“至暗时刻”。因而书中所谓“现在”皆指约一个世纪前;且正如《大转型》的作者波兰尼,身处那个时期必然会对19世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抱更负面的看法——两者甚至不约而同主要归咎于机器。
论性质,本书既是技术史经典,也是技术哲学经典。这在章节结构中体现得泾渭分明:三百多页的前五章是技术史,基本按时间顺序;第六到八章约两百页是技术哲学分析及结论;最后附有从10世纪到1933年的“发明清单”——这里的“发明”,也包括科学发现与制度创新。本文着重技术史部分——脱离年代框架的哲学分析于我很是隔膜,只能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品味了。但作者的主要结论或解决方案应呈现出来,即“基本共产主义”——普遍分配基本生活资料的制度。
三个技术时代:从田园牧歌到堕落和悔过
作者将近千年来“机器文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始技术(现代技术的黎明)、古技术(以煤铁和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新技术。
作者对“始技术时代”的描述,特别有助于澄清一些流传甚广的“认知偏差”,如过度强调蒸汽机和煤炭在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扩散中的作用。
“若说工业不久前才获得动力,就是忘记了倾泻而下的水和呼啸而过的空气产生的动能”:水车、风车和风帆,才是近代欧洲上升时期大部分时段的主要动力源。作者极力赞美机器文明的这个时期:1448年,维也纳一半的房屋都有玻璃窗;15世纪,眼镜已相当普及;第一次工业展览会1569年在纽伦堡市政厅举办;16世纪出现了机械针织长筒袜、内衣、轻便可洗的棉织紧身衣等弹性贴身衣物(常被误以为是几个世纪后的发明);17世纪(我国明清鼎革之际),为供应大规模航海所需,荷兰建立了生产压缩饼干的大型工厂——中欧与西欧的“工业化”实远早于工业革命。
甚至到富兰克林时代才变得普遍的“靠个人(尤其技术发明方面)才华发家致富、跻身权贵之列”(好听的讲法是“自我实现”)的美国梦,也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样可追溯到这个“始技术时期”(约相当于我国明代)。达·芬奇在笔记中写道,“明天一早,1496年1月2日,我将做出皮带,并进行测试……每小时做400根针,乘以100就是每小时4万根……假如生产400万根针,每1000根卖5索里第,那就是2万索里第。每个工作日1000里拉。如果一个月共做20天,一年就是6万达克特。”——这笔钱约等于中等意大利邦国的岁入,也足以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雇佣军或商船队一整年。
除以上工业成就和下个时代才变得普遍且趋极端的“工业心态”,在这个田园牧歌般的第一时期,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的“异化”还不严重,因而比之前、之后的时代都更接近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发展。作者用诗意的笔触总结道:
始技术文明直到18世纪进入衰退之前,其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地获得更大的力量,而是要更痛快地享受生活……美好的形象比比皆是:田野里怒放的郁金香……丝绸衣服下肉体的起伏或少女乳房的弧度……重复的菜肴变成了一整套程式,从刺激唾液分泌的开胃菜到标志吃饱喝足的甜食……触觉也更加精致:……印度的最轻薄的达卡细布……精致光滑的中国瓷器……花园里的花卉提高了视觉和嗅觉的敏感度……卡斯泰尔神父甚至提出了制造气味羽管键琴……人们不会用肮脏油腻的手去触摸书籍或其他印刷品……就连厨房里过去粗糙的铁锅也换成了铜锅铜盆,被……擦拭得能照出人影……饮酒人啜饮杯中酒之前,先凝神注视酒的颜色。看到恋人的愉悦暂时淡化了占有的欲望,恋爱因此越发热烈悠长……人无论贫富,都明白并努力培育玩乐的精神。工作的信条即使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也不占支配地位。
与之形成令人绝望的对照的,是“进步”的(对英国而言)19世纪的景象:“干线的快车服务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的集中,而支线和乡村地区的铁路服务则逐渐破败、消亡或被故意取消。从乡村的某个地区旅行到另一个地区,经常要先到一个中心城镇,再往回走,像是走之字形。旅行距离是实际距离的两倍。”——这解开了我多年的困惑:为何从剑桥坐火车去牛津要绕远路经过伦敦。
“帕特里克·格迪斯把这种纯粹的物理人口聚集称为复合城市……仅仅是因为建筑物和人口的聚集而看似城市社会。”(预示了芒福德的后期城市思想)
“铁和煤是古技术时期的主宰。目之所及尽是它们的灰黑颜色:黑色的靴子、黑色的烟囱帽、黑色的客车或马车……无论……原来是什么颜色,都很快被古技术活动产生的烟灰和煤渣染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灰色、暗褐色和黑色。……铁无处不在。人们睡在铁床上,早晨用铁脸盆洗脸……乘坐铁路机车在铁轨上驶向城市,过了铁桥后到达铁皮屋顶的火车站。”
“受战争滋养的军工产业因修建铁路和过去的战争而产能过剩,四处寻找新的市场……兢兢业业地为股东服务,在世界各地煽动国与国之间的恐惧和竞争。美国钢铁制造商破坏了1927年的国际军备大会。”
“煤的呛鼻气味是新工业主义的熏香。工业区如果出现蓝天,说明发生了罢工、停工或工业萧条……工厂所到之处,河水发臭有毒……既不能饮用,也不能在里面游泳”——联想到本世纪初上海的苏州河重又变清,明确标志着江南地区脱离了古技术时代。
“为了谋利,铁工厂厂主和纺织厂厂主几乎和工人一样拼命。他们和工人一样处处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只不过工人是迫不得已,他们却是出于贪婪和权力欲……不仅不让他们的工资奴隶享受人道生活,也几乎同样坚决地剥夺自己的人道生活。”
“裸体……被谨慎地禁止,就连裸体的雕像也不准。道德家将裸体视为诲淫,认为它会让人忘记工作,损害机械工业的系统性禁制。性没有工业价值。理想的古技术人物连腿都没有,遑论……”
最后,作者有力地嘲讽了19世纪开始占压倒性优势的、对“进步”的迷信:
事实上,13世纪的城市比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城镇更明亮、更清洁、更有序;中世纪的医院比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医院更宽敞、更卫生;在欧洲许多地方,中世纪工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古技术时期被绑在半自动机器上做苦工的工人……如果用高点作为参考,例如16世纪的德意志矿工经常三班倒,每班只工作8小时,然后再看看19世纪的矿山,就知道没有任何进步。
至于芒福德所说的第三个时代——新技术时代,它在本书写作时尚在襁褓之中;读者或许能比作者看得更清楚,故此处不再赘述。
些许“过时”之处
由于本书的写作年代和作者的视角关系,书中少数内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有“时过境迁”之感。在这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国家与“去工业化”国家之间,正是前者重拾起后者已不再崇信的“机器宗教”(“发明的必要性是一种教条”),引起一种错位感:
上个月英国刚开始推广一周四天工作制,而笔者某日就着新闻吃早点时发现,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尤其被马云当年有些不合时宜地推崇的“996”一词已火遍全球、进入英语,本地新闻里也能读到这词——显然18至20世纪盛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工作的信条”,如今几乎只无缝衔接式地存在于中国。
但全球北方(主要位于欧亚大陆和北美的工业国)总依相似的节奏从工业化滑向后工业化,从本地出生人口正增长转向负增长——这不,近两年在中国“反内卷”的呼声也起来了;而几乎就在英国推广四天工作制的同一个月,中国推出了欢迎全球年轻科学技术人才的K签证。
总体来说,本书瑕不掩瑜,还是很值得通读、深思的,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以下试举一二。
作者将军事作为(机器)工业之先驱,学理上大体也能成立:“制服就是这样的象征与徽章,在17世纪首次被大规模使用……操练使士兵行动如一,纪律使士兵反应如一,制服使士兵外观如一。军容风纪成为新的团队精神的重要内容”。今年纪念二战结束大阅兵所体现的饱满精神状态,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高潮的事实相协调。著名自媒体人“美版曹操”将之归因于中国自古由治水而养成的“秩序优先”文化,却严重失焦了——他可能在中国生活得太久,忘记了在近代恰恰是欧洲率先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同时期处于“帝制晚期”(明清)中国之散漫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桑巴特“中肯地指出”,亚当·斯密本该用武器制造而非大头针制造作为“专业化和集中生产所带来的节约”的例子,但我认为斯密的选择更为明智。无论机器和工业有多么难以撇清的军事起源,技术上的“进步”一旦发生和持续,就有了独立的生命。
建构理论时,让人们“下意识地”先想到可能满足人类各种和平需求的商业应用,这不是比反复暗示它们曾被主要用于、将来仍可用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各国各族统治者之间是零和游戏,对各国百姓而言是负和游戏——在道德上更可取吗?《易·观》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之谓也。学术并不总是价值中立的;只要有可能,就应选择“教化”而非“教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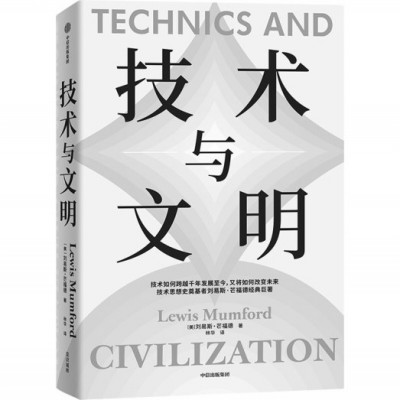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