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
翻译家杨必(1922—1968),无锡人,排行第八,杨绛先生的小妹。姐妹情深,杨绛作有散文名篇《记杨必》。正是此文述及杨必生于上海,长于苏州。关于杨必的童年,苏州学人黄恽有所发现。他在《燕居道古·杨绛的小妹》(2014年出版)中,提及1934年4月4日(民国时期儿童节)《苏州明报·儿童节特刊》中有关杨必的介绍:
杨必,年十二岁,江苏无锡人。六岁入本校(苏女师小)幼稚园,后来因为距离住的地方太远,便转学到城西小学。隔了二年,再入本校。现在是六年级上期。在一级中,她的年纪最小,但是无论哪一种功课,成绩都很优异,而且聪颖异常,过目不忘。去年全校举行作文竞赛,获得冠军。先生、同学,没有一个不称赞她的好学。杨君不特品学俱优,而且擅长演说,更富于办事能力。因此,本学期,便由全校公举她为小仓市市长。
这一年,杨必正在苏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六年级。黄先生还提及报上有一张杨必的照片,只是模糊了。笔者近日查阅1934年第3卷第2、3合期《吴县教育·各校优良儿童》,发现此刊不仅刊出了上述杨必的简介及清晰的照片,而且还有一篇杨必的习作,题目正是《庆祝儿童节》(作者署名:苏女师小六上 杨必),原文如下:
这几天来,各个同学脸上都笑嘻嘻的,我当然也是很快乐。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三月三十日,我校预祝儿童节。往常,家里过端阳节啦、中秋节啦——都很快活!现在有了儿童节,“我们的节”,岂不是更兴奋吗? 这的确可以鼓起我们的兴趣,且可以启发我们爱国爱家爱群的心理哩!
在外国,他们当然也有儿童节,如英国、美国、日本……等,也都有。而且日本还分成男童节和女童节,他们还注意儿童的健康,所以在儿童节还举行婴孩的健康比赛,这是我们小孩的顶快活的一日。
说来惭愧!中国的小孩,都是弱不胜衣,不能同外国去比。我想:如果我们把身体锻炼特强了,比别国的儿童还要强。那么,以后的儿童节,岂不更快乐吗?
杨必早逝。世人熟知的除去两部译著《剥削世家》《名利场》,还有一篇散文《光》,刊于1944年第4卷第6期《万象》。这篇作品写于1934年,那年杨必才12岁。尽管这肯定不是她最早的一篇作文,却是世人目前所知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杨必不愧是“昔日作文竞赛的冠军”。这篇作文围绕儿童节快乐的缘由,一气呵成,语言通俗,充满童真,又不失深度。她在文中对待外国孩子的态度不亢不卑,彰显爱国的情怀与爱家的情感,令人难忘。
《庆祝儿童节》是杨必小学毕业年的作品。杨绛《记杨必》及黄恽《杨绛的小妹》只记:杨必是在苏州读完初中,才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的。那么她读的哪家初中呢? 很有可能是苏州英华女中(今苏州十六中)。英华女中成立英华女学校英华校刊社,编印中英文年刊《英华》。这本年刊不仅刊载时事评论、读书心得,而且辟有文艺、游记与杂俎等栏目,选刊学生优秀习作。目前笔者仅见1936年第6期《英华》。此期《英华》刊有两篇杨必的作品,作者署名中均有“中二上”。从《英华》的创办地点到杨必的就学班级,显然作文的作者就是从苏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毕业的杨必。
两篇作文,其中一篇又是写的儿童节,名为《儿童节感想》:
儿童节到了,照例是很热闹的,日里有庆祝会、讲演、表演、茶点,夜里还有提灯会,每个儿童的小心灵中,充满着快乐。这个为他们特设的“节”,给予他们最大的欢欣,新衣、新帽、糖果,给予他们极大的满足,这一年一度的难得的儿童节,哪个儿童不欢迎呢?
在这喜气洋溢的儿童节,谁曾想到在这一班幸福的儿童以外,尚有无数少衣缺食在痛苦中过活的儿童,他们没有穿戴新衣帽和尝糖果滋味的福气,他们只好穿破衣、嚼草根,这种苦乐的分配,未免太不平等了。
能享到幸福的儿童,恐怕几千个中间才有一个吧?
在江南富庶的区域内的儿童,如果看到苦恼的小同胞,恐怕觉着穿着绸衣好像是粗布,嚼着美味的糖果好像嚼蜡吧?
相比小学时期的习作《庆祝儿童节》,身为初中生的杨必心中已有大爱,不再关注儿童的健康问题,而是通过儿童生活的观察,考虑到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她是一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初中生。同样另一篇习作《储财不如储学说》,也能反映出杨必具有很强的思考能力:
金钱是物质上最宝贵的东西,吃的,用的,只要有钱,什么不得?金钱真是万能呀! 但是,有钱的哥儿小姐们,却是被金钱害 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有钱,要什么学问?还怕将来养不活自己吗?金钱诚然是好的,但是被强盗偷了怎样?被贼偷了怎样?存生银行里,银行倒了又怎样?由此,我们知道,金钱是空虚的,单有金钱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什么才是实际的?只有学问,学问藏在脑子里,不会被强盗抢去,也不会被偷掉,有了学问才能随心所欲,敌人有飞机大炮死光……我们可以发明更利的战器,别人医学发达,我们可以制造更有用的药品,中国人的脑子不会比外国人轻,不会藏不下学问,我们不应该求目前物质上的舒适,把学问置于脑后,应该想到日后的幸福,乘有机会求学的时候,多多地把学问储起来。
这虽然是一篇中学时期的习作,但是文中爱才(尊重知识)的信念却是杨必一生坚守的。她写散文,译名作,教学生,无不是学习、传播知识的结果。尤其是在译著方面,杨必成绩斐然,这就不得不说说她的第一本译著《剥削世家》。
早年,笔者负笈奥克兰大学时,去惠灵顿游玩,在Foxton(狐狸镇)的海滨木屋借住数日,屋主是梅西大学的一位高级讲师。他早年师从王佐良和许国璋等英文名家专攻英语,后长期在海外高校从事中英文翻译的教学工作。在海边散步时,屋主和我畅谈起了中国的翻译家。他诚恳地提到:“作家的译著往往靠不住,虽然他们有名气,但不少作家的外语水平其实有限,反而有些名气不大的翻译家的译著才是忠实原著的翻译。”最终,他极力向我推荐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屋主的话,我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回到奥克兰后,我急忙上网浏览。网上不乏有关《名利场》的文章,相比杨必的第一本译著《剥削世家》,知者较少,却值得细述。
《剥削世家》是爱尔兰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1767-1849)的名著,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据研究《剥削世家》的专家George Watson的介绍,此著是“第一部英文地域小说(regional novel)”。数家中文网站称《剥削世家》是埃杰窝斯的处女作,其实不然。在《剥削世家》之前,埃杰窝斯已经出版了三部著作,譬如儿童故事集《父母亲的帮手》(1796年初版)。《剥削世家》以来客仑脱城堡为中心讲述了爱尔兰来客仑脱家族的故事。此书于1800年由J. Johnson公司初版发行,是著者的第一部小说,短小精悍,颇为畅销,同年又出了第2版。此后多家英国知名出版社重印此书。如Macmillan and Co 公司的1895年初版(多次重版)和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社)的1964年版本等等。杨译《剥削世家》由平明出版社于1953年初版发行,属“文学译林”丛书,永立印刷所印刷,定价4200元,仅印5000册。除了此版,笔者还购得一本作家出版社于1955年第1版的《剥削世家》,实为平明版的翻印本,印量更少,4500册。
译书难,译书名更难。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译好书名就如同拥有一个好的“开局”,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陈丽女士在其研究专著《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中写道:“杨必先生早在1953年就将该书译成中文,并将书名改为《剥削世家》。”我基本上同意“改名”一说,而且觉得“改”得应该,“改”得精妙。首先,杨必本人在《剥削世家“小引”》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原名《来客仑脱堡》”,可见译者主动声明了自己没有直译书名。其次,《剥削世家》的英文原名是Castle Rackrent。Castle意为“城堡”。在西方,城堡往往是古老家族(世家)的象征或标志。如英语中有句俗语:My home,My castle,其意就是“我的家,我的城堡”。而且城堡在西人脑中是非常熟悉的影像,不过国人相对陌生。相比“西方的城堡”,对于深受传统家族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世家”一词,自然显得更为亲近。rackrent“高额租金”之意,rack一词有“烤架、拷问架及折磨”的意思,rent就是租金。因此将两词合成,“烤出来的租金”,引申为“剥削”,未尝不可。而且中文书名直接一针见血地表明了全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来客仑脱家族可耻的剥削行为。书名《剥削世家》不仅译得传神达意,而且拉近了这部西方小说和中国读者的距离,实在是难得。不过陈女士称“杨必先生将书名改为《剥削世家》”有待商榷。据杨绛先生的回忆,杨必当年在傅雷家中做家教,傅先生鼓励杨必译书。钱锺书先生为杨必“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可见,书名《剥削世家》很有可能出自钱锺书之手。
《剥削世家》的译文和书名一样译得精彩。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通过来克仑脱家的一位老仆人的讲述将故事情节一一展开。杨必的译文,不但原汁原味地展现出了英文文本的真实性和趣味性,而且清新流畅,一气呵成。《剥削世家》读来看似语言平淡,实则从选词到句子结构,译者均有精心选择。笔者读后,颇感“爱不释手”。比如巴脱力克爵士死前曾经唱过的歌曲,我曾特意去读过原文,再对比杨必的译文,确实译得很有水准。“清早起,到上床,滴酒不喝,倒下去不过像十月里枯落的树叶;清早起,到上床,酒气醺醺,活得才不冤枉,死也算个好人”,准确通达的译文将爵士醉生梦死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给了中文读者。
初次阅读英文《剥削世家》是在网上,我无意发现了此书有篇英文《序言》,表现出了埃杰窝斯对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延续,持有乐观态度,如《序言》的结尾是“当爱尔兰由于被英国统一而丧失其民族特性的时侯,回眸生活在往昔的 Kits 爵士 和Condys爵士这样的人物,她会发出愉快又自满的微笑”。1800年,英国和爱尔兰签订同盟条约,爱尔兰彻底成为英国的领土。同年,《剥削世家》出版,《序言》尾句的意义深远。不过我的两本中文本里根本没有《序言》。难道是杨必漏译了吗? 我初始以为网上那篇《序言》也许老英文版本中没有,因此杨必当时没读到此序。我为此去了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先后查阅了1800年的初版和再版(均是电子版),以及1910年和1964年重印的英文版《剥削世家》。四本书中全印有此篇《序言》。仔细的译者译书,通常会找来几种版本的母本,以便互相参阅,因此杨必应该看过《序文》。为什么她没有翻译呢? 当年与翻译《剥削世家》有关的杨必女士、钱锺书和傅雷先生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也许只有在世的杨绛先生才知道其中的答案。
多年前,关于《剥削世家》的中文译本还出过一段有趣的“文坛公案”。1992年3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一封杨绛先生的来信,主要内容如下:“1992年2月 22日贵报载吴德铎先生《也谈傅雷误译》一文,提及我与杨必,想是误传。杨必译《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一语,缺乏事实根据。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她有疑难便来信向我们询问。”钱杨伉俪在当代中国学界和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杨先生的追忆本不容置疑。但是数年后,《傅雷文集》(傅敏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有傅雷先生写给友人宋淇的亲笔信:“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若要为“译文略为润色”寻找一个注脚,不妨看下周立民先生《傅雷致巴金四封书简浅疏》:傅雷不仅将杨必的译稿推介给负责平明出版社编辑工作的巴金先生,还于信中告知巴金:译稿“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红笔批注均出弟笔,冒昧处乞鉴谅为幸”。《剥削世家》从译文到出版,傅雷都是出过力的。钱先生认为,回忆是靠不住的。但傅雷先生的那两份信写于1953年初,同年《剥削世家》由平明出版社初版,两年后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对于杨先生的说法也不必太在意,相信杨先生本意不是去否定傅先生的“功绩”,毕竟是多年前的往事。
杨必很早离世,命运多舛。我们脑海中的杨必女士是“可爱的”,因为她高超的英文水准和特殊的亲友关系,钱氏夫妇和傅雷三位译林高手才会为翻译《剥削世家》做出贡献,我们才有幸读到一本不可多得的翻译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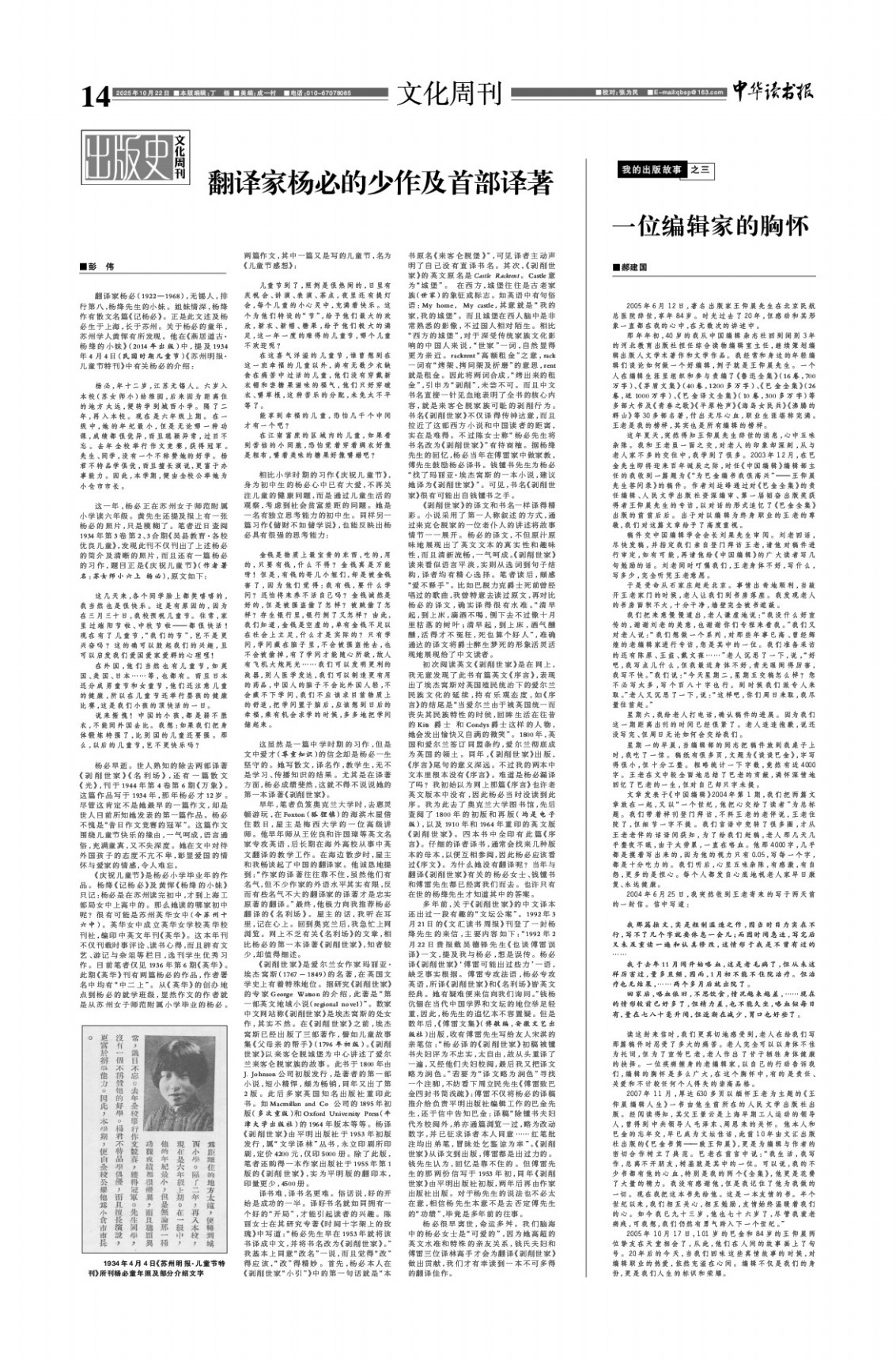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