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智
近年来,地域学术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成果亦层出不穷,而在众多的地域学术研究中,关学研究则是较为特殊的一脉,原因在于其他地域学派往往侧重于文化,而关学展示的更多是思想(陈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学的研究就更加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众所周知,关学是理学初创期至为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与其他学术流派一起成为理学的共同创建者。自《关学文库》2015年出版以来,关学研究开始步入快速道,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皆前所未及。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教授的新著《关学〈中庸〉学研究》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该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论证细密、逻辑严谨,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关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关学建构的经典依据。
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依经立言”式的,也就是学者思想的建构多是借助于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展开的。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关学也不例外,它尤其是借助《周易》和“四书”这五本经典来建构的。《宋史》就说张载的学术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也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论》《孟》之要归也。”这是合乎实际的。然细究起来,这五本经典在张载关学的体系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也正是因此,学界一直就有对张载之学到底是易学还是“四书”学的争论,部分学者的研究则更加细密,如钱穆指出张载思想还是“得力于《易》和《中庸》”。晚清关学大儒贺瑞麟则说“张子得力于《中庸》”。我认为,从张载先著《横渠易说》的历史事实以及《正蒙》中有诸多与《易说》重复的内容看,古人关于张载“以易为宗”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不过,古人也说张载“以《中庸》为体”,从他建构的“性与天道为一”的思想体系来看,《易》和《中庸》在关学思想体系建构中确实处于核心的、纲要的地位,二者都应受到重视。《关学〈中庸〉学研究》则通过选取关学历史上近20位典范学者,详细梳理文献史料,细密详实地给予论证,从一个侧面将这些学者的共识加以细化和充实,进一步印证了《中庸》在关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就较以往的笼统性表述更加可信和翔实,从而明晰地考察了关学的经典建构依据,这对于推进和深化关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凸显了《中庸》学研究的关学贡献。
陈来先生曾指出:“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此论言之有理。这就告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儒学,在关注它的普遍性的同时,必须不能忽视其地域性,因为地域性传统是中国哲学的固有且强势的传统。就当前学界对《中庸》学史的研究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聚焦在整体的《中庸》学史研究或断代的《中庸》学史研究,很少有从地域学派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就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域学派在《中庸》诠释学史上的贡献,不免有遗珠之憾,也有违中国哲学地域性传统的这一特质。《关学〈中庸〉学研究》正是有鉴于此进行创作的,它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漏之处,展示了关学在《中庸》学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如关学推进《中庸》学术地位的上升、着意发展义理型态的《中庸》学、凸显和强化“追验-经世”的《中庸》学诠释方法、彰显和落实《中庸》所蕴含的礼学精神等,这些贡献极大地推进和深化了《中庸》学的研究,在尽可能的方向上打开了《中庸》的诠释角度,发展面向。更为重要的是,关学在《中庸》学的这些独特贡献被作为《中庸》学的普遍内涵所接受,不再只是关学所独有的。因此,贺瑞麟以“道法《中庸》”来作为关学的学术宗旨和特质也就不难理解。敬峰教授的著作极有洞见地抓住这一点,以此可见该著不俗的学术价值。
三是丰富了关学的经学研究。经学与哲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的关系,如顾炎武就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冯友兰更为明晰地指出:“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这就反映了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经学研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制度化的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经趋于瓦解,但经学研究则依然在继续着,并一直持续存在。近些年,关学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主要聚焦在典范个案如张载、吕大临、吕柟、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贺瑞麟等,而作为关学重要侧面的经学,则囿于文献、视角等原因,学界研究相对薄弱,仅有的研究成果亦主要局限在易学、礼学等方面,关学丰富、多元的经学面向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难以真正揭示关学的生成历程。作者这些年一直深耕关学经学领域,先是聚焦关学“四书”学领域,尔后又具体入微地关注关学的《中庸》学,这就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憾,丰富了关学的经学视域,也相应地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带动和深化关学其它经学领域的研究,如《论语》学、《孟子》学、《春秋》学等,因此,敬峰教授的《关学〈四书〉学研究》《关学〉学研究》所起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是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的。
总之,《关学〈中庸〉学研究》的价值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点,但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关学的研究维度。当然,是书也存在对典范个案的比较还不充分、对不同时期学者之间思想的承继与变异的考察仍需进一步加强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无疑是近些年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关学,从而从一个重要维度深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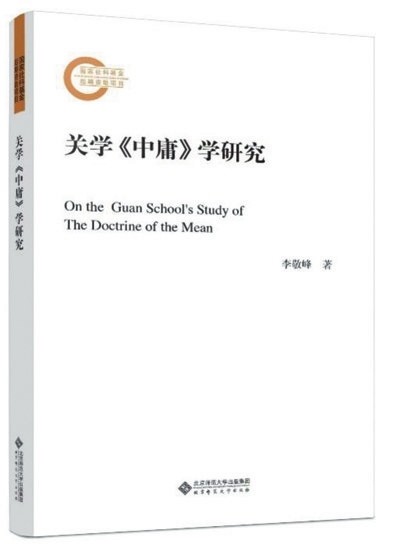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