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白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政府启动一项代号为“回形针行动”的秘密计划,系统性掠夺纳粹德国在军事科技和生化领域的研发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诞生于对集中营奴隶的残酷役使乃至罪恶的人体实验。更惊人的是,美国不仅掠夺纳粹研发成果,同时也掠夺了1600余名纳粹科学家,其中不少人背负战争罪指控,甚至是集中营医学屠杀的主谋。
在《科技掠夺行动》中,美国记者安妮·雅各布森以详尽史料揭开这段历史秘辛:众多曾为纳粹德国效命的科学家,在战后跻身美国航天、生物医学等核心领域,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美国战后的科技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这些背负道德污点的专业人才。在“民主灯塔”神话早已破灭的当下,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以确凿的证据,揭露美国科技宣传中长期被回避的问题:正如其早期财富积累来自于殖民掠夺,美国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则伴随着掠夺以及对伦理道德底线的悍然践踏。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
本书披露的诸多历史相片中,奥托·安布罗斯在审判法庭上轻松大笑的画面,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他是希特勒绝密武器——塔崩毒剂的主要发明者。
塔崩属于有机磷酸酯类化合物,与杀虫剂同属一类,却是致命的神经毒剂。其毒性超过芥子气五倍,只需一小滴沾染皮肤,30秒内即可致人死亡。中毒者临终前会剧烈抽搐,如同被杀虫剂喷洒的蚂蚁般痛苦挣扎。作为希特勒严守的最高机密,塔崩凭借极强的挥发性和皮肤渗透性,能够轻易突破当时所有的防护面具。
1942年起,安布罗斯管理的工厂开始利用集中营俘虏生产塔崩。这些劳工不仅承担繁重劳作,更被强制参与生化实验:如佩戴防毒面具后遭塔崩喷射以测试防护效果。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德军储备了大量塔崩炸弹,但直至1945年战争落幕,始终未在战场上动用这一武器。究竟是希特勒人性未泯,还是因战局溃败过速而无暇部署? 这一矛盾现象终成历史未解之谜。
1945年,盟军在兰布卡麦尔森林附近的地堡中发现了这种物质。美军第45实验公司的化学家以野兔进行试验,测试出该物质的巨大毒性,众人无不骇然。而此时的生产工厂早已被清空,所有文件、证据也被尽数销毁。
当盟军找到安布罗斯时,他自称是“一名普通的化学家”,并将法本公司工厂伪装成生产肥皂与洗涤剂的场所。他不仅向风尘仆仆的美军士兵赠送免费肥皂,还提供强力清洁剂用于洗刷装甲坦克上的泥浆,其“殷勤”表现一度迷惑了前线部队。面对讯问,他指着剃着光头、瘦骨嶙峋的劳工谎称他们是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自己则“好心”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岗位,绝口不提这些人实为集中营幸存者。
正是这样一位残忍狡诈、无可辩驳的战争罪犯,在纽伦堡审判定罪后,竟仅服刑了不到18个月,就以“技术合作需要”为由被提前释放。获释后,安布罗斯受雇于美国能源部以及化工巨头格雷斯公司,而后又转型为富商大贾,成为多家巨头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本书作者安妮·雅各布森还揭露,有资料显示安布罗斯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沙利度胺”事件存在关联——这种曾被宣称对孕妇绝对安全的止吐药,最终导致一万多名胎儿严重畸形,而它很可能是安布罗斯当年为纳粹研制神经毒气时开发的相关产物之一。
同为塔崩毒剂发明者的施贝尔,比安布罗斯更早获得美方豁免,冷战时期他在海德堡为美军主导沙林毒气的改良研发。这些曾经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罪犯,凭借技术专长从纽伦堡的被告席走向美国科技体系的贵宾席,从阶下囚摇身变为座上宾。
从虐杀者到迪士尼明星
德国V-2火箭发明者冯·布劳恩在战后为美国科技服务的历程,无疑是“回形针行动”中更为人熟知的典型案例。这一案例被安妮·雅各布森详细挖掘,贯穿叙事始终。
本书开头即呈现这样的场景:贵族出身的天才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正准备接受希特勒授予的“战时服役骑士十字勋章”——这是纳粹德国给予非战斗人员的最高荣誉。而这枚勋章的荣光,是集中营劳工用尸骨堆砌的。
作为德国V系列武器的核心组装基地,冯·布劳恩的工厂从建立之初就推行“不计人力损耗”的强迫劳役制度。开工仅6个月,就有近3000名俘虏因超强度劳作致死——他们每周7天、每日12小时在隧道中组装火箭,瘦骨嶙峋的躯体常被沉重零件压垮,动作稍缓就遭毒打丧命,而死者很快被新的俘虏取代,“从隧道里运出的只有火箭和尸体”。由于V-2项目属于最高机密,使用苦役劳工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其封闭性——这些俘虏被断绝对外通讯,从进入工厂起就注定在劳动中耗尽生命。
恶劣环境下的组装质量难以保障,部分火箭在发射台发生意外爆炸,德军将其归咎于“蓄意破坏”。仅某一天,就有57名俘虏被绞死,尸体在生产线上悬挂示众达24小时。而当冯·布劳恩被盟军俘虏时,这位战犯毫无忏悔之意,反而以“社会名流”的姿态周旋:据情报人员回忆,他主动与美军士兵合影,时而微笑寒暄,时而指着对方勋章攀谈,对德国战败的事实与战争责任只字不提。多年后他曾对美国记者坦言,当时确信自己不会被冷遇,因为“我们掌握着V-2技术,而你们没有”。
布劳恩抵达美国后,凭借V-2火箭技术积累,迅速成为美国空间技术领域的灵魂人物。1950年起,他先为陆军研制“朱庇特”弹道导弹,后执掌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担任土星5号运载火箭首席设计师。在“阿波罗计划”中,正是这款高110.6米、起飞重量3038吨的巨型火箭,将阿姆斯特朗等宇航员送入太空。阿波罗计划的成功让冯·布劳恩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于1970年被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勋章”。
如果说来自科技领域和世俗方面的嘉奖尚在情理之中,那么他在童话世界受到的追捧,则多少显得讽刺。凭借在“太空旅行”概念推广上的影响力,冯·布劳恩接到迪士尼公司的邀约,合作制作一系列关于太空探索的电视片。他签署了合同,担任三部迪士尼电视剧的技术顾问。其中,1955年播出的《人与月》特别节目吸引了4200万名观众,创下当时美国电视节目收视率第二的纪录。荧幕上的布劳恩身着灰色双排钮扣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讲解太空知识时语调温和,又充满奇思妙想。这一温文尔雅的火箭科学家形象,通过迪士尼的强大传播力深入人心,居然成为无数美国儿童的童年梦想之一。
尽管布劳恩已成功重塑形象,但他的纳粹过往仍未被所有人遗忘。美国歌手汤姆·莱勒曾专门创作歌曲揶揄此事,歌曰:“只要火箭飞上天,管它落到哪一边? 这个哪关我的事,冯·布劳恩耸耸肩。”
科学家享受掌声,政治家承担骂名?
尽管美国政府极力为“回形针行动”披上正当性外衣,向公众宣称:那些曾为纳粹效力的科学家已处于严格监管之下,他们并非极端分子,而是纯粹的“科技爱好者”。但这一行动仍遭到诸多民众抵制,其中就包括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尖锐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存在潜在危险。他们在德国曾身居要职,或为纳粹党员,或为坚定支持者,这一事实让我们必须审慎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核物理学家汉斯·贝蒂更发出灵魂拷问:“美国参战的初衷,难道是为了让纳粹思想渗透进教育与科研体系? 难道要为了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面对这些正义的责问,美国政府不仅置若罔闻,更在1950年后启动“回形针加速计划”,将更多身陷囹圄的纳粹科学家纳入麾下。这一荒诞操作催生出美国民间的黑色幽默:“如果你喜欢大屠杀,又要全身而退,那就去做个科学家吧。孩子,如今这可是逃脱杀人罪名的唯一途径。”
在冷战技术争霸的逻辑下,似乎只要成为掌握尖端科技的科学家,且这些技术对美国发展有利,就能获得“特权”,其战争罪行因技术价值被豁免。
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所谓的“特权”绝非是对科学家的尊重。“权责对等”是社会运行的规则之一。例如,仅对未成年人实施有限度的责任豁免,这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自主能力。美国对待这些纳粹科学家,与其说将其视为战争罪犯,不如说是视为德国战争赔偿的特殊“战利品”。他们的思想、政治主张、战争罪责被漠视,仅剩“技术价值”被利用。其表面享受的“特权”,实质上正是科学家群体的“失权”。
科学家享受掌声,政治家承担骂名。2023年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二战胜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意单独会见奥本海默——这位为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原子弹之父”,询问他成为世界著名人物的感觉如何? 言辞中有嘉奖之意。而奥本海默正沉浸于原子弹爆炸在日本造成的深重灾难中不能自拔。他对杜鲁门说,感觉自己双手沾满鲜血,为制造原子弹感到自责,并提议关闭美国生产原子弹的工厂。杜鲁门嗤之以鼻说:广岛或长崎的人只关心原子弹是谁下令投的,而不是谁造的(意思是说:要承担罪责也轮不到你)。两人会谈不欢而散,杜鲁门还不悦地告诉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以后不要带这个哭包来见我。”
这段情节深刻揭示出美国政客对科学家的一贯态度:在权力逻辑里,科学家不过是技术的延伸载体,他们被允许用专业能力服务于政治目标,却不配拥有独立的道德判断,更不该提出与政治意志相悖的主张。当奥本海默试图对科技后果反思时,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来自权力阶层的反感与排斥。而奥本海默后期的挣扎更在于,他不满足于只享受掌声和鲜花,还试图进行道德反省。
20世纪以来,无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民族的科学家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功成名就,收获鲜花、掌声、勋章、地位,他们唯独得不到的,是对于基本人权的尊重。1950年前后,当纳粹科学家靠“回形针行动”正在美国风生水起之时,钱学森这位曾为美国二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功勋科学家,却被吊销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离开最为先进的航天技术领域,更被限制“不得离开美国”,遭受长达五年的人身监视;爱因斯坦通不过曼哈顿工程的政审,还常年遭到24小时监控,美国移民局甚至联合FBI搜集证据,试图撤销其公民身份并将他驱逐出境。
功勋科学家与纳粹战犯的境遇反差,构成历史最尖锐的反讽。掌声与勋章,不过是奖励顺从者的糖衣;而那些秉持良知的科学家,只会被视为失灵的零件。所谓“科学圣地”的光环,也遮掩不了美国科技发展中的阴暗一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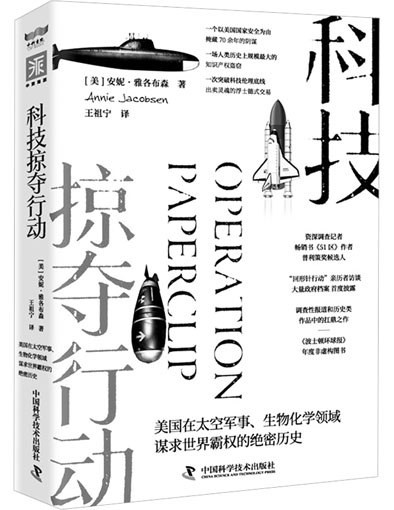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