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水环绕苏州城。水中之船如过江之鲫,一艘连着一艘。船行过,岸边桂花瑟瑟而落,而鸟们安然不动,因为它们早就习惯了行船之声、水波在船舷边的激荡之声。
阊门外太子码头、万人码头、山塘街、胥门码头……枫桥夜泊的不是愁绪,而是粮船。
船式有木船、滩船、关驳船、码头船、米包子船、常熟船、绍兴船、苏北船、良划船、西樟船……
米行自备的是运米船,柴行专门有柴船,送香客去杭州进香的船叫香船,送酒的叫酒船,这些都属于专船专用。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苏州的桥,有名可查的就有四百多座。宝带桥、帝赐莲桥、接驾桥、枫桥、乌鹊桥、草桥、香花桥、进士桥、歌薰桥、悬桥、花桥、渔郎桥、渡僧桥、乘鱼桥、彩云桥、鹤舞桥、窥塔桥……
汉字的美,在苏州的桥名上闪耀光芒。它们大多数与运河水有关。随手指的一座桥,也许就曾被文人墨客们歌颂过。
苏州的街巷里,每每有河、有桥,桥边有茶馆,茶馆里唱评弹。那些街巷里的小河,并不浑浑噩噩,它们有波澜,有鱼,清澈见底。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这些街巷里弄的小河,都与运河有关。夜深人静时,它们都会聆听运河传来的波涛声,就像孩子倾听母亲的心跳声。
《红楼梦》开篇写了苏州阊门的繁华,阊门的繁华是运河带来的。水运年代的奢华,极尽人间悲欢,演绎红尘万丈。乾隆六下江南,走的是京杭大运河,苏州是他的必到之处。大运河给苏州带来无尽的物,带来南北贩夫走卒,带来诗词歌赋,带来范仲淹、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也带来以游玩为名的天子。
春秋时吴国为伐齐国,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凿了第一条人工运河,长一百五十公里,叫邗沟,许多书上称邗沟为“运河第一段,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这是公元前486年的事。
公元605年,隋代在邗沟的基础上进行大扩展。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开凿了江南河、通济渠、永济渠,然后连接起来成了史书上称的“南北大运河”。元代时进行翻修,弃洛阳,取北京,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史称“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比南北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到了明清两朝,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兴修。它就像一座老房子,隔些日子便要进行翻新维修。古老的运河使用至今,不得不归功于它的不断翻新和维修。
吴国之都苏州是我的家乡所在。家乡有一个说法:大运河由苏而起,向吴而生。公元前495年前后,吴王夫差役夫开河运漕,自苏州经无锡到达孟河,长达八十多公里,是江南运河最早开挖段。
家乡还有个说法:邗沟并不是中国第一条人工运河。第一条人工运河是公元前506年,吴王命人开凿的胥溪,船舶经胥溪从苏州城直通太湖和长江,是世界公认的最早运河。
于是,大运河的江南开挖段,最早是在苏州,世界上第一条人工运河也在苏州。因为苏州才有了运河。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史志笔记》中写道:
苏州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旧物……其所以历久而不变者,即为河道所环故也。
这句话说成大白话就是苏州这么古老,但一直保持着活力,主要的原因就是环绕苏州的运河水道。
苏州城是与护城河同时诞生的。护城河自古就是大运河的主航道。苏州护城河来头很大,它与苏州城同时诞生于公元前514年。这一年,伍子胥相天法地,在此“凿斯水,筑斯城”。城为“阖闾大城”,水为护城河,立水陆城门八座。苏州弄堂众多,有“伍子胥弄”。
苏州的护城河也就是大运河故道中最早问世的一部分,从此苏州人被运河水环绕身侧。即使苏州城内没有那么多的河泊,只要有了这条绕城大运河,那也是家家都枕着河睡觉了,没说的。
作为苏州人,走来走去都绕不过运河水。
我出生在苏州望星桥畔的严衙弄。弄堂边上有一条行道,行道边上有一条河,叫官太尉河,这条河通着运河。运河就在不远处,阳光下碎金烁银,铺出一河的富贵。那时候运河里的船不多,经常是安安静静地流淌着,运河还没有改道。运河改道是二十年后1987年的事,工期十年,1997年完工。改道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大运河的运输越来越繁忙,有一些狭窄的桥洞关隘处,经常险象环生。
运河里的鱼曾经很鲜美。运河里的鱼品种也多,鲫鱼、草鱼、鲢鱼、鲤鱼、鮰鱼……在运河里长大的一些鱼,长到十几二十斤是寻常之事。运河水急河深,野钓困难,但还是有一些迎难而上的钓客,几十年如一日在运河里打窝垂钓。
后来钓上来的鱼有机油味了,预示着河里船只太多,航道超负荷,污染严重。再后来,没人吃运河里的鱼了。那些鱼空有漂亮外表,却有着呛鼻的机油味,下不了嘴。
难怪鱼儿有汽油味,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大运河日夜繁忙。苏州的米、油、煤炭、建筑材料、农用物资,有一半是通过运河运到各乡镇的。它是黄金水道,也是负荷最重的水道。古城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来自大运河的压力,苏州不断地拓宽航道、截弯取直、加固驳岸。有汽油味的鱼儿还算是小事,运河对城的影响、城对运河的限制束缚,都到了极限。
岁月更迭,世事变迁。当苏州开始大运河改道工程后,城里的河渐渐少了,但几条主要的还在,学士河、临顿河、平江河、桃花坞河、干将河、府前河……它们都通着运河,熟知运河的秘密,唱着与运河一样的亘古不变的歌。
苏州以水而生,以河而荣。太湖固然是它的身畔明珠,运河,是它项上金链、腰间玉带。住在这个地方,想不炫富都不成。
当我住在严衙前时,谁也没有料到大运河今后会这么热闹,又会因热闹而改道。改道后的运河,千吨大船畅通无阻。以前的急促与混乱,航行中的危机四伏一去不返。
五岁时,我跟着父母离开严衙前,去苏北“上山下乡”,是从南门轮船码头坐着船去的,一路在船上玩耍、睡觉,看大运河的水波。后来船到了镇江,进入长江,两天两夜后,上岸,坐上解放军的大卡车,往苏北平原的目的地而去。再回苏州城已是五年后,短暂的停留,居住的弄堂里也有河,但不是大运河。
我读高中时住在旧学前,那里有苹花桥,有一条南北向的临顿河,长两千四百米,北接齐门外城河,南连干将河,干将河上有十九座桥。齐门外城河那里有古城门和城楼,内侧有水城门。1950年代拆了古城门和城楼通路,1978年拆除造了水闸。2011年又修复了齐门城楼遗址和部分城墙。
临顿河也是通着运河的。它可通舟楫,供主妇洗涮。女人成堆聚集在一起洗衣洗菜和淘米的河埠头,就是河水的上游。没人去的僻静下游的河岸边,常常是洗脏东西的地方,包括涮马桶。我记得水总是急急忙忙一刻不停地从北向南流,河水打着小漩涡,一眼就能看到水底。水里有很多小鱼儿在游。没有人朝水里扔垃圾,倒是经常有阿姨阿婆们捞出水里遗落的菜皮、树枝什么的。经常有马桶盖被水漂走,岸上就会热闹起来,女人们会帮着追马桶盖,手上拿着树枝、杈子什么的东西,沿河追着捞。男人们一般是站着看热闹。有一次,一位男人调侃追马桶盖的女人:快点跑,马桶盖就要漂到运河里去了。
读完高中,我们全家搬到了里河新村。新村西边,就是运河,印象最深的是货船吃水很深,缓慢行驶的船体仿佛快要没进水里。睡在床上,半夜里常听得河里汽笛声声。那时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听着运河里的汽笛声,常常想跟着这样一艘船流浪远方。
1988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家三口住在严衙前东北边的一个小弄堂里,离运河很近。夏天,一家三口吃了晚饭,就去运河边散步。也曾在运河里游泳,把儿子脱得光溜溜的扔到水里,或者放到水边的竹排上。运河里的水还清,还能游泳。吹过运河水面的风,无色无味。
作为曾在运河里游过水的人,我负责任地讲,正常的运河水,确实不像一般的池塘水。池塘水柔和丰富,气质如女性。运河水的气质偏中性,它简单冷漠,公事公办的样子,击打在身上,带着不知来路的浑厚的力,令人感到它深不可测。
我已不再想跟着运河里的货船流浪,守着运河,就是守着自己曾经的梦想岁月。
文学路上的恩惠
在我记忆里,我母亲是第一个给我文学恩惠的人。我家是1969年冬从苏州下放到盐城阜宁乡下的。我妈妈当时才二十五岁。她把家里大部分东西都变卖了,唯独留下了许多书。她把这些书带到了苏北乡下,对她来说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的狂热行为,却也无意中打开了我通向文学之路的大门,给了我一个无路可走时的生存之道。她会写一些旧体诗,但是写得很拘谨,用词用得小心翼翼。我一直认为,以她的人生阅历,当过教师、医生、企业家,她如果写小说,会很有意思。
但是妈妈在文学上对我的恩惠不仅仅在于那些带到苏北农村的书。大概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一家人去县城玩,妈妈要给我买一双布鞋。1970年代的苏北农村相当穷,吃饱穿暖是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男孩到了十来岁还光屁股是常见的,为了一把稻草的归属也会动刀子。当然他们现在的生活已是翻天覆地,改革开放给穷人带来了富裕,富裕带来了做人的基本尊严。
在这之前我还有过一双红皮鞋,我穿上它出门转一圈,回到家时只剩一只了,是跳水沟时陷进了污泥里。我平时就赤着脚走路,和我村里的小伙伴们一样。这回妈妈要给我买新鞋,那是我人生中的大事。没料到我看上了柜子里的一套书,浩然的《艳阳天》。我就提出不要鞋子要这一套书,我妈妈二话不说就给买了这套书。我后来看完了这套书,年纪太小,看不懂什么,但记住了书里的一些气息和场景。
我成年后,感激妈妈对一个孩子的理解。除了理解,她对我还有深深的宽容。农村孩子中有许多学业很好的,即使学业不那么优秀也是读书认真的。可我从一年级就开始开红灯,有时候语文、算术双双不及格。我不爱上学,成天在外面游荡,过我的梦游生活。我妈妈那时候教中学,还兼做校医。老师们碍于我妈妈的面子,都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么一个差生,提出买一套对功课无用的小说,妈妈居然马上答应了。与众人面前装扮女儿相比,她更看重一本书的价值。这种智性,是文学给予她的。文学恩惠了她,她又恩惠了我。
在文学上,妈妈没有教过我任何东西。或者说她也没空教我什么。我记得她唯一教过我的是一个成语:乌云密布。有一天她正在家里闲着,看到天空里乌云翻滚而来,渐渐遮蔽天空。她就朝天上一指,对我说,这就是乌云密布。
后来我在《钟山》上发表中篇处女作《成长如蜕》后,她对我惊叹:你还会写小说啊? 她不知道她在文学上对我有过莫大的影响。是的,对一个孩子的宽容和理解就是最大的支持。
我在阜宁农村读完三年级,父母把我送回苏州外公外婆家。他们考虑到女孩子在穷乡僻壤出路少,也想避免以后嫁个苏北乡下人,就独留了我的户口在苏州。现在要回苏州读四年级了。若干年后,我偏偏还是嫁了一位苏北乡下人,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我外公外婆住在观前街西头的建设弄,邮电大楼旁边,第一百货商店对面,是个热闹的地段。弄堂口是11路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地上总有汽车卖票员随手扔下的一只只票根,我很喜欢这些票根,捡了不少放在口袋里玩。我的舅舅和舅妈也住在我外公外婆家。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是我的表弟。我就整天抱着我的表弟在外面游逛,城里的亲戚中,没有人让我去学校读书。我也没有去学校读书的愿望。
但我想看书。我那时候已看完了《石头记》《西游记》《普希金文集》《艳阳天》,当然是看不懂的,许多字也是连猜带蒙。这不妨碍我读书的热情。我们住的是一个大宅院,前院后院、楼上楼下住着六七户人家。我每个人家都去打探了一下,只有后院一对小夫妻的家里有书。他们有一位年纪和我相仿的女孩,女孩长着一头自来卷发,长得像个洋娃娃,十分漂亮。我向女主人借了一本《海岛女民兵》,书里有个某工厂工会的印章。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我拿起书就忘了别的事。因为小表弟没人抱,我的舅舅觉得是书犯了错,就把书撕掉了。我那时候虽然十岁不到,也知道还不了书是一件不好的事。我慌乱、焦急,还想过用别的书代替。最终我两手空空地去找借给我书的女主人。我站在她家门口,难为情地告诉她,我还不了书,因为书被我舅舅撕掉了。女主人笑盈盈地上前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没关系的,书不用还了。然后她给我的口袋里装满了爆米花,回过头对她那个像洋娃娃的女儿说:你看人家,没有书还找书看,你有书也不看。
这一天对我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不用还书,口袋里装满爆米花,因为我爱看书,还受到了莫大的肯定。
半年后,我被妈妈接回了阜宁农村,估计她已知道我在苏州是没法去学校读书的,还是老老实实回苏北乡下。我又开始了乡村里的梦游生活。
我不知道那位女主人姓甚名谁,我只知道她给予我的文学恩惠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就这样,我在乡下混到初中二年级。妈妈怕我大了以后找苏北人结婚,又让我独自回苏州了。以前,苏州人非常忌讳与苏北人联姻,如果谁家有女儿嫁给了苏北人,那就是整个家族的羞辱。我还是住在外公外婆家里,我的舅舅舅妈也还是与我们住在一起,小表弟也四岁多了。我们住在观前街玄妙观后面,这个地方更热闹。
我那时候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孤身一个女孩寄人篱下,吃不好、吃不饱还是小事,内心的孤单落寞可想而知,有时候半夜醒来,正巧被子上有月光洒着,那就怎么也睡不着。
外公是木匠,舅舅也是木匠,他们家里自然是没有书的。但上天总会给落魄者补偿,我与班上的女同学范苹苹交上了朋友,听说她爸是范仲淹的后人。她家离我家不远。她家里也没有书,但她家里有两位爱书的人。我就把她家当成了我家,一个精神之家。我常常扔下书包就去她家,有时候一天之中要去她家好几趟。
范爸爸与范妈妈就是那两位爱书的人。他俩非但爱书,还爱写作。范爸爸是小学美术老师,范妈妈是丝织厂工人。家里有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也是丝织厂工人,小女儿读高中,小儿子读初中。
自从我和范爸范妈谈了我的写作理想之后,他俩捷足先登,风风火火地开始了散文写作。我每次去她家,她妈妈就会拿出一本活页笔记本,上面写着一篇篇散文。范妈妈一边看笔记本,一边告诉我她昨天写了些什么内容,范爸爸就在边上插话、补充。谈得最多的是一篇《天平山一瞥》的散文。这篇散文是范爸范妈两位共同的杰作。他们斟字酌句,不停地朗读、争论、修改。写得很是苦恼,但也苦中有乐。
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日子,我深入一个家庭,见证了两位中年文学发烧友对写作的虔诚,见证了汉语在一个普通家庭迸发出来的光芒。他们一辈子也没有发表过作品,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他们爱写作,只是喜欢写作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光亮,带来愉快。
我那时候还没有写作,这一段经历,为我将来的写作打下了精神的基础。在这个家庭度过的日子,成为我写作前的预热阶段。不管过了多久,这种热度还保持着当初那样。他们没有教过我高深的学问,他们也不懂高深的学问。他们让我看到了对文学的至诚之爱,这种赤子之心才是写作中最可贵的元素。
这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给予我的文学恩惠。
很多时候,施惠的人并不知,受惠的人也不觉。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但那份恩惠就如头顶上的太阳。你就是瞎子,也能感受到它的温暖。
(本文摘自《运河边有个我》,叶弥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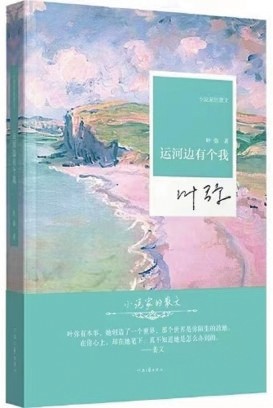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