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始于1970年代。那时候,一个乡村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自田头广播、大人的片言只语和没完没了的战争电影。我们从电影里认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们由此认识了这个世界,知道美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沙俄和德国宪兵。田头广播连接着伟大首都北京,从那里我们感受毛主席挥舞的大手和思想的光芒。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大手一挥,整个中国就生动起来。乡村的天地就这么大,但通过广播和电影,世界的边界得以拓展。如果那时候,要我画一张地图,那么,北京理所当然就在世界的中心,我的村庄则紧靠着北京——实际上我的村庄距北京一千八百公里。我的志向远大,在一个闭塞的乡村怀抱着有朝一日把全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解放出来的理想。
后来,小情小调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播上软绵绵的抒情音乐代替了刚性宏大的战斗歌曲,说明社会的斗争性减弱了。电影的内容也随之改变,银幕上出现了一些柔软的内容。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电影令人惊艳:柔软的身段,华丽的服饰,缤纷的头饰,迷幻的脸谱。是的,我说的是戏剧电影。我看到的戏剧同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却可以击中我们的情感。我们都看过样板戏,样板戏的服饰是我们时代的装扮,既写实又夸张。但这些戏剧一点也不实际,一招一式,像是空中的舞蹈,显得清丽而寂寞。
世界在一点一点打开。世界有着它光滑的表面,也有它复杂的肌理。现在,幽深神秘的地带向我敞开了,我感到这世界出现了一些原来我浑然不觉的消息,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北京,也不是来自我自制的版图,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更确切地说,我的内心被某种力量裹挟了。当时,对戏剧的迷恋几乎是乡村的全民运动,无论老幼都参与了这一拨的追逐。乡村电影总是在晒谷场放映,我们早早搬了凳子,占据有利位置,看着太阳从头顶偏向西方,然后,太阳又一点一点从西边的山下沉落。等待的时间分外缓慢,黑夜迟迟不来,就好像这世界只留下白天本身。但夜幕还是会准时降临的,然后银幕上开出艳丽的花朵——那种垂死的封建主义花朵,我觉得那像是天堂降临到人间,银幕上的一切具有非人间的气味,那布景上的一切莫不似想象中的仙境。
乡村电影往往在一个晚上要在附近的村庄轮流上演,我们叫作“跑”片。这个村庄放映完后,迅速传给另一个村庄。因此,如果我们村庄是天黑开始放映,那么另一个村庄则要在晚上九点之后,再下家就得在凌晨了。我们为了再看上一遍,往往跟着片子跑,从这个村庄辗转到另一个村庄。虽然刚看过一遍,但我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实在太困了,也会在操场边的某个草垛上睡去。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散场,操场上充满了落寞的气息,然后,就起来奔回自己的村庄。通向家的路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脚步声在黑夜里带来回声,就好像有人跟随着你。你跑得快,他也跟得快,就好像尾巴上跟随着一个鬼魂。我的心蹿到了嗓子眼,由于惊恐,有时候会哭出声来。直到回到家,才松一口气。
我们迷上了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一部绍剧电影。绍剧是一种很特别的戏剧。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平时哼唱的“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绍剧中的唱词。绍剧高亢、激越,同绍兴的民风颇为相似。绍兴人身上有一种颇为强悍刚烈的东西,绍兴人是颇具革命性和破坏欲的。绍兴是江南的异类。出生在绍兴的鲁迅被称为硬骨头自有其来历。孙悟空唱着绍剧,在银幕上变幻莫测,腾云驾雾,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火眼金睛,妖魔现形。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孙行者,那么人生就简单了,所有的愿望顷刻间就可以达成,什么都不在话下。
越剧《红楼梦》把银幕的灿烂推到了极致。那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如水的女性、绚丽的服饰、烟花般的灯火,再加上故事的缠绵,令所有人神魂颠倒。
但是真正的《红楼梦》比电影要复杂得多。有人开始讲述曹雪芹的《红楼梦》。讲述者是一个劳改犯——一位曾经的教师,因为犯过作风问题而锒铛入狱。他从牢里出来后,回乡成为一个农民。在夏日的夜晚,他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人,月光照耀着黑压压的人头,他温柔的声音在夜色中缓缓回荡。他讲述的《红楼梦》充满了神话般幽深的气息。我们都知道了前世的姻缘,那个林妹妹原来是绛珠仙草,而那宝哥哥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绛珠仙草。林妹妹来到世上是来还“原债”的,她将把上辈子领受的甘露以眼泪的方式还清。林妹妹的眼泪,注定是流不干的。这个故事从戏剧的热闹,转变成至情的悲剧。人们听得不胜唏嘘。
后来,听众慢慢减少了,那个劳改犯的《红楼梦》虽然没完没了,但听多了我们也就感到无聊了。听众还是有的,慢慢地,只剩几个妇女和姑娘了。后来,这几个女人为这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争风吃醋起来。在某个黑夜,这个男人被打成了重伤。
绍兴一地,诞生了两个剧种: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绍剧,充满了阳刚之气,适合金戈铁马。另一种是越剧,则是阴柔缠绵,适合儿女情长。这是十分奇怪的现象。就像周家,诞生了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一个是刚烈的鲁迅,另一个是平和的周作人。
我的村庄就在离绍兴城不远的曹娥江边。我喜欢绍剧,也喜欢越剧。高兴的时候,便会歇斯底里地吼几句绍剧,如果有点少年式的小小伤感,那么就哼几句越剧。绍兴既有绍剧式的大爱大恨、直来直去的一面,也有越剧式的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表情,绍兴的个性是很两极化的。
村庄的女人们大都喜欢越剧。那些年轻姑娘开始寻觅她们心目中的“公子”。她们用麦秸秆编织扇子,在扇子中织上电影里的唱词,送给心上人。乡村的恋爱在戏剧的熏陶下,似乎有那么一点“鸳鸯蝴蝶”的味道了。
那年夏天,我感到身体分外轻,又觉得体内充满了力量。我们还是像往年一样,刚入夏就跳进曹娥江游泳。往年,在江水中游泳都是赤身裸体的,但这一年,我总是穿着一条短裤。我感到我的身体有了一些令人脸红的变化。
我对戏剧电影也有点腻烦了。那唱腔,曲里拐弯,婉转曲折,没完没了,终究还是磨人耐心的。幸好,这时候,乡村开始放映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
我们国家拍出了新的故事片。这些故事片讲述的就是眼前的火热生活。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公交车班组里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忘了,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观后的感受。我觉得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浪漫迷人,充满了乐观和纯真。公交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欢笑、歌唱,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充满重新解放的新时期的喜悦。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部糟糕透顶的电影,但当时我却因此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公交车自然成了我想象中的城市的重要表征物。熙熙攘攘的人们、鱼贯而出的乘客、沿马路热气腾腾的小吃、姑娘的裙子、色彩各异的气球、漂亮的发式、高耸的建筑,通过电影进入我的内心。我牢牢地记住了它们。它们叫城市,与我所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那个在银幕上的世界,光彩夺目,像是一些精致的玩具。它是我的乡村的反面,就像现在乡村是很多人心中的乌托邦,那时候城市是一个乡村少年的乌托邦。
一批早年拍摄的老故事片开始陆续在乡村放映。《舞台姐妹》《一江春水向东流》《女跳水队员》《冰上姐妹》这些电影向我们展示一个不同于革命的世界,一个充满女性的舒展、柔美的世界。革命女性服饰统一,她们的美掩藏在蓝布衣衫下面。这样的世界同样连接着一些深远的传统,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传统。《一江春水向东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时代的上海,一个糜烂腐朽的上海,一个金碧辉煌的上海,一个虚无缥缈的上海。十里洋场、华灯凄迷,风华绝代、柔情万种。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拓展,如同那个我最初绘制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版图需要重新调整,对历史认知也必须得到修正。
我喜欢上了上官云珠演的那个角色。她不算是个漂亮的女性,白杨看起来比她美丽端庄得多,但她在电影里比白杨更性感、更放浪。她胸部高耸、肌肤裸露,她和男人跳贴面舞,和男人打情骂俏,和男人在床上打滚,场面令人想入非非。
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个仲夏之夜。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家的阳台上,失眠了。我脑子里全是色情的场景。一个少年对色情的想象资源有限,他还没有见过女性的身体,不知道女人的秘密,他想象中的女性虽然赤身裸体,但形迹模糊,十分可疑。到处都是水,不是白天的水,是昏暗的夜晚的水、暧昧的水,水中女性众多,像莲花,层层开放,而我像鱼儿一样在这些花朵丛中穿行。
女主角是谁呢? 她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她的那张脸在无数面目模糊的女孩中分外清晰,令我心头暖洋洋的。
她是隔壁班的女孩。她有一张稚气的脸,鼻子上经常有细细的汗珠,那年夏季,好像细汗一直在她的鼻子上。但她的身体开始饱满起来,有了曲线。那是让人费解的令人充满好奇的曲线。我无法想象。
那时候,我已是一个初中生。我家前面的那条路是通向学校的必经之路。每天放学,我就快速地回家,站在阳台上,看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几乎不用寻找,我就知道她出现了。她在那个拐角出现之前,我就嗅到了她的气息,那气息好像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存在。然后,我看见了她。她低着头,从来不朝我这边看,而我贪婪地看着她,不放过她任何动作。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好像有些欣喜,她在追打另一位女孩。她的样子令我感到喜悦和宁静。我觉得生命中似乎有一个盼头,等待她的出现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渐渐走远,马路上空无一人,我的心就像马路一样空荡,就好像我的心被她带走了。
她是我同学的堂妹。她家就在那同学家的隔壁。为了接近她,我开始去那个同学家玩儿。在星期天,我背着书包去他家做作业。在乡村,大人们是没有星期天的,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白天的乡村,只有老人和孩子,非常安静、自由,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喜欢黑夜,喜欢黑夜里那种天和地融为一体的神秘感。在白天,我们制造黑夜,我们关起门窗来,点亮油灯或者蜡烛,在昏暗的光线下写作业。我的同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可以一天不说话。他的皮肤很白,他们家里人皮肤都白。她当然也很白。我多么希望他和我聊聊她。或者,希望他把她从隔壁叫过来,一起做作业。
有一天,她过来了。她过来时,脸是红的。她来问一道数学题。她先问她的堂哥,他没解出来。她又来问我。她就坐在我身边,我激动得发颤,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的。后来我终于解出来了。我讲给她听。这时她站起来,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在我解题的纸上移动。我碰到了她的手,她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我说话结结巴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理解。她最后拿起纸,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走了。我说,你同我们一起做作业吧。她脸上一下子飞满了红晕,摇摇头,说,不了。
我感到既幸福又羞辱。幸福就在我的手上。我的手滑滑的,感觉分外敏锐,好像全身所有的感知都集中到了手上,好像全身只有那只手是有意识的、会思考的,我感到这只手的陌生,好像它并不属于我,总之,它是一个异样的存在,是我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那部分相当于万恶旧社会的革命圣地延安。羞辱的是她没有留下来,那等于是拒绝了我,我于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像尘埃一样无足轻重。我的心头有一丝尖锐的痛楚。
很快就到了冬天。我们穿起了冬装,但由于身体长得太快,去年的冬装太小了,我们因此看起来有点可笑。可那段时光,我是多么爱美啊,为了使衣服看起来不太短,我穿得异常单薄。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瘦弱的身体瑟瑟发抖,但一看到她,我就会感到暖和。
白天,公社的礼堂要放电影了。公社的礼堂没有窗帘,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它的光芒比电影放映机发射出来的光线更强烈。总有使白天变成黑夜的办法。礼堂的窗子上糊上了涂成黑色的报纸,人造的黑夜就出现在礼堂。我已记不清那天放映的是什么电影,为什么公社的礼堂突然放映起电影来。我们没有票,好不容易才钻进礼堂。在座的都是公社的头面人物,他们的座位后面已挤满了人。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她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她的周围是几个毛孩子,他们不会感到她的存在,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在银幕上。可是,当我看到她就在不远处时,电影就消失了。电影变成了一团缤纷绚丽的色彩,声音也显得极不真实。在我的感觉里,别的一切都退到很远的地方,好像礼堂里唯有她存在,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第二天,在学校的一个拐角,她突然塞给我一包东西,然后就跑开了。我预感到这包东西里有我期望的一切。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把这包东西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北风很大,气象预报说,过几天就要下雪了。我虽然衣着单薄,但这会儿一点也不寒冷,就好像那包东西是一个巨大的热源。那一节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感到一切都远离了我,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就好像我进入了某个真空世界。
包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块围巾。那是一封充满了革命词汇的信,当然,充满了情感。她在信里叫我哥哥。她勉励我为革命、为“四化”学好本领。读着她的信,令我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太激动,相反,我感到全身发冷,就好像我落在了一个冰窟窿里面。我内心的狂喜早已被恐惧占据。
一块轻飘飘的围巾和一片薄纸把我压垮了。我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情。我心很虚,好像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那天放学,我再也没有站在阳台上等待着她走过。我躺在床上,想象着她路过时的模样。平时,她是不会朝阳台看一眼的,今天呢?她会向阳台顾盼吗?她会对那个没勇气的家伙失望吗? 她能明白我身上这千斤重担吗? 她不会明白,她比我有勇气。她一定不会想到,我是这么容易被击垮。我的心有一丝隐痛。
我不知如何处置围巾和信。我不可能把围巾围到我的脖子上,我又不知道把它们藏在哪里。我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现在像两枚炸弹一样令我感到危险。我暂时把它们压到床垫下面。
她大约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但我假装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开始热衷于和男孩子混在一起,开始远离女生,就好像女生是危险品,必须敬而远之。有时候,我会和她迎面相遇,我会对她微笑,我希望用微笑暗示一些什么,但是她不再理睬我,她不再看我一眼。后来,她提前退学,去城里顶替父亲的工作。再后来,我就把她忘记了。
有一些新的电影被拍了出来,由此诞生了一批电影明星。我在一本叫《中国青年》的杂志的封三上,看到了她们的照片。她们是刘晓庆、张金玲、陈冲,等等。她们成了我的梦中偶像。我最喜欢在电影《小花》中扮演寻找哥哥的陈冲,我弄了一张她的年历,在画片中,她显得稚气、单纯、朴实,但她丰满。她们慰藉着一个少年热闹而寂寞的日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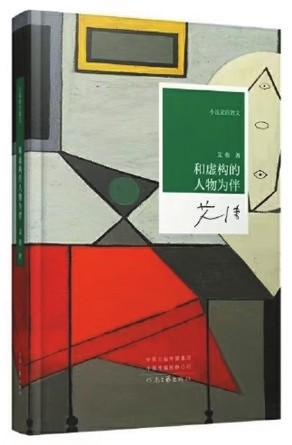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