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对他辑校古籍的研究,已有很多学者做过,但是用非常纯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辑校古籍的手稿,这样的研究成果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中华书局出版的石祥研究员所著《鲁迅辑校古籍考》,是这方面颇具前沿性的一项成果。
《鲁迅辑校古籍考》共十六章,依鲁迅辑录的古籍的性质,分为史籍地志、中古文史典籍、博物杂考书三编。上编四章,考察《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等四种辑本的结构化和文本生成;中编八章,述考《嵇康集》《谢灵运集》《沈下贤文集》等八种辑本的手稿面貌和校勘问题;下编四章,前两章讨论《岭表录异》《云谷杂记》两种辑本的辑校体例、校勘思路等,后两章综述鲁迅抄校《说郛录要》等博物书、辑录《范子计然》等越人子书的复杂情形。
尽管正文是以逐章逐种讨论鲁迅辑校古籍的面目呈现的,但从研究的创新性来说,以置于全书之首,名为序章的《鲁迅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为代表,全书充溢着一种力图对20世纪早期中国传统体式文献手稿作一具有理论深度的审视的气魄和视野,同时又不乏精当合规的专业巧思。如所周知,在古籍版本学领域内,以套格笺纸的样式作为鉴定古籍写本的重要依据,已是一种颇为成熟的方法。但在鲁迅研究中,前此似无人应用过此法。本书排比鲁迅日记所用的套格稿纸,得出各种样式套格纸的绝对或相对使用时间,以此对照现存鲁迅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种所用的各种套格纸,推定各稿的书写时间,使得那些原本零散且无法直接判断辑校时间的鲁迅稿本,被排次到一个相对合乎逻辑的时间序列里,使后续逐一考察鲁迅辑校古籍辑本的工作,建立在一个较既往研究更为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上。全书以此为开场,可以说无论在鲁迅研究还是古籍研究方面看,都是非常有新意,也非常到位的。
至书中正文各章的学术价值,个人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为鲁迅辑校古籍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因为鲁迅地位特殊,有关其辑校古籍的研究,尽管在鲁迅研究界仍属小众题目,但从各个辑本的角度看,已不乏相对成熟的成果。像著名的《嵇康集》辑本,已有的论文几乎把一些基本问题都做过。但是,本书作者凭借其古文献专业从业者的敏锐眼光,发现学界迄今对鲁迅当年辑校《嵇康集》时所用的底本——明吴宽丛书堂抄本,尚缺乏深度关注,即以此为入口,重新对勘丛书堂抄本《嵇康集》和鲁迅辑校本诸手稿,发现在辑校过程中,鲁迅所作所为,有的非常专业,有的也颇业余。前者如在对校、他校两者顺序的处理上,鲁迅一反古籍整理常态,不以同为嵇康别集的对校为先,而以他校(主要是唐代类书等)为先,本书即指出此举乃鲁迅深谙传世魏晋诸名家别集,均后人所辑,其文字在校勘上的重要性,有时反不如唐宋类书,因为后者很可能保留着更接近魏晋时代名流原作的面貌;在理校和本校方面,像对《声无哀乐论》一篇丛书堂抄本“季體采诗观礼”句中“體”字的校勘,作者引述鲁迅两部手稿中的三条校记,显示原本应作“季札”二字中,“札”先讹为“礼”,“礼”又变为“禮”,“禮”再讹为“體”,以实例彰显了鲁迅的旧学功夫确实到家。后者如在复核校勘文字时,作者发现鲁迅的校勘,文字上有不少漏校,校勘结果的处理,也存在前后依违两端,有不够严谨处。这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作为学者的鲁迅当年辑校古籍时的实态,说明以标准的古文献学来衡量,鲁迅整理古籍到底在什么水平上,他对某书的具体认识又是怎样的。这样的写法与结果,与一般研究鲁迅辑校古籍的论著站在单一表彰立场上讨论的路径,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本书作者在这上面尽管未加特定的评论,但其朴素的结论,对于拓展鲁迅研究者的视野,无疑是有益的;对于整个鲁迅研究而言,有时候比要反复说鲁迅如何深刻、如何不同凡响,可能更有意义。
其次是为中国古籍整理史的研究与书写,提供了一个古今贯通、证据充分的上佳案例。迄今为止有关古籍整理的历史考察,有两个基础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连续性的全宗史料明显缺乏,二是中国的古籍整理传统从古至今都是重书(原典)不重人(整理者)。以此迄今为止将古籍整理的过程,通过相对完整的史料梳理,做得相对细致与深入的,是有关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古籍出版为中心的古籍整理史的梳理,尤其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相关古籍整理的人事回忆与考辨。与之相反的,是即使是对孔子那样的具有开路先锋性质的先秦古籍整理大家,其实相关的研究远未达到充分且有明确共识的程度。本书选取鲁迅那样一位天然具有强关注度的现代名人的古籍整理成果为研究主题,可以说至少在两个方面为中国古籍整理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作了很好的示范:一是将关注的重心,从相对单一的书转移到复合态的人与书二者;二是将深度考察的时段从当代上溯到了现代。就人与书的复合态的研究而言,本书中涉及的同一种古籍的辑本,从手稿的角度看,既有鲁迅本人的,也有周作人和许广平的。如果把重点放在书的角度上看,二周和许广平的抄本价值判断很简单,就是以抄写内容是否准确为准;但如果把视角转换为书与人并举,则辑本如何诞生的复杂样态,就凸显出来了。至于把古籍整理史研究的深度考察时段上溯至现代,是因为很多人忘记了,像鲁迅那样的新文化运动干将,曾亲与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事业,则他如何处理相关学术事务,既可以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射和映照他前后的中国古籍整理史上存在的各种历时与共时性现象——在辑佚和校勘古籍时,他们所遇主要问题是什么,可能走的弯路在哪里,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置这些问题等——又可以呈现五四那一代先哲们在“打倒孔家店”式的激烈姿态背后,内心和笔下实际存在的传统底色。
再次是展示了古典文献学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天地。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看,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前只是一个二级学科专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只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还是运用某种古典方法研究任何文献,迄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本书虽非古文献理论著述,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了什么才是有活力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中国古典文献学正是一种以传承中国古典学术方式为旨归,对一切古典体式文本作搜辑、整理和考辨的跨学科、跨时代的学问。本书尽管处理的对象是一位现代大作家、大思想家很特殊的一批古典体式的辑佚和校勘之作,但成果集结为专著,给人以最大的启示,在于运用传统的纯正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在跨界和跨时代研究方面能产生如何令人惊艳的效能。以第二章讨论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为例,作者通过细致排比考订,展示的不仅是鲁迅辑本内容上相对于前人辑本后出转精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独创的“增益型”基本的概念统领下,藉由鲁迅相关辑本手稿俱在的有利条件,完整复原了一种前人已有辑本的古籍,如何在鲁迅笔下二度重生且旧貌换新颜的曲折过程,也就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解答了古籍辑本是如何“生成”的问题。此外,单就版本学而言,本书考察鲁迅手稿,大都从实物版本(纸张、墨迹等)出发,而归根于文本版本(文字差异、文本层次等),两方面结合大都堪称完美,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更高的专业标准来衡量,已出版的这部《鲁迅辑校古籍考》,在外部形态方面尚有可改进之处,即开本过小,无随文插图,局部高清图过少,且色彩失真、清晰度不够。依全书的文字内容来看,这本是可以做成一个既有深度又非常好看的图文对照的书,现在这个书的成品样貌,读者面相对就比较窄,事实上哪怕是专业的古典文献学者,通读全书也不太轻松;研究鲁迅的学者,除非对相关课题作过专门研究,一般恐怕也看不太懂,更遑论普通文史爱好者了。目前的版式与图文设计,未能充分体现作者著述的高远立意,也在客观上降低了该书本可产生更为广泛的学术文化效应,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不过从整体上说,《鲁迅辑校古籍考》仍是一部非常出色地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研究鲁迅辑校古籍的专著,其价值已跨越了单一的鲁迅研究,而对中国古籍整理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深度展开均有显著的推进作用。作者在引言里提到,鲁迅用力最深的以《古小说钩沉》为首的小说文献的辑录校勘,本书未有论及,今后将另撰专书讨论。我们也非常期待那部专著能早日完稿并出版,与本书合为双璧。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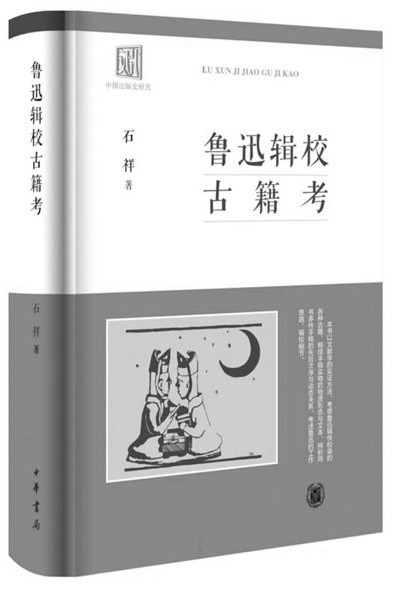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