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九迪/文■任增强/译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有一个源自古代传统、令人浮想联翩的称谓,即其自称的“异史氏”(the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诸多学者已然指出,蒲松龄效仿了公元前2世纪的太史公司马迁。两人的自称不仅措辞类似,而且用法相近:司马迁在评论历史叙事时,自称“太史公”;而蒲松龄也仅仅是在故事所附的阐释性和评价性批语中,自称为“异史氏”。
然而,“异史氏”与“太史公”之间的有意回响,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因为蒲松龄所评论的主题并非军国大事抑或显赫的政治人物,而是鬼狐和非正常的人类经验,即其所谓的“异”。蒲松龄“史氏”的称谓主要是修辞性的:一方面,传递出传统历史书写包罗万象之义;另一方面,在倾注个人极大热情的领域,肯定自身的权威性。这种对“史”与“史氏”的特殊理解根植于私修历史的传统,这在蒲松龄之前的时代已然大量存在(再一次,我们可以将这一传统追溯至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史书最初是私人化的,而后才被视为官修正史)。通常认为,这种私修历史的传统刺激了中国小说的创生。的确,小说有两种主要的称谓,即“外史”(unofficial history)和“逸史”(leftover history),因为这些著作的内容一般不见于官方的历史记载中。
这些外史的作者通常自称为“外史氏”(Historian of an Unofficial History)。然而,在16、17世纪时,越来越多的作者会取一些笔名,以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特别的志趣。我们发现有作者自称“情史氏”“畸史氏”“幻史氏”,所辑内容则冠以《情史类略》《癖颠小史》《绿窗女史》等。如同《聊斋志异》,这些故事和轶事集,并非以时间为序编排而成,书中事实与虚构杂糅;这些作品中的历史观念似乎更接近于百科全书式的,即将古今所发生的故事,围绕某一主题加以辑纂。然而,我们也会发现诸如袁宏道(1568—1610)的《瓶史》,甚至并非叙事性的。上述书名中“史”这一术语,似乎仅仅表明这些作品是据某一专门主题编纂而成。这些例子意味着“历史”作为一种观念或一个范畴的随意性与松散性,这种自由度必然会传导至明末清初的小说实验中,而《聊斋志异》在其中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彼时的“史”至少在特定语境中,接近于古希腊语中“历史”(historia)一词最初的含义——一种“询问”或“调查”。
本书以为,正是在询问与调查的意义上,我们方可理解蒲松龄的巨制。《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经三十余年,从描写东海中蛤与蟹共生关系的简短条目,以展现自然界之异,至情节复杂而具有自我意识的元小说(metafiction),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狐仙请作者“烦作小传”——无论在规模还是跨度上,均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故事集,还包含作者的序言与评论。尽管这些评论通常是教化式的,但绝不会俯就其读者。与故事本身相比,这些评论辞藻更华丽、更艰涩难懂,不论是充满激情的、不着边际的,或是诙谐滑稽的,往往都使得读者对故事的阐释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不同于博尔赫斯(Borges)笔下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百科全书”,《聊斋志异》的广博并不意味着其排斥所有明晰的逻辑范畴。在蒲松龄的自称“异史氏”以及书名“志异”中,“异”这一术语显示出各种故事、评论以及序文之间如何互相协调一致。“异”这一主题,加之蒲松龄强大的声音与洞悉力,使得《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故事集,绝非一种随机的组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异”是蒲松龄提供给读者的一把管钥,用以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相应地,这一概念是本书阐释蒲松龄作品的聚焦点。
《聊斋志异》不仅在风格、范围以及复杂性方面,堪称达及中国文言小说的顶峰,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故事集已经定义了我们对文言小说的认知。现代以来对白话小说的推崇,使得文言小说与西方小说间的区别渐趋模糊。《聊斋志异》的故事并非只是碰巧以另一种语言写就的白话小说。白话小说,按理说,是在被清晰界定的某一虚构空间中展开的。而《聊斋志异》与之不同,其有意跨越小说话语与历史话语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是以继而产生的模糊性为依据的。而当蒲松龄以一位尽职的历史学家的方式提供信息来源时,这种模糊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蒲松龄的此种声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 在传统评论者眼中,《聊斋志异》是一部“劣史”(bad history),因为蒲松龄不可能亲闻亲见其所描述的一切;而对另一些评论者而言,蒲松龄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因为其故事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真实历史人物的官职几乎都是准确的,我们或许可以将上述两类评论者斥为天真的读者。但是因为蒲松龄至少在名义上声称具有历史权威性,从未完全匿身于纯粹的虚构之中,其所描述事件的可信性与准确性,对于读者而言总会是一个潜在的争论焦点。对蒲松龄作品的阅读,事实与虚构层面间的张力与蒲松龄对“异”的创构息息相关。
笔者使用“Strange”这一术语,以对应三个关键性的汉字,“异”“怪”与“奇”,它最为恰当,但诚然并非完美契合。此三字是常见的同义或近义字,通常用于相互界定。当三字组合为“奇怪”“怪异”“奇异”等词语时,彼此间的区别则更为模糊。一部唐代辞书中有关“怪”的循环定义,完美地阐明了这些术语之间的可替换性:“凡奇异非常皆曰怪。”还有一个例子,明代一则滑稽的鬼故事为追求喜剧效果,而有意强调了这些术语之间可替换的本质,不信鬼神的故事主人公冯大异,名奇。
然而,这三个汉字的语义域和隐含义并非完全相同。其中,蒲松龄用于小说名的“异”字,涉及范围最广,用法最为灵活。其基本义即“不同”或“有所区别”,相应地有着“不平常的”“突出的”“非固有的”“异端的”“古怪的”等含义——总之是异乎寻常。而“怪”的意义跨度最窄,指的是“怪异的”“奇怪的”“畸形的”“异常的”“莫测高深的”,最具有贬抑的意味。正如晚明作家冯梦龙(1574—1646)所谓:“然究竟怪非美事。”与其邪恶的隐含义相一致,“怪”又指动植物或无生命体所幻化成的妖怪。“奇”作为审美性评价术语,有着一以贯之的历史,覆盖了“稀有”“原创”“奇幻”“惊奇”“怪异”等畛域。尽管“奇”通常是一个较高的评价指标,却也具有反面的意思,指“对正常的偏离”。正如一位明代作家在历史通俗演义中为英烈辩护,而疾声力陈道:夫“所谓奇者,非奇邪、奇怪、奇诡、奇僻之奇……非若惊世骇俗,吹指而不可方物者。”其笔下的“奇”,意义十分模糊,又诉诸常见的论点,即“奇”与其反面“正”,两极可以相生。将这三个术语与其最常见的、完全相反的对立面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确实有所助益,比如“异/同”(different/same),“怪/常”(aberrant/normative),“奇/正”(exceptional/canonical)。
很难精准地对“异”给出一个明晰而充分的定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异”可界定吗?抑或说,具有充分的弹性、不可把捉、变化无常,是“异”重要的特征吗?在中国,人们很早便认识到,物之“异”并不在物自身,而在于观看者或阐释者的主观理解。故而,“异”是文化所创生之物,并在写作与阅读中得以不断更新;而且,它是借助于文学与艺术手段而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此意义上,“异”的观念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超自然、奇幻或者奇妙之类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说法所依据的无不是所叙事件在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能性。而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对立,一直以来是西方奇幻理论的基础,最为有名的即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托多罗夫在三种基础文类间进行了区分:神异(the marvelous)、奇幻(the fantastic)与怪诞(the uncanny)。如果所叙事件与后启蒙时代的科学常识相吻合,则我们处于“怪诞”的畛域中;若与上述规律相矛盾,则我们进入了“神异”的领域。只有当读者在上述两端犹豫不决时,我们才会处于“奇幻”的场域之中。正如克里斯廷·布鲁克-罗丝(Christine Brooke-Rose)所归结的:“故而奇幻文学的基础是模糊性,即奇异事件是否是超自然的”。
将托多罗夫的学说应用于一般的中国志怪文学,具体至《聊斋志异》,那么问题便立即凸显了出来:我们无法假定现实常识中的同样“规律”在其他文化中,或者在其他历史时期总能奏效。在《聊斋志异》中,规律是不同的。鬼魂既被视为心理所诱发的,同时又具有物质存在性,正如一组镜头(a sequence),既是一场梦,同时又是真实的事件。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当事物悖论性地被证实,又同时被否认时,其结果往往便是“异”。换言之,“异”与“常”之间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相反,是不断更易、模糊、擦抹、增殖抑或重新定义的。事实上,“异”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正在于这些界限可以无休止地被加以操控。
《聊斋志异》中的一则故事或许有助于阐明对“真”与“幻”之间界限的有意模糊,这一点也是本书就蒲松龄笔下之“异”开展研究的核心内容。《褚生》篇,开场便叙及陈生与家贫的同窗褚生之间的友谊。陈生出身殷实的商贾之家,窃父金代褚生遗师束金,其父发现后,遂使陈生废学。后陈父故去,陈生复求受业,拜褚生为师。不忘陈生高谊,褚生捉刀代笔,代陈应试。至期,褚生让陈生从表兄刘天若外出。陈正要出门,褚生自后曳之,差点扑地,而刘天若迅速挽之而去。
在刘家留宿多日,忽然中秋将至。刘天若邀请陈生登画桡,赴皇亲园游玩。登舟后,刘请新来的勾栏歌姬李遏云唱曲助兴。刘命之歌,李遏云面带忧容,竟唱古时挽歌《蒿里》。陈生不悦,曰:“主客即不当卿意,何至对生人歌死曲?”姬致歉,强颜欢笑。陈生稍息怒,命其歌自作之艳曲《浣溪沙》。姬奉命吟唱。已而泊舟,过长廊,见壁上题咏甚多。为留念,陈生即将李遏云所作《浣溪沙》题于壁上。
日已薄暮,刘天若遂送陈归,因闱中人将出。
陈见室暗无人,俄延间褚已入门,细审之却非褚生。方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惫矣!”共扶拽之。转觉仆者非他,即己也。既起,见褚生在旁,惚惚若梦。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惊:我实鬼也。”
翌日清晨,访李姬,则得知其已死数日。故地重游,故事这样继续道:
又至皇亲园,见题句犹存,而淡墨依稀,若将磨灭。始悟题者为魂,作者为鬼。
陈生最终的醒悟,自然源于对自身经历的清醒思索,但同样也引导我们从另一维度重新研读整个故事。可以看出,褚生在故事中自始至终是鬼,在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褚生与好友变换身份,以报其高谊;刘天若与唱曲助兴的李姬,同样也是鬼,而中秋节时的陈生,则是其与肉体相分离后的魂魄。
我们也正如陈生一般,被故事中误导性的因素带入歧途:令人不解的时间提示、句子中显性主语的频繁省略以及空间的分隔。即便当陈生面对一个作为他者的自我(himself as other)时,其依然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出于惊异与无法完全相信,陈生进一步探寻外部证据。
然而,这进一步的证据,来自陈生本人。探查的最后,陈生发现其本人竟然不经意间成为自身生活之“异”的记载者。正是他在壁上的题句,言之凿凿地记下了其在故事中对生与死,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跨越。颇有意味的是,此壁并非普通建筑或房屋的墙壁,而是廊壁;表面来看,是连接两个地方的过渡区域,但似乎又导向乌有之乡。正如泊于湖面上的画桡,廊壁亦将陈生所历悬置了起来。壁上的墨迹,惊人地显现出其作者的身份——不知其人、难以捕捉,处于完全消逝的进程中。幽灵般的痕迹于在场与缺席间短暂悬置,这无疑是魂魄所作,由陈生本人与另一个陈生所题。尽管故事谨慎地将陈生所历深深植于其主观理解中,但并不至于令我们自忖,此是否为其主观想象所生出的。此处的关键在于,陈生幻觉的主观性并未消除其所历的奇异性;相反,正是借此而获得了可被认同的形式。但那一形式,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记录本身便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
稍显简短,但是笔者对这一故事的解读,揭示出一种与托多罗夫截然不同的角度。不可否认,《褚生》篇包含了托多罗夫在奇幻文学中所析离出的因素,诸如分身、犹豫、模糊语言。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完全缺席的,即读者必须义无反顾地在超自然动因或理性解决方案间作择选。故事自觉地承认,有必要向故事中的人物以及读者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但是那些证据被有意模糊掉了。最终,壁上的题句既在又非在(both there and not there),生动而详致地解释了一种本篇以及其他诸多《聊斋》故事中的处理方式,即擦抹掉真实与虚幻之间,以及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种教训,即过度僵化的分类会造成各种错误的二元对立。这些范畴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18世纪小说《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对这一认识作了最好的归纳:“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另一教训或许是,如果“异”是可以界定的,那么必须在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变动区域中加以界认。
在早期对“异”的探索中,作者与读者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知识。而本书的研究,则试图展示在后世蒲松龄如何重新建构“异”。至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已然累积了过量的作品,彼时更多的是对其他文学作品的熟悉程度,而非外部世界,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的期待。就此而言,《褚生》篇提供了一个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当陈生初过园中走廊时,壁上已非空白,历代文人的题咏甚多。壁面已然成为一系列叠加的文本。当陈生紧接着题词于壁上时,其举动,并无任何特立独行之处;而其题句,与其他题词并无任何区别。陈生,也不过是另一位将自身所历记于壁上的题咏者而已。但当陈生又至皇亲园时,发现其他的题咏作为固定的标尺,从未发生变化,唯独其题句颇为怪异,“淡墨依稀,若将磨灭”。
其他这些题咏的在场,隐喻式地强调了在研治《聊斋志异》时所必需的一种或多种文本语境。我们需要将蒲松龄的故事置于悠久的志怪传统中,这一传统赋予其写作素材来源,并迫使蒲松龄进一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需要将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安置于明末清初的士人文化语境中,借以复原其故事的全部意义,更好地理解其故事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同样,我们也需要去重新审视《聊斋》评点的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系统,有助于我们追溯历代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不同理解。
为结合这些语境而对《聊斋志异》加以阐释,本书的研究分为两编。第一编梳理17—19世纪的《聊斋》阐释史,以确定读者是如何理解或解释“异”的。而后,细致审读蒲松龄在引人瞩目的《聊斋·自志》中如何呈现自我,以及蒲松龄本人与“异”之间的关系。第二编则转向故事本身,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该编并不着眼于鬼狐等已成为《聊斋志异》标签性的内容,转而探讨16—17世纪中国士人文化颇为关注的三个重要主题,而普通读者或学界一般不曾将这些主题与《聊斋志异》联系在一起。这三个主题,均涉及对人生经验中根本性界限(fundamental boundaries)的跨越,即“癖好”(主/客)、“性别错位”(男/女)、“梦境”(幻/真)。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关注,本书能够规避“超自然”的问题,转而探讨蒲松龄如何更新了“异”这一文学范畴。
结语部分,则以《聊斋》故事《画壁》为例,着重分析“异”的创构与越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回应《褚生》篇。再一次,故事主人公在游历的最后,发现墙壁已然发生了变化——画壁上所绘的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少女的垂髫。然而,此次的主人公不但是变化的记录者,也成为变化的动因:他进入画壁之中,并与女子结为夫妇。当其返回人世间时,此岸的世界,以及隔离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无不发生了改变。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译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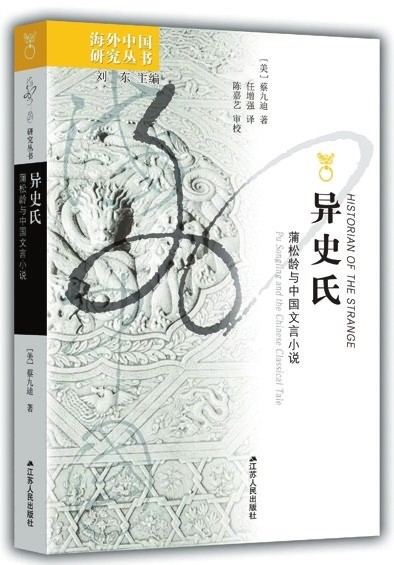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