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河源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同治中兴名臣,为已病入膏肓的满清,续命半个世纪。同治七年底,功高震主将赴直隶总督任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先后四次陛见中,太后垂询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军队的裁撤。曾氏日记,颇有记述:“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撤得安静?’对:‘安静。’”涵养极深的曾国藩,也难忍失望,其幕僚赵烈文录下曾氏怨怼:“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翌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对决,正式推开。一年之内,美国上千万的青年男女,受训参战。几年浴血,彻底改写了二战局面。二战胜利,修复战争创伤,成为摆在各国面前无从回避的急务。对美国而言,如何“根除士兵的不适应症”,安顿归休的1500万参战将士,是非同小可的浩大工程,没有成例可援。“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像周武灭商之后那样,铸剑为犁马放南山,并非易事。终战两年前,推动新政的罗斯福总统就对此难局,忧心忡忡,“请求国会起草法案,确保光荣的退役士兵得到承诺,他们可以进大学,可以通过国家提供的经费获得职业培训”。说穿了,不过国家预贷,推迟庞大的待业人群蜂拥入职,为经济体系消化吸纳劳动力提供缓冲。一个词:权宜。
这权宜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波折重重,争讼不断,条文不断修改。譬如,取消25岁的入学年龄限制;政府支持学习的最长时限翻倍,从2年增到4年;基础薄弱的老兵,“在校学习的时间延长到了9年”。总之,拆除了不利老兵入学的诸多门槛。法案修正案推出后,每位服役人员都收到跟战时特供的军版图书大小相似的宣传册。社会各界,包括“图书馆管理员再次行动起来”,用力所能及的方式,为退役大兵顺利“回归平民工作”提供程序、信息等多方面适应性帮助。结果,1945年2月 1日退役的150万军人,不到1%申请入学,局面令人沮丧。嗣后几年,彻底改观:“9年时间里,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大约780万老兵接受了教育和培训,总共有220万老兵注册了大学课程。从1947年到1948年,美国大学中50%的学生是退伍军人。”此前作为精英教育不言而喻象征的大学窄门,从此大开为国民教育。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吾国民间长期流传的这句俗语,表达着对一个行当的刻板歧视。类似偏见,有相当的普遍性。《法案》在美国,同样反对者众,不少“批评家认为退伍军人不想学习,没有兴趣读书”。只是退伍军人们后来在美国大学的杰出表现,就连那些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老兵是最优秀的学生”。而吃力追赶“就知道读书、读书,一切时间都在读书”的老兵的普通学生,甚至会在老兵学生“平均分提高者”的称号前面,冠以“该死的”诅咒。恨恨之意,溢于言表。虽然法案也未能促成退伍非裔士兵和女军人的普遍入学(要到19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才完全“男女同校”),但《纽约邮报》1945年春所鼓吹的“一支世界上最用功读书的军队”,在战后课堂上,依然延续着他们贯穿军旅的阅读习惯。那些无比珍惜时间,用知识二度武装起来的老兵大学生们走进课堂、踏上社会,焕发出的生产效能,远非《法案》倡导者、起草者、执行者们所逆料。
在壕堑、在散兵坑里的等待,漫长枯燥;“在炮弹袭击的间隙”掏出军版口袋书读上几页,死亡的威胁与恐惧,也减轻许多。可以说,二战为美国准备了最为集中的读书群体,“有些人从前只读报纸,主要是漫画报,从不读别的书(而现在也开始爱上读书)”。刚进入战时状态的美国,物资装备极为短缺,“为士兵提供图书,成为美军维持士气的战略性举措”。战前纽约图书馆协会发起向士兵捐赠图书,“胜利图书运动”募集的1800万册图书,极受欢迎,供不应求,直接间接促成了多方参与的战时图书协会成立。“由于协会制订了在军中大受欢迎的版式,以及对每月图书种类的精心选择,读书已经成为不可抵制的快乐。”1.23亿册便携的军版图书,就这样成为美军行装的标配,令并肩作战的盟军他国士兵眼红。“很多人在前线时已经读了柏拉图、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其他人读了历史、商务、数学、自然科学、新闻以及法律等学科的书。”四年战火间歇养成的阅读习惯,滋长的阅读能力,在生死存亡的刀锋时刻,为士兵构筑了一个超离残酷的精神世界,更为美国士兵们退役后进入大学,做了不期然的扎实训练。
《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一书,围绕着美国战前未雨绸缪,战时全力以赴以图书装备美军的两场运动,呈现出图书馆员、出版者、军方、物流、学术界、读书界的诸种样貌,揭示了现代战争或许为人忽视的一幕:思想武器不低于“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力量。
无心插柳的《法案》能绿树成荫,两次图书运动厥功至伟。这曲阅读的颂歌,不仅提供了一个审视二战的全新视角,在视频风行娱乐至死、文字阅读岌岌可危的当下,无疑也是极佳镜鉴:浮嚣世态中,阅读曾经提供过结实锚点。或者这就是《当图书进入战争》这偏门小众的作品,能一再重印的因由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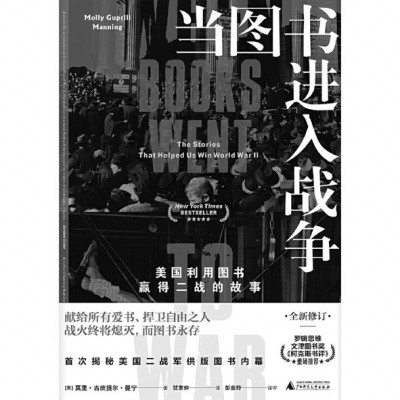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