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占鹏
敦煌研究院杨秀清先生一直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曾利用敦煌童蒙写本论述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和思想,为我们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敦煌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常识、经验与规则。从2007年起,杨秀清先生关注到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儿童图像,尝试运用“图像证史”与“形象史学”的方法,分析这些儿童图象的来源与意涵,先后发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研究》(一、二、三)、《情态任天然——敦煌壁画中的古代儿童游戏》(上、中、下)等文章。2024年2月,杨秀清先生《敦煌壁画中的儿童生活》(以下简称《敦煌儿童》)一书由未来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收集、整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莫高窟等石窟壁画中的儿童图像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中古时期儿童形象和生活的具象。
《敦煌儿童》共分八章,分别是“绪论”“新生命的诞生与人生的初始”“伦理亲情下的儿童生活”“敦煌壁画中的儿童游戏”“敦煌壁画中的童子拜佛图像与儿童的佛教信仰”“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学生生活”“敦煌壁画中的儿童服饰”“余论”。
首先,作者提出“图像证史”与“形象史学”的方法对敦煌壁画中儿童形象研究的意义,高屋建瓴,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调。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历史研究中著名的“二重证据法”。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在这些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带入更广阔的领域之时,缘起于西方艺术史领域的“图像证史”,即以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理解和重构过去的研究方法,亦开始走入了我国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中国形象史学、图像史学等新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的建构。对于国内学者提出的“形象史学”的概念,《敦煌儿童》中评价道,其既吸收了西方“图像证史”的观念和方法,也继承了我国自古就有的“左图右史”、图史互证的传统,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必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敦煌儿童》统计出莫高窟、榆林窟共534个洞窟中的儿童图像千余身,考图像之所据,用之与文献互证,阐述中古儿童史,进而开拓了童蒙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其次,《敦煌儿童》按照儿童的诞生、成长过程,对壁画中的儿童图像进行了分类,探讨了相关儿童形象的出典和意涵,并将落脚点归于唐宋时期的儿童生活。第一章的“新生命的诞生与人生的初始”,其关注点就是初生婴儿图像,作者列举了敦煌壁画中释迦和弥勒“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步步生莲”以及“阿夷占相”“太子沐浴”等图像,指出这些神话故事反映了人们在乞求母子平安的同时,对新生命未来命运的强烈期待。作者特别关注到敦煌壁画中的化生童子,认为化生童子的出现,与入唐以来西方净土经变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同时指出,化生童子在西方极乐世界里,是以无量寿佛的“百姓”身份出现的,因而反映的是儿童现实生活的画面,也是对儿童生命本真的赞扬。
《敦煌儿童》第二章“伦理亲情下的儿童生活”讲述父母对儿童的呵护,关注点为婴幼儿图像,列举了敦煌壁画“鹿母夫人故事”“母语婴儿喻”“如子得母”“栏车相拥”“负子而行”“携子而行”图等,指出这些壁画充分表现了儿童的天真无邪与父母亲的慈爱之情,真实再现了儿童生活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母子情深和儿童成长的轨迹。也有壁画中呈现出母亲携两儿过河遭遇不幸和“二母争子”“夜叉抱子”的故事,表现了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磨难,弥足珍贵。
第三章“敦煌壁画中的儿童游戏”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壁画中的儿童游戏,关注点为幼童图像。书中列举了骑竹马、玩沙土、骑狮子、骑牛、爬树和采花、百戏杂技、步打球、水中嬉戏八种常见的游戏,其中百戏杂技又分顶竿、叠罗汉、倒立、掷倒、下腰、玩木偶。每种游戏都配了一幅或是多幅高清彩色插图,并与传世记载和佛经相互印证。显然,较之传世典籍的记载,敦煌壁画呈现的儿童游戏种类更多,且壁画形象展示出游戏的样貌、儿童的身姿、玩具的形制,鲜活而生动,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儿童游戏和儿童生活的认识。
其三,《敦煌儿童》通过考察敦煌壁画中的童子拜佛形象,为探寻“童子拜佛”经典来源提供了一种合理思路。《敦煌儿童》第四章“敦煌壁画中的童子拜佛图像与儿童的佛教信仰”着重考察这一问题。作者指出,在佛经中虽然尚未找到“童子拜佛”的确切依据,但是《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贤愚经》卷第三《阿输迦施土品》、《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三、《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受决定记品》中,或言佛陀前生为童子时,因为向佛献花或布施等行为,最终获得福报,得道成佛;或言阿育王为儿童时,向佛布施,最终得为转轮王等,这些记载大概与后来童子拜佛的由来有着比较明确的关联。唐宋时期,佛教成为敦煌社会中最主要的信仰,佛教信仰弥漫社会各个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中,敦煌儿童难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作者进而指出,依据经典记载,儿童对佛的布施与供养,是在游戏中完成的,而很多儿童游戏是对成人生活的模仿,社会生活中的佛教生活内容,自然会为儿童模仿和学习。
其四,《敦煌儿童》全面整理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儿童服饰,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探察唐宋儿童生活添加了色彩。由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较少,学界对于古代儿童服饰缺乏深入认识。敦煌蒙书《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等杂字书中罗列有很多服饰,但由于缺乏图像搭配,难以将服饰的名称与形貌结合。作者对敦煌石窟中的儿童图像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在第六章“敦煌壁画中的儿童服饰”中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对服饰的种类进行了梳理,并附高清彩图,让我们对唐宋时期敦煌儿童服饰有了初步了解和直观印象。
《敦煌儿童》共介绍儿童服饰13种,分别是荷叶帽、抹额、围嘴、肚兜、裲裆、半臂小袴、背带裤、袴褶、袍服、襦群、平头履、翘头履、乌皮靴。从书中所附壁画插图来看,基本上呈现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儿童的穿着特点,而且由于佛教壁画的特性,壁画中的童子穿着普遍较为清凉,基本上是着内衣或夏装,甚至只着短靴,且衣着颜色鲜艳,让观众得观肚兜、裲裆、半臂小袴、背带裤等的具体形制和配色。
部分壁画中的儿童服饰还体现出民族交流交融的特点。如抹额常见于汉族武士形象,但是莫高窟第359窟东壁门南维摩诘经变中一成人和儿童均着吐蕃服装,其中儿童头裹抹额,说明抹额不仅流行于汉族,也流行于其他民族。又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中儿童所穿背带裤,并非中原王朝的传统服饰,而是从古代波斯传入西域,再从西域传入内地的。
其五,《敦煌儿童》将壁画中的儿童形象与传世文献、敦煌文献结合,资料详实,相互释证,探源发微。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洗浴及满月之礼”时提出,新生儿出生后,要进行三日洗儿礼,这也是唐宋时期儿童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作者运用传世文献《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旧唐书》《资治通鉴》《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文献论述了唐以来的新生儿洗浴之礼,又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河012号(BD06412)、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做了论证,然后才回到莫高窟第290窟、第61窟壁画中的“九龙灌顶”和“太子洗浴”图,指出“这些壁画内容表达的正是为新生儿童沐浴的象征意义,由此引伸出世俗间为新生儿洗浴的礼仪是非常有可能”。在论证过程中,还举出了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和英国博物馆藏Ch.0039、Ch.xxii.0035等绢画,以作补充。可以说,《敦煌儿童》在保持语言通俗、鲜活的同时,学术论证严谨,实现了图史互证、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互证。
以往童蒙文化研究研究,囿于传世资料和理论,主要集中于蒙学教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儿童游戏等方面。杨秀清先生另辟蹊径,以图释史,发掘了童蒙文化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视野,可以说发图像儿童史研究之先声。笔者相信,随着出土资料的更多发现,研究新视野的不断开辟,中国古代童蒙文化研究必将迈入更加广阔的领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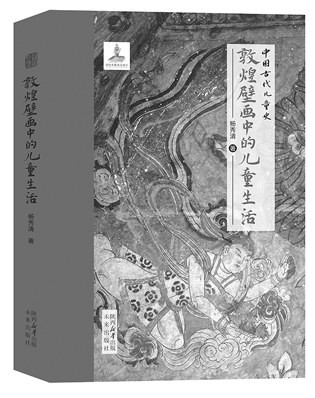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