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陇上到吴越》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刘进宝教授的一部学术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学术普及性短文、发言稿、纪念文章、书评等文字23篇。作为一个敦煌学领域的初学者,笔者在研读《从陇上到吴越》一书的过程中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指导。
一、初学者的入门指南
首先,本书阐明了敦煌学的基本概念,提示我们从中华文化的根源出发,树立正确、客观的研究意识。书中收录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一文,从莫高窟的创建、敦煌文献所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敦煌的发展演变、匈奴人和月氏人的起源和迁徙、“吐火罗语”的来源等多个方面,说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吸收了中亚、西亚、南亚文化后产生的地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才是敦煌文化的“根”与“魂”。《从提出背景看“丝绸之路”概念》分析了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其中学术背景主要是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特别是英国学者亨利·裕尔对通往中国之路的考证;而李希霍芬研究中国的政治背景,则是适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学者大力考察、搜集情报,以达到便利其经济扩张的目的,我们研究者需将“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背景与其独到的科学价值分开看待。
其次,本书为历史学的初学者们提供了学习方法的指南。书中《学会读书和思考》一文,对比了不同时代读书学习不同的特点和环境,强调了基础学科的重要性,明确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相,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要摒弃一切杂念的干扰,潜心追求真理,对学术贡献要做出正确的评价。该文章的独到之处,尤在于列出了一张具体书单,包括《文史知识》“治学之道”专栏、名家名作《治史三书》《读书与治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上学记》《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师门问学录》等文章著述,给初入门的学生以实用的指导。
再次,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的多篇书评,具体演示了如何进行读书与思考。例如,《敦煌学的珍贵历史记录——读〈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就做了一次阅读的示范。作者不是孤立地盯住《敦煌人生》这本书,而是将该书放在纵向、横向的脉络里发现其价值。通过纵向地与敦煌学术史资料对比,指出该书的价值,即指出了段文杰对临摹之学的创造性贡献、对敦煌艺术来源的思考,提供了对莫高窟编号的新材料、敦煌艺术与新疆石窟的联系、与印度佛教艺术的联系等等。又能从横向的角度发现该书与部分同类传记相比,具有客观真实、不拔高、不虚美的特点。《敦煌大众思想:“大众思想史”的一个个案》一文,从“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敦煌大众与大众文化的新探索”“如何理解佛教的大众文化”三个角度进行评价,尤其是透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文化史思潮与文化热的背景,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的学术视野。
胡适曾对年轻人说过一句话,“为学要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从陇上到吴越》的作者刘进宝教授,在上课时不无遗憾地感慨说,“过去的学者往往是金字塔式的学者,而现在很多是旗杆式的学者”,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然而,如作者所演示的那样,进行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尝试掌握系统化、全景式的通识体系,或许是我们再次塑造“金字塔”的第一步。
二、敦煌学术史史料宝库
“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学者队伍发展壮大、学科范畴持续演进,敦煌学的发展本身又成了研究的对象。因而对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既应保持记录历史的自觉,又有梳理、研究学术史的必要,《从陇上到吴越》正是一部记录、研讨敦煌学术史的佳作,为读者打开了探望敦煌学的一扇窗口。
1981年,有关日本学者藤枝晃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传曾引起学界、政界与民间的强烈震动,对此,刘进宝教授曾两次专文辨析。收录在《从陇上到吴越》中的《吴廷璆先生与敦煌学》一文又补充了夏鼐日记、张国刚和杨栋梁回忆文章中的有关资料,进一步证实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之语确是关心我国学术事业的吴廷璆所说,并非出自藤枝晃之口。
《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的写作,既有作者段兼善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部分,也有根据传主的日记、笔记、论文考论而成的部分,其中难免有失误之处。例如有关甘肃省敦煌学学会成立大会的情况,作为当时的会务人员之一,刘进宝在书评中指出会议召开时间并非传记所说的1991年12月31日,而是此前的12月24至25日。而且当时段文杰正在印度考察,实际上没有出席会议,书评对大会选举的甘肃敦煌学会领导名单也做了补正。1993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学术会议”,同为参会学者的刘进宝也指出,段文杰原本计划参加,但或许是由于身体原因,实际上没有成行,并援引李永宁所作的会议简记给出了确切的证据。
《从陇上到吴越》还在集结诸多珍贵史料、总结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揭示了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何在。如《敦煌学术史研究的新使命》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打破中古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的界限,将中古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研究与近现代的档案、报刊、回忆录、书信、日记材料结合起来,将强调学术成果的狭义的“敦煌学学术史”扩展为“敦煌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等,在敦煌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
三、学者人格的纪念丰碑
本书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学者的人格,其中作者对自己的老师朱雷先生用笔最多。2021年8月,朱雷先生逝世,作者撰写了多篇文章,带我们领略朱雷教授的学术人生。
1974年至1986年期间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由唐长孺先生领导、朱雷等先生参加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负责,整理组远赴新疆、北京等地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整理组先是避入故宫武英殿,而后又转至上海,始终坚持工作。由于研究工作的劳累、生活条件的艰苦严重伤害了朱雷先生的身体,他前后八次发生胃出血,但仍就坚守在工作岗位上。1974—1986年,朱雷在十多年中长期工作在新疆、北京的研究一线,“偶尔回家时,两个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偷偷问妈妈这个人怎么还不走? 还要住在我们家?”
朱雷教授严于律己,在担任许多职务、负责经费分配的情况下,从未申请出版过自己的论著,即使这样做既符合规定也十分便利,就连送给学界师友的赠书也是自己出资购买的。同时又能做到宽以待人,从不埋怨别人的不是,不说其他单位或学者的研究不足,不抱怨缺少经费。朱雷先生这样的性格延伸开来,也就会对亲近的人和学生们严格要求,说“过分强调缺钱,发牢骚啊,不好”。
除了朱雷先生外,《从陇上到吴越》还为读者呈现了学贯中西、关心敦煌学发展,为改变“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而奔走疾呼的吴廷璆先生;性格直率倔强、深耕宋史和西北史地教学科研工作的陈守忠先生;“打不走的敦煌人”施萍婷先生;无私提携晚辈后学、淡泊名利的刘光华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风范。
《从陇上到吴越》也是作者自身的一段学术生命史。刘进宝教授是甘肃兰州人,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曾用名“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学习、任教,在敦煌学、隋唐史、丝绸之路、西北史地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2002年,作者调入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至今工作于浙江大学,经历了“从陇上到吴越”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刘老师一直致力于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的教学、研究,尤其是在担任浙大历史系主任、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在资源整合、队伍建设、科研推进、学术著述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作者身在吴越、心系陇上的治学情怀,闪现于全书的字里行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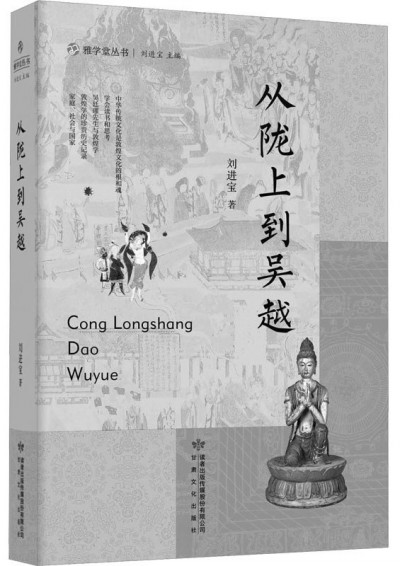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