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一
屈原(前339? -前283)的《离骚》是一首空前的抒情长诗,凡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其中前一半大谈政治,后半则因政治失意转向恋爱,并以“求女”为线索直达篇末。
全诗可以分为两大段,一过渡,一结语。第一大段从诗的开头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内容是说诗人在楚国政治生活中的斗争与失败。第二大段从“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曲顾而不行”。朱熹《楚辞集注》云:“跪而敷衽,以陈如上之词于舜,而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所以埃风忽起,而余遂乘龙跨凤以上征也。然此下多假托之词,非实有是物与是事也。”这是很好的解说,这里大抵离开楚国政治纷争的现实,而进入瑰丽缤纷的幻想世界,抒写诗人的求索和牢骚。
第一大段写现实,第二大段多假托之词,介乎两段之间的部分,即从“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到“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巾之浪浪”,是一个过渡性的段落:既是由现实转入幻想的过渡,也是由大谈政治到转而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过渡。女嬃对抒情主人公的责备和规劝充满了现实的内容,屈原不大相信她的话,于是跑到重华那里去陈词,已渐有假托的色彩,所陈之词尽管主要还是政治生活方面的,但他在这一方面已经完全失望了,便流着眼泪告别政治,转而打算以“求女”来改变自己“茕独”的处境,并由此引出《离骚》的后一半来。“乱曰”云云是全诗的结语,或曰尾声。
二
屈原本来是楚国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出身于公族(与王室同姓),德高能强,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相当于副首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的政治抱负是加强法治,举贤任能,建设“美政”,联齐抗秦。可惜他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诬陷,糊里糊涂的怀王疏远了屈原,拒不接受他提出的正确主张,降职任用,调出首都;结果国家越来越糟,最后怀王本人竟被骗到秦国去,就死在那里。继任的顷襄王更是一个糊涂虫,听信谗言,干脆将屈原流放到江南,后来国事日非,亡国之势日趋严重,屈原悲愤之至,遂投汨罗江自杀殉国。
《离骚》作于屈原被迫离开首都前往汉北之时,诗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遭受忧患的诗人从自己的家族出身说起,强烈地抒写家国情怀,诗中充分写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更写到自己惨遭打击、被疏远之后的哀伤怨愤,但他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高洁: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服……
佩缤纷其繁饰兮,
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这种不惧高压坚守高尚的硬骨头精神,是屈原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值得永远保爱!
看到老弟这样倔强,屈原的姐姐赶紧出来教训他,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你务必要放随和点,保住自己才是! 亲属劝人一般不讲大道理,只注意安危。于是诗人离开故地到大舜的陵墓那里去寻求精神力量,他始终不肯屈服妥协,在大局问题上仍然坚持己见,但国家大事自己已经没有参与的资格了,只好转而进入私生活的领域。他在诗中写道:
阽余身而危死洗,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故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巾之浪浪。
诗人流着眼泪离开政坛,走上了求女的长途。
三
《离骚》中的“求女”是屈原以幻的方式来写自己私生活中的感情,写他本人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以后转而寻找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来填补心灵上的空缺,只不过他身在情场而仍然未能完全忘却官场,从事恋爱而仍然未能完全忘却政治而已。
屈原的求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叩阍求女。向重华陈词以后,诗人朝发苍梧夕至玄圃,并由此继续上征去叩击天门,可惜不得其门而入。诗中全然没有提到求见天帝而只说他此行的目的是求天女: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阊阖而望余。
时暧暧其将罢兮,
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白水兮,
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诗人求见的对象就是末一句提到的高丘之女。高丘指神话中的昆仑山,或称昆仑丘。据说这乃是接通天地之山,也是众神之所居。古人以为昆仑山分为上中下三层,天帝住在最上层,诗人上征到这里来,为的是追求这里的神女。诗中“结幽兰而延伫”一句分明写出了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但阊阖之门亦即所谓天门从来是不肯轻易打开的,屈原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哀叹“高丘之无女”。当诗人发此哀叹时,他已经走下昆仑了,但还有些不甘心,所以反顾而流涕,并且终于把此行的目的清楚地交代了出来。按诗中的描写,诗人的路线是先上后下,先由苍梧出发,上征至县圃(即玄圃),在这里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天庭冲刺,叩阊阖之门求女;可惜不能得手,遂济白水,登阆风,阆风即玄圃,诗人回到了昆仑的中层,这时回望最高层,不胜悲哀。上天求女宣告失败。
第二个阶段可称为下山求女。求高丘之女既不可得,诗人遂转而去求“下女”:“及容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下女”即下文所咏叹的宓妃、有娀氏之佚女和二姚,她们的地位也相当的高,但相对于昆仑极顶的天女来说,她们只能称为“下女”。可惜这一阶段的“三求女”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于是诗人感慨道: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第一句总述到此为止的一系列求女的失败。诗人的求女本是政治上失意以后不得而已求其次的行为,现在求女又告失败,于是不免又回过头去寄希望于政治,幻想“哲王”(具体说就是楚怀王)忽然觉悟,自己东山再起,为国家效力。可是“哲王”仍然糊里糊涂,这一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希望。
既然哲王不觉悟,那么只好再来求女,天上地下他都已求过求之而不得,再求就得另寻出路,非出国不可了。出国在屈原来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决策以前要再三研究反复思量,于是要问卜求神,这样诗中就出现了占卜、降神两大情节。先是请教灵氛占卜。诗人向灵氛提出的问题就是能否出国求女,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是如果真的出了国,则自己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将彻底结束;他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楚国的政治舞台上来,而一旦出了国,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出国一事,决不能草率地感情用事,于是他又去请教巫咸,请他来决定自己的去留,解决心中的“犹豫”和“狐疑”。巫咸的回答畅论圣君贤臣必然合拍,和衷共济以定天下,他明确指出诗人可以在外国找到政治上的出路,同时兼及求女,希望他趁人尚未老时赶紧解决问题。按照巫咸的结论,如果屈原出国,不仅可以获得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同时也会有政治上的遇合;爱情,诗人是要的,但是在楚国之外有什么遇合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毕生追求的无非是楚国的强大,离开了祖国,“美政”还有什么意义!
四
《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尾声。当诗人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排除一切疑虑,开始实行其先“上征”以出国的计划时,他在半空中“忽临睨乎旧乡”,突然决定立即取消出国的打算,取消求女的宿愿,复回其故国。他的感情如此之强烈,以至影响了他的仆人和坐骑:“仆夫悲余马怀兮,蜷曲顾而不行”。这样一个定格的镜头具有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爱国之情压倒一切,先前的种种考虑虽然都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爱国恋乡的情结面前,它们全都顷刻烟消云散。与其出国求女,还不如留在故国,隐于草野,再看情形: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再不追求神女,更不出国,姑且隐遁。“彭咸”是何许人,“从彭咸之所居”具体内容如何,现在没有材料能够直接做出说明,但从另外三篇楚辞文本即《卜居》《渔父》《招隐士》中可以推测彭咸乃是一位隐遁的高人,屈原打算走他的道路。
《渔父》写屈原被怀王疏远放逐后“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隐士渔父劝他不必固执己见,要与时推移;《卜居》写屈原向占卜专家郑詹尹请教,詹尹听了他的陈述以后也拿不出好办法,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自行决定吧。《招隐士》称屈原为隐士,劝他走出山林水泽,回到体制之内来。
综合这些文本中透露的信息,可以推知屈原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便隐退于野,清理思想,以规未来。他没有马上自杀,后来的投汨罗江是在若干年后楚国面临亡国危机之时,终于下决心以身殉国。
从政不合而上下求女,求女不得而考虑出国,出国不忍而将“从彭咸之所居”——从几度“求女”到终于隐遁,屈原在政治失意以后经历了种种思想煎熬,一时还没有结果。至于他下决心以死报国,那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同《离骚》没有直接的关联。
不久前获悉,一位国外学者魏宁(Nicholas M. Williams)在研究《离骚》的最新论文(收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Chine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一书)中认为屈原最终扬弃了世俗的情感——对君王和身边小人的怨恨、对楚国前途的担心以及自己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失望,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升华(sublimate)。屈原没有自沉汨罗,而是过上了隐居生活,成为了巫师的朋友。《离骚》最后一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商朝大夫,而是《山海经》海内西经和海外西经中提到的“巫彭”和“巫咸”,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详见顾钧《“离骚”的四种翻译方法》,《文汇报》2022年4月3日《文汇学人》版)。这样的见解似乎未免走得过远,但有一点大有道理,这就是屈原所说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并不是指决心投水自杀,而是表示将退出纷争,走向隐遁。
可是历来的注家往往不肯如实地将“求女”看作诗人感情生活中的事情,而把它千方百计地往政治上拖去,其思路与解释《诗经》的儒家经师们一定要把不少优美的情诗解读出许多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来如出一辙。在经师的眼中,《诗经》中的作品并不是诗,而是经,总是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和教训。《离骚》本来是诗,但后来也成了“经”,于是其中也就必然要包含许多大道理大教训,何况《离骚》中本来就有大量的政治内容,因此,将其中并非政治的东西也说成是关于政治的隐语乃是很容易也很有必要的事情。
政治家屈原在不得已而离开政局中心以后内心一度失去平衡,转而用寻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来填补心灵上的空白,找一个避风的港湾让自己得到休息和慰藉,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由于楚文化中有着甚深的人神恋爱传统,他写自己的爱情便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政治和爱情乃是《离骚》的两大主题。可是到了深受“诗教”教条浸淫的儒家学者们的眼睛里,诗人笔下那些沉痛炽热的诗情就非得翻译成君臣之际的关系不可,关于“求女”的种种“比兴”式过度诠释遂大行其道,并且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不易动摇。屈原在《离骚》之末表达的隐遁之意,也被一笔抹杀,一味强调他决心以死相争。殊不知这样一来他的生平经历和若干楚辞中的作品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说。
但也有不为儒家诗教教条束缚的高人,鲁迅先生在1907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 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
鲁迅深刻地看出了“哀高丘之无女”等等内容乃是涉及“眷爱”的“芳菲凄恻之音”;鲁迅批评诗人反抗精神不够,那是因为鲁迅当年正醉心于“摩罗诗人”,反观中国传统文学,遂觉得即使是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也还是缺乏与传统决裂、向传统挑战的反抗精神。这一批评带有鲁迅早期浪漫主义的色彩,对古人或不免责之过严,后来他修订了自己早年的这一意见,指出屈原的《离骚》等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鲁迅全集》第9卷),这里有着非常重要的观察:屈原之旨甚明,求女就是求女,并无政治方面的微言大义。
五
《离骚》是一首关于政治和恋爱的抒情长诗,美政、美人,屈原都想要,而他最深的感情,则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美好的旧乡故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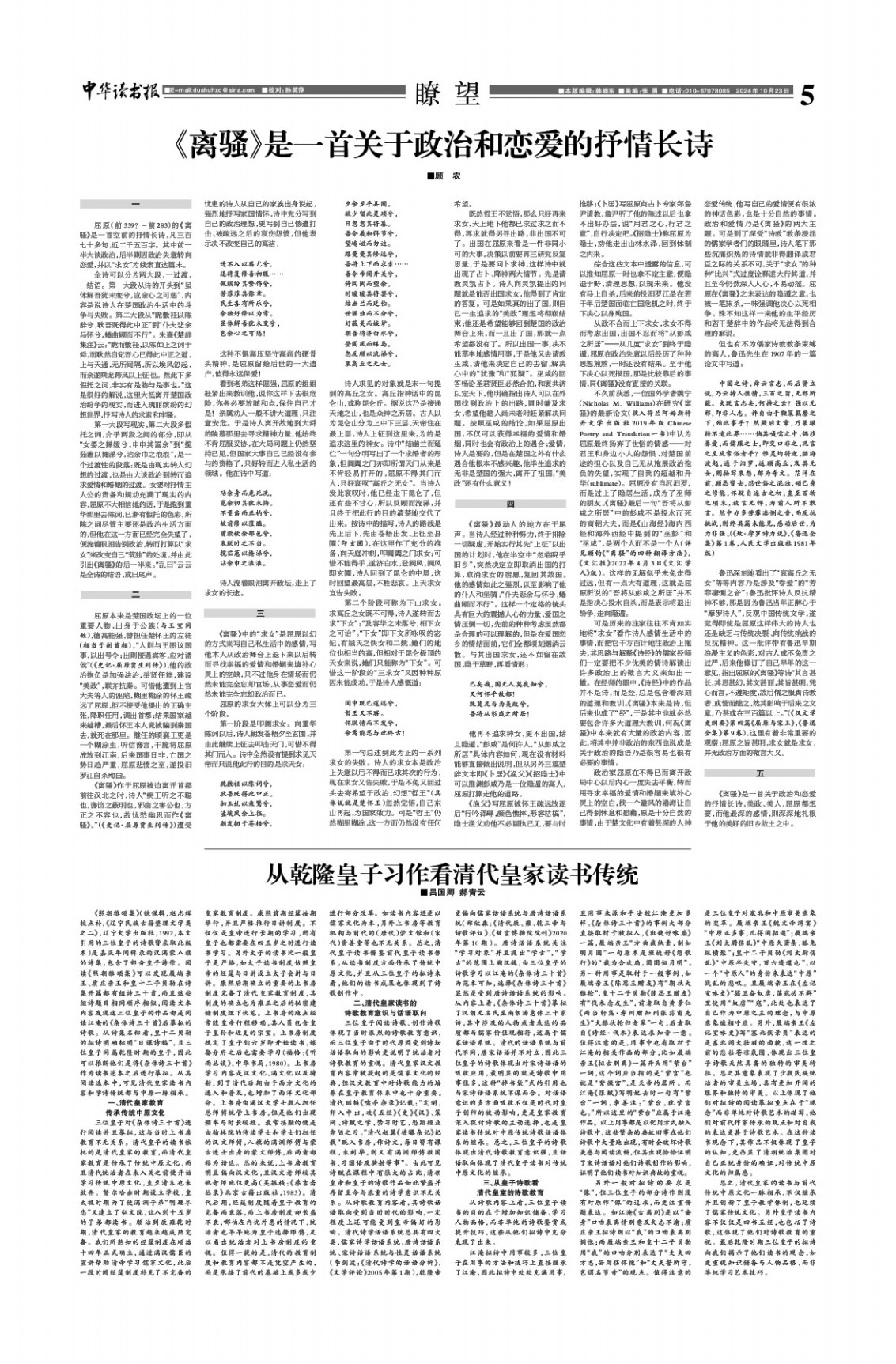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