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卿 郝青云
《熙朝雅颂集》(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辽宁民族古籍整理文学类之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本文引用的三位皇子的诗歌皆采取此版本)是嘉庆年间辑录的汉满蒙八旗的诗集,包含了部分皇子诗作。阅读《熙朝雅颂集》可以发现履端亲王、质庄亲王和皇十二子贝勒在诗集开篇都有组诗三十首,而且这些组诗题目相同顺序相似,阅读文本内容发现这三位皇子的作品都是阅读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后摹拟的诗歌。从诗集名称看,皇十二贝勒的拟诗明确标明“日课诗稿”,且三位皇子同属乾隆时期的皇子,因此可以推断他们是将《杂体诗三十首》作为读书范本之后进行摹拟。从其阅读选本中,可见清代皇家读书内容和学诗传统都与中原一脉相承。
一、清代皇家教育传承传统中原文化
三位皇子对《杂体诗三十首》进行阅读并且摹拟,这与当时上书房教育不无关系。清代皇子的读书依托的是清代皇家的教育,而清代皇家教育是传承了传统中原文化,而且清代统治者在未入关之前便开始学习传统中原文化,直至清末也未放弃。努尔哈赤时期设立学校,皇太极时期为了使满洲子弟“明理尽忠”又建立了弘文院,让八到十五岁的子弟都读书。顺治到康雍乾时期,清代皇家的教育越来越成熟完备。我们所熟知的经筵制度在顺治十四年正式确立,通过满汉儒臣的宣讲帮助清帝学习儒家文化,此后一段时间经筵制度补充了不完备的皇家教育制度。康熙前期经筵按期举行,并且严格推行日讲制度。不仅仅是皇帝进行长期的学习,所有皇子也都需要在四五岁之时进行读书学习。另外太子的读书比一般皇子更严格,如太子读书制度仿照皇帝的经筵与日讲设立太子会讲与日讲。康熙后期确立的重要的上书房制度完备了清代皇家教育制度,其制度的确立也为雍正之后的秘密建储制度埋下伏笔。上书房的地点经常随皇帝行程移动,其人员包含皇子皇孙和近支的宗室。上书房制度规定了皇子们六岁即开始读书,嫁娶分府之后也需要学习(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0)。上书房学习内容是汉文化、满文化以及骑射,到了清代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和普及,也增加了西洋文化部分。上书房由满汉大学士数人担任总师傅统管上书房,但是他们出现频率与时长较短。最常接触的便是由翰林院的侍读学士和学士们担任的汉文师傅,八旗的满洲师傅与蒙古进士出身的蒙文师傅,后两者都称为谙达。总的来说,上书房教育明显偏向汉文化,且汉文老师较其他老师地位更高(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清代后期,经筵制度随着皇子教育的完备而衰落,而上书房制度却长盛不衰,哪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统治者也早早地为皇子选择师傅,足以看出统治者对上书房制度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承接了前代的基础上或多或少进行部分改革。如读书内容还是以儒家文化为本,另外上书房等教育机构与前代的(唐代)崇文馆和(宋代)资善堂等也不无关系。总之,清代皇子读书借鉴前代皇子读书体系,从读书制度方面传承了传统中原文化,并且从三位皇子的拟诗来看,他们的读书成果也体现到了诗歌创作中。
二、清代皇家读书的诗歌教育意识与话语取向
三位皇子阅读诗歌、创作诗歌体现了当时浓烈的诗歌教育意识,而三位皇子由于时代原因受到诗坛话语取向的影响更说明了统治者对诗歌教育的重视。清代皇家汉文教育内容常被提起的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但汉文教育中对诗歌能力的培养在皇子教育体系中也十分重要。清代昭梿《啸亭杂录》记载:“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恐蹈矩业弇陋之习。”清代赵翼《檐曝杂记》记载“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由此可见诗赋在课程中有很大的占比,清朝皇帝和皇子的诗歌作品如此繁盛并存留至今与浓重的诗学意识不无关系。从诗歌教育内容看,其诗歌话语取向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受到皇帝偏好的影响。清代诗学话语系统总共有四大类,儒家诗学话语系统、唐诗话语系统、宋诗话语系统与性灵话语系统(李剑波:《清代诗学的话语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乾隆帝更偏向儒家话语系统与唐诗话语系统(郑欣淼:《清代康、雍、乾三帝与诗歌评议》,《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唐诗话语系统关注“学习对象”并且提出“学古”,“学古”的范围上溯汉魏,由三位皇子的诗歌学习以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为范本可知,选择《杂体诗三十首》显然是受到唐诗话语系统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杂体诗三十首》摹拟了汉朝无名氏至南朝汤惠休三十家诗,其中涉及的人物或者表达的品质都与儒家价值观相符,这属于儒家话语系统。清代的话语系统与前代不同,唐宋话语并不对立,因此三位皇子的诗歌体现出对宋诗话语的吸收应用,最明显的就是诗歌中用事很多,这种“掉书袋”式的引用也与宋诗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对话语意识的多方面吸收不仅是时代对皇子创作的被动影响,更是皇家教育深入探讨诗歌的主动选择,也是皇家读书传统对中原传统诗歌话语体系的继承。总之,三位皇子的诗歌体现出清代诗歌教育意识强,且话语取向体现了清代皇子读书对传统中原文化的继承。
三、从皇子诗歌看清代皇室的诗歌教育
从诗歌内容上看,三位皇子读书的目的在于增加知识储备、学习人物品格,而非单纯的诗歌鉴赏或提升技巧,这些从他们拟诗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江淹拟诗中用事较多,三位皇子在用事的方法和技巧上直接继承了江淹,因此拟诗中处处充满用事,且用事来源和手法较江淹更加多样。《杂体诗三十首》的事例大部分直接取材于被拟人,《班婕妤咏扇》一篇,履端亲王“方曲裁纨素,制如明月圆”一句原本是班婕妤《怨歌行》的“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月明”。另一种用事是取材于一般事例,如履端亲王《陈思王赠友》有“期扶大雅轮”,皇十二子贝勒《陈思王赠友》有“伐木念友生”,前者取自黄景仁《两当轩集·寿州赠知州张荪甫先生》“大雅扶轮归老辈”一句,后者取自《诗经·伐木》表达求知音一意。值得注意的是,用事中也有取材于江淹的相关作品的部分,比如履端亲王《拟古别离》一篇开头用“紫台”一词,这个词应当指的是“紫宫”也就是“紫微宫”,是天帝的居所。而江淹《恨赋》写明妃去时一句有“紫台”一词,李善注:“紫台,犹紫宫也。”所以这里的“紫台”应属于江淹作品。以上用事都是以化用方式融入诗歌中,这些繁杂的典故旧事在他们诗歌中大量地出现,有时会破坏诗歌美感与阅读流畅,但其出现恰恰证明了宋诗话语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证明了他们读书对知识典故的重视。
另外一般对拟诗的要求是“像”,但三位皇子的部分诗作则没有对原作“像”的追求,而更注重借题表达。如江淹《古离别》是以“妾身”口吻表离情别意及矢志不渝;质庄亲王拟诗则以“我”的口吻表离别惆怅;而履端亲王和皇十二子贝勒用“我”的口吻分别表达了“丈夫四方志,安用伤怀抱”和“丈夫誓所守,岂谓名节奇”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皇子对塞北和中原审美意象的变革。履端亲王《魏文帝游宴》“中原正多事,几得闲招邀”;履端亲王《刘太尉伤乱》“中原久萧条,狐兔纵横聚”;皇十二子贝勒《刘太尉伤乱》“中原半失守,百六逢邅屯”,以一个“中原人”的身份来表达“中原”战乱的悲叹。且履端亲王在《左记室咏史》“骠卫奋奴虏,荡寇功不群”里使用“奴虏”“寇”,此处也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原之主的理念,与中原意象遥相呼应。另外,履端亲王《左记室咏史》写“塞北恢景员”表达的是塞北阔大壮丽的面貌,这一改之前的悲壮苍凉氛围,体现出三位皇子诗歌天然具备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总之其意象表现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审美立场,具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和独特的审美。以上体现了他们对拟诗的阅读摹拟重点在于“观念”而非单纯对诗歌艺术的描写,他们对前代作家传承的观点和对自我的表达更甚于诗歌艺术。在这种读书观念下,其作品不仅体现了皇子的认知,更凸显了清朝统治集团对自己正统身份的确证,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归属感。
总之,清代皇家的读书与前代传统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不仅继承并且创新了皇子教学体制,也延续了儒家传统文化。另外皇子读书内容不仅仅是四书五经,也包括了诗歌,这体现了他们对诗歌教育的重视。最后乾隆时期三位皇子的拟诗向我们揭示了他们读书的观念,如更重视知识储备与人物品格,而非单纯学习艺术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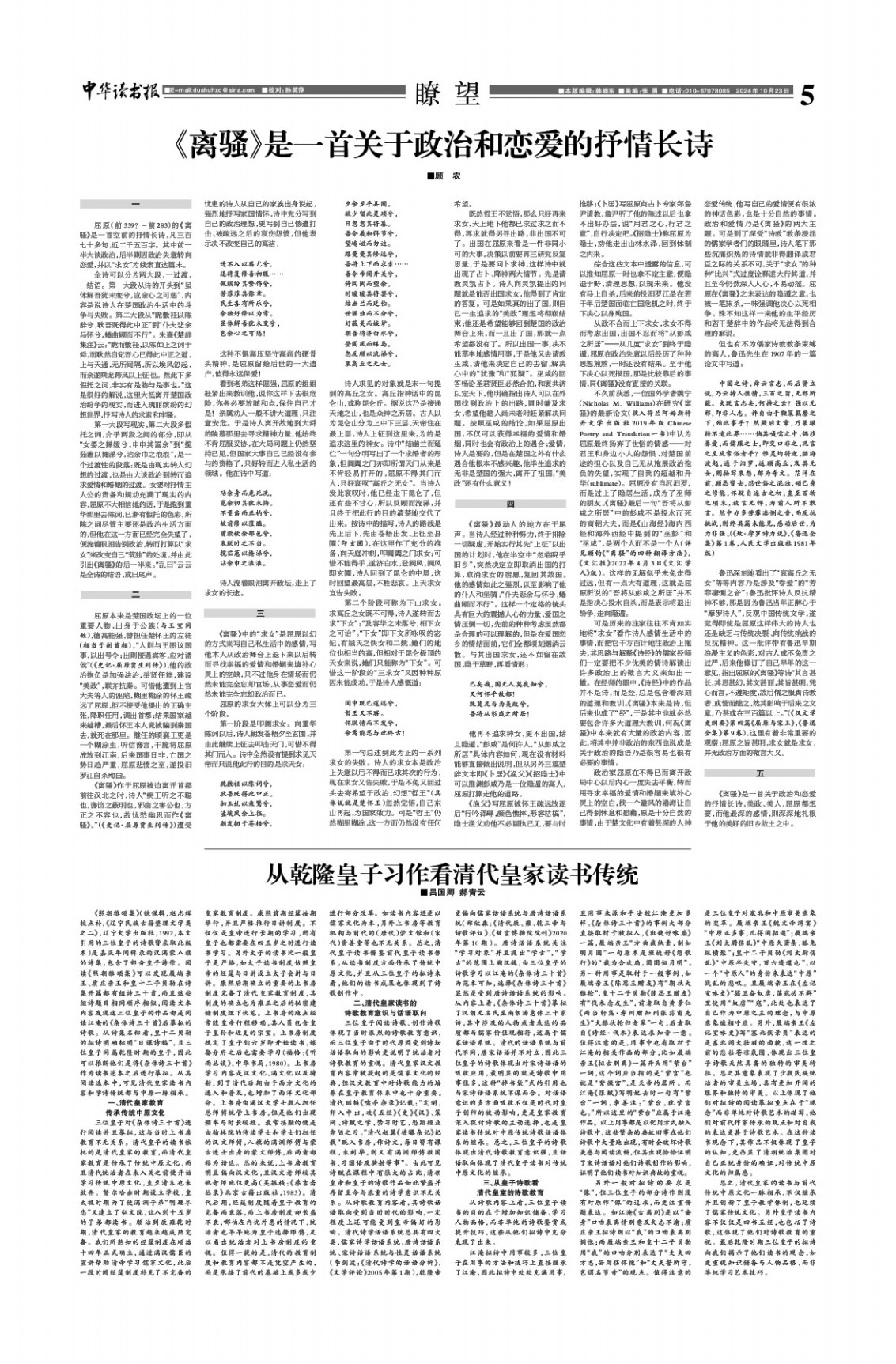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