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姗姗
在启蒙时代的熠熠群星中,竟然是那个一无是处、毫不起眼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成为了最具原创性、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同时代的人越是了解卢梭的过去,知道他从未上过一天学,在38岁一举成名之前断断续续地打着零工,做过雕刻匠学徒、男仆、冒牌的音乐老师、巡游修道士的翻译、土地登记处职员、家庭教师、作曲家、使馆秘书等等——大多数工作都表现不佳,每一种工作都干不长久——就越是震惊于这样一个人居然能成为杰出作家! 无论是18世纪的普通公众,还是乌德托夫人和卢森堡公爵这样的赞助人,无论是狄德罗、达朗贝尔这样的哲学家朋友,还是伏尔泰这样伟大的对手,都还没有意识到,卢梭绝不仅仅是启蒙时代的杰出作家之一,更是整个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利奥·达姆罗施(Leo Damrosch)的《卢梭传》将讲述这个凡人如何蜕变为天才的精彩故事。故事的最后,我们将恍然大悟,卢梭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才般的伟大作家,恰恰是因为他感受着每一个平凡的现代人的感受,思考着每一个平凡的现代人的思想。
一、卢梭的原创性
我们如此之深地浸润在卢梭的遗产之中,以至于如果不具备历史学视野,就很难再体会到其著作是多么大胆和原创,多么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不仅构成了现代人类学的前奏,也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先声。通过将自然人类同于野兽,卢梭勇敢地挑战了《圣经》中按上帝面容所塑造的人的形象,从而挑战了教会的权威。通过对理性的贬低,卢梭向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发出了质疑,从而挑战了哲学家的权威。通过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描绘与判断,卢梭不仅向所有的富人、贵族、上流社会和统治阶级发起了攻击,更向文明社会的全部成员发出了挑衅。卢梭所描绘的人类逐渐疏离本真自我的堕落过程,后来被马克思凝结成“异化”概念。而当卢梭将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确立为文明社会应该复归的标准时,他已经预见到并参与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社会契约论》正是试图提供一套规范,让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之中也能享有类似于自然人的自由和平等。此后,合法的政治共同体不再是基于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自然法,而是基于每位共同体成员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自由被看作人之为人的美德,被视为人最根本的自然权利。卢梭重新定义了文明人的自由,即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由此,他开创了自由的哲学,影响到康德以降的整个德国唯心主义传统。
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仅仅被卢梭视为《爱弥儿》的附录。《爱弥儿》所阐述的自然教育主张影响深远。其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何种具体的教育措施和方法,而在于它要求发展一套培养自由个人的教育哲学,以便为合法的政治共同体的创立奠定基础。
《新爱洛伊丝》让同时代的人首次意识到生命中缺乏“爱情”,使得激情成为了美德,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在卢梭笔下,写作不再是揭示的工具,而变成了揭示本身;语言也不再是区别于自我的工具,而就是自我本身。这一全新的写作方式——语言即本真自我,已被现代文学所普遍接受。《新爱洛伊丝》对个人感情毫不掩饰的直率表达、自由奔放似乎只随着情绪起伏的笔法以及忧郁感伤略带夸张的情调,都预示着即将席卷文坛的浪漫主义潮流的来临。
正因为语言即本真自我,所以卢梭才能够承诺他将写出生命中的一切。关于过去的记忆可能会出错,但当下饱含感情的写作本身已经展现了自我。假如他用想象填补了记忆也无关紧要,因为一个人的梦的性质也反映了这个人的性质。这样,《忏悔录》发明了现代自传体裁,并确立了关于自我的新标准——真诚、想象力、情感和个性。当写作自传成为一种关于自我的探索时,卢梭所开启的方向最终通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在历史哲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或许还有心理学)领域全都写出了开创性伟大著作的人,居然是那个一直颠沛流离四处谋生、羞怯胆小却期望着在巴黎出人头地、满口奉承话的卢梭。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
二、卢梭的“哥白尼革命”
卢梭人生的扭转被称为万塞讷启悟。1749年,卢梭37岁,刚刚在巴黎稍稍安定下来。拙于社交的卢梭不太喜欢巴黎。他厌烦用严格校准的时间表规定日常工作日的每一个细节,厌烦无孔不入的社交礼节那虚以委蛇的虚情假意,厌烦只会逢迎社会思想与趣味的沙龙哲学。但他仍然努力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一切。毕竟,这就是文明的巴黎的生活。直到记忆中的那个夏日(实际是10月),他在去万塞讷监狱探望被囚禁的狄德罗的路上,偶然读到了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像被一道灵光的闪电击中,卢梭一直模模糊糊感受到的“不对劲儿”忽然清晰起来:科学与艺术把人的生活装饰得越来越文明,但这种文明已经变成了伪装,甚至奴役——“人们总是根据其他人的期望和意见来衡量一切,甚至对自己也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第216页)。蜂拥而至的可怕真理让卢梭眩晕不已,以至于他不得不在路旁的树下躺了一刻钟。据其自述,他此后的主要著作,不过是这一刻钟灵感的苍白无力的呈现。
从这一刻起,卢梭决心做一个不为“这里的人”所理解的“野蛮人”(《论科学与艺术》的题记是:“这里的人不了解我,所以把我看作野蛮人。”):不再从外部看待自己,而是诚实地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看待世界。冒着过分简化的风险,卢梭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追溯至某种最切身的真实感受。《论科学和艺术》源自他对于深受优雅精致又繁琐造作的法国宫廷礼仪文化影响的巴黎社交文化的不满。深思熟虑之后,《论不平等》致力于从更宏大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这种不满的正当性,勇敢地从“根部砍断”了文明之树(第218页)。卢梭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对于种种不平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一个例子最鲜明地表明了他曾多么根深蒂固地将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卢梭给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当秘书时,迷上了一个名叫祖莉埃塔的妓女。当他走进祖莉埃塔的闺房,沉迷于她的妩媚温柔,感叹她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之时,他下意识的反应是去探寻她身上隐藏的缺陷。因为他深信,如果不是存在着某种缺陷,这位天仙般美人怎么可能沦落到在社会底层做一名妓女呢? 于是,当他发现祖莉埃塔的一个乳头内陷时,秩序得到了恢复:这位美人原来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大自然的弃儿”!(《忏悔录》,第7卷)现在,通过《论不平等》,卢梭不再用现有社会秩序来解释生活中的不平等,而是反过来,用生活中的不平等来论证现有社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如果现有的文明令人背离了自身,那么,回到人的整全和统一就成为了此后所有著作的严肃主题。《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分别给出了政治的、教育的和爱情(或小团体)的解决方案。每一种解决方案都与卢梭的亲身经历之间存在着某种呼应。《社会契约论》中合法的政治共同体投射出卢梭对于祖国日内瓦的期望、对于想象中的斯巴达的倾慕。《爱弥儿》试图重整人的欲求的出现秩序,使人恢复自然的和谐,而这种秩序与卢梭自身成长过程中欲求的产生秩序正好相反。《新爱洛伊丝》中朱莉及其丈夫沃尔玛、从前的情人圣普乐之间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联系,就像华伦夫人及其情人阿内和卢梭、乌德托夫人及其情人圣朗贝尔和卢梭一样。(第319页)
《忏悔录》是一份流放中的自我辩护。在这个过程中,卢梭开始探索自我。确实,如果自我将成为观察和批判外部世界的基点,那么,自我本身理应得到严肃的认识和批判。写作《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时,自我分裂成了卢梭和让-雅克。这一分裂的至深意义仍未被充分揭示。在最后的著作《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写作变成了对分裂自我的疗愈。如同达姆罗施所言,“一个天才可以把不幸和神经官能症转化为优势”(第440页)。
终其一生,卢梭都在以非凡的勇气践履和揭示他从万塞讷启悟中获得的真理。在我看来,卢梭所做的事,与康德后来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类似。康德颠倒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指出不是客观对象决定了主体的思维,而恰恰相反,是主体的先天思维方式构建了客观对象。卢梭更早地感受到并用他自己的方式揭示了类似的洞见。
三、让-雅克塑造卢梭
卢梭总结万塞讷启悟说:“在看到这个题目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忏悔录》,第8卷)此后,卢梭便坚持从自我经验出发写作。这使得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变得异常艰辛,以至于他貌似夸张的自述很可能只是如实记录了其真实感受:“从那时那刻起,我就坠入了万丈深渊。”(《忏悔录》,第8卷)
首先,写作本身变得非常艰涩。由于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都需要经得起自身经验的检验,卢梭写得很慢,也很费劲。狄德罗具有倚马可待的才思,卢梭却总是在散步或长时间的失眠之后,才能费力地写出几个段落。(第215页)
其次,卢梭颠覆性的作品使得他晚年被迫流亡,更重要地是,令他在朋友中也很难得到认同,像是“被活埋在活人中间”(《对话录》,对话I)。从内部发起批判比做一个外部的批判者要承受更为沉重的压力,也要忍受更为可怕的孤独。在面对来自天主教和新教的攻击的同时,卢梭还必须承受朋友们的漠视和抛弃——反讽的是,为卢梭提供庇护和支持的恰是卢森堡公爵和孔蒂亲王这样的贵族。(第354-355页)其他启蒙哲学家共享着许多思想,就像“穿着一种团队制服,这让他们像自行车赛车手一样,可以从彼此的滑流中受益”(第219页)。但卢梭拒绝穿上这种制服,最终变成了伏尔泰眼中“启蒙运动的叛徒”。在根本上,多数启蒙哲学家们并不同情下层阶级。格里姆(Frederick Grimm)对卢梭政治著作的批评表达了一种典型的观点:“一般人并不是为自由而生,也不是为真理而生,尽管他们嘴里经常念叨这些话。这些无价的东西属于人类的精英,其明确条件是他们在享受这些东西时不要过分夸耀。其余的人生来就是为了奴役和错误。他们的天性置他们于那里,并使他们受到不可战胜的束缚。读读历史,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第348页)
最后,卢梭探究得越深,就越发现自我变得不可捉摸,这令他的精神处于永恒的不安之中。起初,卢梭发现,自我是由人生经验塑造出来的,童年经历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接着,他意识到,人生中那些任性、陶醉、狂乱甚至疯狂的时刻和事件可能表现了最真实的自己。他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我看起来与自己如此不一样,以至于有人会把我当成另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第437-438页)他甚至接近于发现了“无意识动机”。当卢梭意识到自己开始绕开某个街角以避开在那里要钱的一个小男孩时,他分析说:“这是我在反思时发现的,因为在此之前,这一情况从未在我的想法中清清楚楚地呈现过。这一观察使我想起了许多其他的观察,都使我确信,我的大多数行为的真正的第一动机并不像我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清晰。”(第482页)
然而,卢梭从未放弃过在所有的分裂和龃龉之下探索或塑造自我的基本核心。一位同时代人以非凡的洞察力凝练地说明了这一点:“卢梭有一个人造的性格,但不是一个虚假的性格。他并不完全是他看上去的那个样子,但他相信他是。”(第254页)
卢梭敏锐的感受几乎总是一针见血地预示了后人的真知灼见。当代认知神经科学通过对裂脑病人的实验,发现心智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认知系统,而是诸多认知系统的组合,而人之所以感觉自己只有一套心智,是因为左脑中存在一个能够为我们的行为进行统一叙述的特殊机制,即“解释器”(interpreter)(加扎尼加:《双脑记: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加扎尼加 自传》,罗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82、112页)。简单地说,卢梭对自我的探索完全符合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即,自我有很多个,但“解释器”会让人觉得只有一个自我。
在我看来,让-雅克塑造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卢梭。于是,那个羞怯胆小、满口阿谀之词以便在巴黎社交圈混下去的卢梭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勇敢大胆、雄辩滔滔、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卢梭。达朗贝尔评价说:“人们必须像我一样理解卢梭,才能看到这种藐视一切的勇气是如何使他的精神得到扩展的。十五年前我看到他时,他……几乎就是个阿谀奉承之辈,他写的东西也很平庸。”(第253页)而现在,通过承担起另外一个社会人格,让-雅克的天才得以发展并呈现。
四、现代自我的预言
自18世纪起,卢梭著作中的自相矛盾就一直饱受诟病,晚近以来的研究则试图解释这些矛盾。虽然学者们已发展出多种阐释模式寻求矛盾背后的统一,但对卢梭来说,诸多矛盾可能根本就是无法解开的。这是因为,自我之间的龃龉必将呈现为著作之中的矛盾。
卢梭发明了孤独的自然人,以此为标准批判文明社会。但他也宣称:“我知道绝对的孤独是一种阴郁的状态,与自然相反。关爱的感情滋养灵魂,思想的交流活跃心智。我们最甜蜜的存在是相关联的和集体的,我们真正的‘我’并不完全在我们自己之内。”(《对话录》,对话II)他甚至并不认为《论不平等》一定洞察了人类堕落的奥秘,《社会契约论》一开篇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 我不清楚。”(第一卷第一章)
卢梭渴求在文明社会中重获类似自然人的幸福,但他从不敢肯定他所设想的解决方案能够奏效。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他认为唯有神的子民才能建立起《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那种合法的政治体。
卢梭绝对而狂热的心理欲望、极端而疯狂的流放经历,泄露出其思想过于极端的病症。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全部著作仍不仅仅是基于一个矛盾的虚构自我的愤世嫉俗的批判,更是基于一个原初的现代自我的深思熟虑的预言。
卢梭的生活如此类似于现代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与其家庭、出身和母邦相隔绝,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职业换到另一种职业,从一套社会关系转到另一套社会关系。卢梭来到巴黎寻求出路时,就像今天那些到大城市谋生的打工人一样。巴黎的生活稍稍安定下来之后,卢梭与洗衣女工泰蕾兹结为了终身伴侣。虽然这与卢梭所建议的现代情感家庭——它基于情感关系,而不仅仅是等级权威——有区别,但在形式上,它仍然更接近现代家庭,而非传统家族。当文坛的名望令这个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有资格厕身于贵族名流之间时,他也从未忘记过自己是一个处于底层的“需要面包的人”,并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双手(而非国王的年金或赞助人的资助)谋生。(第435页)
这样,无论是在社会结构中,还是在心理结构中,卢梭都无比接近于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当他诚实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时,就拨动了与他类似的人的心弦。在卢梭成名的时代,现代公众正逐渐浮现。如同达姆罗斯观察到的,声望越来越取决于公众舆论,而不是专家的嘉许,才使得卢梭这个自学成才的外乡人在巴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哪怕早十年或是二十年,这种成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第162页)
卢梭预言并促成了现代个人的诞生。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卢梭的声音在公众心中激起过深远而巨大的回响。在很大程度上,他所承受的种种心灵的撕裂和身心的紧张,正是一个原初的现代个人在一个缺乏相应制度支撑的社会中所不可避免会遭遇的。
康德说,卢梭教会了他尊重人。在我看来,这本《卢梭传》则教人尊重自我:每一个“需要面包的人”的真实感受和观念都值得他(或她)自身最崇高的敬意和最严肃的探讨。
按:此文写至结尾,遽闻导师耿云志先生溘逝,悲痛不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先生始终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视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紧密相关的两个基本趋向。谨以小文献于先生灵前,作为一种纪念。
2024年8月4日夜于文津街甲9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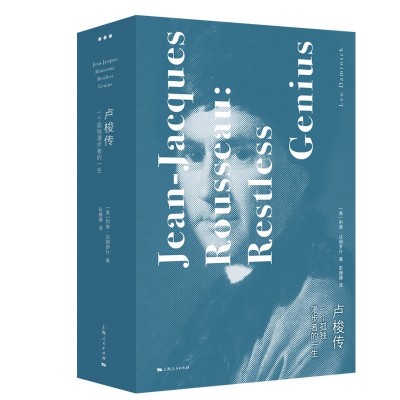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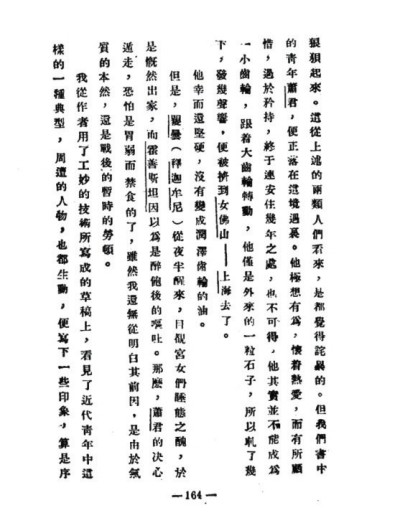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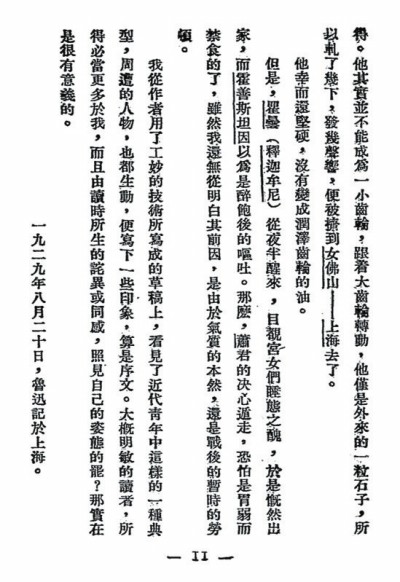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