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来北京,当时也就一岁,两岁开始有记忆,新中国的每一步,差不多都有印象。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
北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我曾熟视无睹,一切再熟悉不过,还有什么值得去看去想去说,甚至写本书?
飞快的城市建设,“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千变万化,面目全非,北京还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小时候,10岁前,我住城里,先农坛、海运仓、拈花寺、东四六条、铁一号,不断搬家,蓑衣胡同上保育院(当时不叫幼儿园),白米斜街上小学,跟老北京朝夕相处。10岁后搬西郊。当时,一出西直门,坐32路,去颐和园,去香山,这一路,我们叫西郊。我住海淀一带,一住几十年。我们说的“海淀”是海淀镇,不是海淀区。虽然海淀区政府就在海淀镇。我记得,小时候有个词叫“新北京”,似乎专指公主坟、五棵松一带,那是个军队大院扎堆的地方。我们这片不一样,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扎堆,是个“文化城”。
当年,毛主席“进京赶考”,他是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直奔香山。那个车站还在,离我现在住的地儿不远,也就一站。他老人家不想搬到皇帝老儿住的地方住,更爱香山。
现在,每年春天,花红柳绿,我会跟学生春游,顺便给父母、老师扫墓,去万安,去福田,去三山五园,我离我心中的老北京好像越来越远。
疫情期间,外地不便去,那我就在身边访古。只因城里城外,进进出出,到处寻找残破不全的历史遗迹,才使我儿时的记忆,连同它的古老背景,在我心中一步步清晰起来。这就是我要写的元大都。
元大都是明清北京城的基础。不了解元大都,就不懂北京城。我抓三个问题写。
一是中轴线:元大都的南北轴线(丽正门以南的明清轴线是其延长线)。重点讨论钟鼓楼与中心台、中心阁的关系,万宁桥与万宁宫、万宁寺的关系。
二是大都水系:高梁河、金水河、通惠河。重点讨论金水河从和义门南水门到元大内的水道流向,以及金水河与高梁河、通惠河的关系。
三是大都50坊:重点讨论元大都11门的配卦和命名之由,拿《元一统志》49坊与《析津志》的记载(提到40坊)和明初33坊做比较,辨析异同。
结论是什么? 这里总结一下,放在前面作预告。第一,我理解的中轴线是串联元大都主体建筑的一条南北轴线,而不是沿旧鼓楼大街(药王庙街)按几何划分画出的大城平分线。它是以万宁桥为基点,即沿海子(什刹海)东缘的切分点画一条线,把钟鼓楼、中心台和元大内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钟鼓楼、中心台不在旧鼓楼大街上,万宁寺中心阁也不在今钟鼓楼的位置。
第二,金水河是大内用水的专供线,它从玉泉山流出,一直傍长河(玉河)走,不是沿西岸走,就是沿南岸走。我理解,此水从和义门南水关进城后,一直奔东走,要经三座金水桥,先经万新(斯)仓金水桥,再经葡萄园金水桥,最后经海子西金水桥,沿柳荫街西岔和龙头井街,南下,进大内。我认为,金水河与西河无关,它与西河相遇,可以跨河跳槽,没必要沿西河南下再北上,兜一大圈,如徐苹芳推测。蔡蕃说是走捷径,从柳巷东口跨河跳槽后,干脆走斜线,往东南拐,先经葡萄园金水桥(他是把葡萄园金水桥放在护国寺南),再经厂桥,比徐说合理,但有点曲里拐弯。邓辉认为,金水河走弓背,沿蒋养房胡同、羊房胡同、李广桥走,只是到了柳荫街,分东西两岔,从柳荫街西岔、龙头井街进大内。分岔后的一段有道理,但前面一大段是玉河出入海子的河道。它从西海子出,过李广桥,沿柳荫街东岔往东拐,先进海子,再出海子。万宁桥下和东步粮桥下出是东玉河,西步粮桥下出是西玉河。这是玉河,不是金水河。金水河不同,它与玉河是平行关系,并不相交,其实,即使最后一段,金水河也在玉河内侧。我们从明真武庙的位置和《真武庙重修碑记》提到的金水河看,金水河恐怕是走直线,最后经海子西金水桥,然后才是沿柳荫街西岔走。
第三,元大都的坊巷应以《元一统志》的记载年代最早、最有系统,《析津志》的记载偏晚、残缺不全,但后者与明初坊名容易对号入座,故学者所绘元大都坊巷图,多半是把《元一统志》与《析津志》拼凑在一起,参考明代坊名来复原。本书是以大都11门的方位、卦位入手,先定城门干道和区块划分,次考《元一统志》的坊名和取名之由,以此作“底本”,最后与《析津志》40坊和明初33坊对勘,类似文本研究。这是已知加未知,虚实结合,整体卡位,既用串并法,也用排除法,跟刑侦方法类似,虽云不中,亦不远矣。
张南金是我最后的研究生。他有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和古文献基础,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孩”,一直住城里,比我更熟悉北京。我们一起考察,一起讨论,一起写这本书。我们的合作很愉快。
当年,孔子带学生春游,“风乎舞雩”,那是个梦。我经常梦见这个遍植绿树的土台。你能想象吗? 它真的就是孔子当年的舞雩台,西周就有的古迹。
每年春天陪我春游的学生和朋友,对我帮助很大。我把他们的行踪记录在案。我们一起行走北京,阅读北京,玩得不亦乐乎。
玩也是学问,玩就是学问。北京太好玩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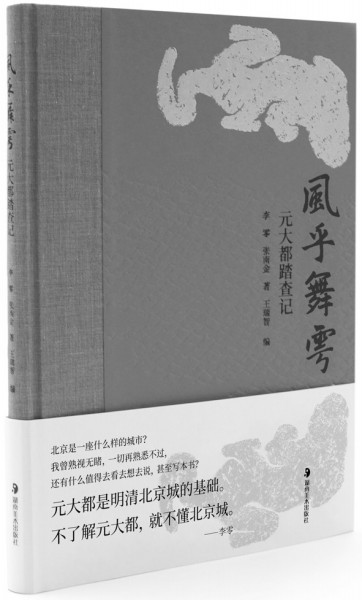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