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将近四十年前整理《宋宰辅编年录》(《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并主要从中挖掘史料写下《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分别刊《历史研究》1985年2月、1989年1月)起,我就较为留意中央政治中的君臣关系问题。后来游学东瀛,接受日本学者的认识,将宋代政治的主要形态归纳为士大夫政治。在本世纪初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就直接以“士大夫政治”入题。士大夫政治可以说是贯穿我研究生涯的一条研究主线。
何以会长期专注于士大夫政治研究? 与我对历史关注的方向有关。近二十年来,我着力于开辟第二条研究主线,就是宋元变革论。这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何从近世走向近代的研究,是向下看的研究。其实,我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向下看的研究。向下看,就是面向未来回顾历史。多数历史学者无论明确认识与否,或者是否愿意承认,内心中其实都潜藏着现实的情怀。历史长河从远古奔腾到今天,又呼啸着涌向未来。我们处于长河中流,观察上流的经历,思索下流的走向。传统社会的思想家往往有着为救世开处方的意识,尽管这并不是今天历史学者的主要任务,但审视思考前人走过的步履,汲取前人的思想精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人类更好地走向未来,无疑是历史学者的重要使命。
士大夫古已有之。古老的《周礼》中便有这样的表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说到士大夫政治,有的学者也会将目光投向东汉的清议、党锢以及太学生运动。不过,我立足于宋代的研究,将士大夫政治赋予了新的内涵。那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以往又有何不同呢? 宋朝开国,五代以来重文的社会潜流,朝廷重文抑武战略转向,行政管理人员的大量需求,诸多方面的历史合力,让隋唐以来涓涓细流的科举规模,犹如开闸泄洪般骤然扩大,一次科举登第人数由几十人增至几百人、上千人。这一在太宗朝肇始的祖宗法,一直贯穿了两宋三百年。龚延明、祖慧先生主编的皇皇14巨册《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就是那个时代辉煌的历史记录。一个技术性的操作,可以说改变和规定了历史走向。
文彦博跟宋神宗讲的那句有名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就清晰地表述了士大夫政治的特征,即君臣共治。不过,宋代的君臣共治并不是像东晋“王与马共天下”那样的权力共享,而是士大夫主导下的君臣共治。实现这样的共治,也并不是由于宋代士大夫拥有东晋世家大族那样的军政大权,而是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全掌控,这种实力绝非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能企及的。在历代相承并不断完善行政制度的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从上到下有序操控,也挤压了君主的行政空间,让皇权进一步走向象征化,更多地以巨大的权威性来为士大夫政治增加分量。这种形式的共治摆脱了特定个人或集团的权力独运,是皇帝的象征力与士大夫的政治力的充分结合。
科举规模扩大的太宗朝后期,士大夫政治初成气候,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李沆、寇准已进入执政中枢,登上政界的制高点。进入真宗朝,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就实现了全面主宰。如本书所述的五个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所谓的“真宗五友”,在这一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为善为恶,姑不具论,在中央政治层面,把士大夫政治在此后三百年的各种作为几乎都预演了一遍。这是我之所以把宋真宗朝作为论述重点的主要考量。除了澶渊之盟,真宗朝戏剧性的事件实在很少,所以历来也不大为研究者所过多关注。其实,继太祖、太宗统一全域的建国期之后,真宗朝对宋朝制度建设的完善,宋辽百年和平期的开启,士大夫对宋朝第一位正常继统皇帝的皇权形塑,都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宋代历史乃至后世。
士大夫政治并不仅仅止于行政施策,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科举规模扩大的直接产物是士大夫政治。同时,金榜题名的荣耀,光宗耀祖的愿望,改变命运的企求,还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之风。除了“学而优则仕”,在唐宋变革的平民化趋势之下,全社会的向学,也带来了教育的普及,提升了全民的文化水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从《论语·季氏》记载的孔子所言看,隐逸也从来不是道家的专有。在乱世,读书人“卷而怀之”,只能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夫。到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宰的氛围,让士人、士大夫极大地激发出入世的“治国、平天下”之志。一直沉睡在《礼记·大学》之中的儒学“八条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宋代士大夫重新挖掘出来,成为涵盖个人、家庭、国家以及世界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赋予了宋代一批士大夫高度的责任感与强烈的事业心。
科举并不仅仅是“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的跳台,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也让应试的士人在习举业的过程中接受了有形无形的熏陶,让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拥有一定的道德意识。关于这一点,甚至充分走向汉化的女真人金朝皇帝都有明确认识。金世宗就曾这样讲过:“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当然,必须承认,士大夫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具有高度责任感与强烈事业心的士大夫精英与无耻的败类都是少数的存在,多数是顺应潮流的籍籍无名的“循吏”。毫无疑问,士大夫精英是潮流的引导者。
制度建设基本底定的真宗朝过后,在士大夫政治大盛时期的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士大夫精英发起了道德清理的精神建设。不仅逆转评价冯道等五代贰臣,还从先秦思想资源中汲取限制诸侯国国君言论,将错就错,挪移用来限制皇权,从而奠定了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儒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后,特别是在理学支撑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氛围之下,士大夫是经典诠释者,君主也要服从他们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大夫占据了一个君主无法比肩的道德与学问的制高点。碾压皇权,道统高于政统。
其实,士大夫精英的一个理想目标,是将君主塑造成自己可以进行精神沟通的同类。《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记载了范祖禹的一段话,这是对因夏天炎热不愿意听经筵讲课的年轻宋哲宗讲的:“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勤其心,务为邪謟,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君主好学,与士大夫好尚接近,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士大夫就会对君主有好感,愿意同在朝廷,一起干一番事业。士大夫对君主劝学的一种企望,就是把君主也变成士大夫中的一员。之所以宋代能够形成士大夫政治主宰的君臣共治,这表明士大夫精英改造君主的努力是比较成功的,宋代皇帝的确基本上是朝着士大夫精英引导的方向走的。我们进一步审视,士大夫政治激发出的宋代士大夫的理想还从政治层面有了更高的提升。正是在宋仁宗朝,相传受教于范仲淹的理学大家张载,就发出了高亢的宣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这一切是为天地,为生民,为往圣,为万世。纵横时空,继往开来,这是何等的气魄! 已经完全超越了政治层面的君臣共治,笑傲江湖,我主沉浮。这种自信,这种自豪,这种苏世独立的觉醒,只有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才会激发出来。
以上讲述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以往历代的不同。关于我之所以会长期专注于士大夫政治研究,前面讲了一句,是“向下看的研究”。宋代以后的元代、明代、清代,政治生态都与宋代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是宋代那个时代涵养的士大夫精神。不论如何时移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为不少读书人所秉持,在政治、社会、学术等不同领域践行,成为各个时代“中国的脊梁”。这种来自宋代的士大夫精神,到了近代,便成为传统知识人与世界接轨转型的内在促因。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很值得我们立足于宋代,并超越宋代,俯瞰近代,进行深入研究,思索中国知识人精神结构的来路。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向下看”,此之谓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入20世纪,传统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帝政走向了共和,王臣变成为国民。不过,思想的遗传,传统的惯力,不仅让士大夫风骨得到传承,也让皇权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顽固地遗存下来。消除皇权意识,人们才能完全从精神上站立起来,但这还需要长久地努力。因此说,研究皇权,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书并非完全是日文版的翻译,在内容上有不少增删调整,主题内容集中在宋真宗一朝。此书在2010年由中华书局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为题初版,后来又易名为《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先后于2015年、2019年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又承罗振宇先生的“罗辑思维”推介,也赢得了学术圈外众多读者的喜爱。此次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厚意,再度推出,我期待更多的读者通过此书来了解一个时代,一个让华夏文化造极的时代,由此理解中国传统知识人的精神特质,并思索在今天的继承。
此次推出,从总编到责编,十分用心,重新做了精致的优化设计,并增插有多幅彩页,强化了本书视觉印象。其中对于每章前的辑封页的设计巧思,责编舒鹏曾这样跟我解释过:“左侧图片为宋陈容《五龙图卷》截图,因话题颇为有趣,暗合五位宰臣宦海浮沉,各具性格。书中五相,虽忠奸有别,但各擅胜场,又时代相近,各有牵扯,与群龙盘缠一起,有许多可供联想之处。故目前依照章节、任相时间前后,与画卷右左顺次,一一对应。”
此外,尽管“士大夫政治”已逐渐特指宋代的政治特征,还是接受总编赵波先生的建议,在书名中明确点明时代,加入“宋代”二字。曾打算将书名中的“权力场”改为意思显豁的“权力纠缠”。在量子力学里,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便把这种现象称为“量子纠缠”。不过后来想想,“权力纠缠”尽管表述具体,但不如“权力场”拥有想象张力。最后,还是用了既无形又可感知的物理学“场”的概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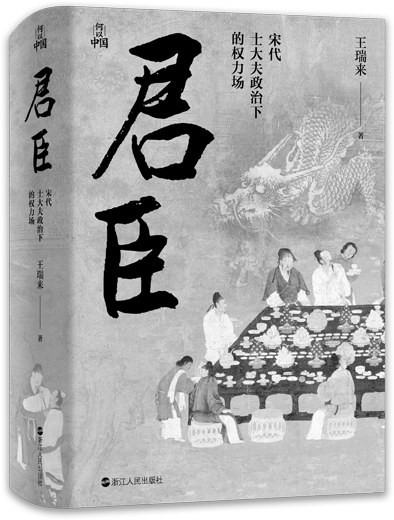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