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釭
梁遇春在这个世界上只匆匆生活了二十六个春秋就被猩红热夺走生命,留下散文三十余篇,此外尚有一批译作,因甚耐品读而蜚声文坛。他师从叶公超,深得英国随笔精髓,散文不乏哲思妙篇,分别见诸于生前出版之《春醪集》和殁后友人整理出版之《泪与笑》。梁氏笔名“秋心”,秋心寂寥,可见其生性多愁善感,另一笔名驭聪,则又表明他对把控文思充满自信。
独抚春醪醒犹梦
《春醪集》,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初版,1月付梓,3月面世,竖排疏行版面清朗,天广地阔留足宽边,每页仅约二百字。书名“春醪”系著者采自1926年在北大一院图书馆翻阅《洛阳伽蓝记》时偶见“不畏张弓拔刀,但畏白堕春醪”句。梁遇春在《序》中感慨道:“我们年轻人都是偷饮了春醪,所以醉中做出许多好梦,但是正当我们梦得有趣的时候,命运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样匆匆地把我们带上衰老同坟墓之途”,这虽未免让人惋惜,“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此安排好了,我们还是陶醉在人生里,幻出些红霞般的好梦吧,何苦睁着眼睛,垂头叹气地过日子呢? 所以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此刻的作者未预料自己的生命如此短促,尚遐思“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
梁遇春对彼时流行的讲演素无热情,甚或在《讲演》一文中暗含揶揄,然而藉《醉中梦话(一)》坦陈:“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梦里未必说话,醉中梦话云者,装糊涂,假痴聋,免得‘文责自负’云尔。”后又撰《醉中梦话(二)》言:“‘梦中醉话’是我两年前在《语丝》上几篇杂感的总题目。匆匆过了两年,我喝酒依旧,做梦依旧,这仿佛应当有些感慨才是。然而我的心境却枯燥得连微喟一声都找不出。”何语出矛盾? 睿智诙谐也,“因为诙谐是从对于事情取种怀疑态度,然后看出矛盾来,所以怀疑主义者多半是用诙谐的风格来行文,因为他承认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亦作(一)、(二)两篇,乃梁遇春写给自己的“信”,启信人“秋心”,署名者“驭聪”,分别作于1927年元宵和1928年3月。其(一)详述失恋烦恼,且袒露“我也是个失恋的人,不过我是对我自己的失恋,不是对于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恋。我这失恋既然是对于自己,所以不显明,旁人也不知道,因此也是更难过的苦痛。无声的呜咽比号啕总是更悲哀得多了。”其(二)情绪有所平复,逐渐从彷徨怅惘转而打起精神,憧憬未来趋向积极,认为“青春之所以可爱也就在它给少年易希望”,“若是青春的丢失,真是件惨事,倚着拐杖的老头也不会那么笑嘻嘻地说他们的往事了。”
《查理斯·兰姆评传》是《春醪集》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梁遇春视兰姆为良师,“人生路上到处都长着荆棘,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常常被刺,就是万不得已皮肤给那坚硬的木针抓破了,我们要去哪里找止血的灵药呢?一切恋着人生的人,对这问题都觉得有细想的必要,查理斯·兰姆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导师。”
梁遇春年纪虽轻但极富定见,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借三国时关云长被斩首英灵不散仍大喊“还我头来”传说,宣称“‘还我头来’是我的口号,我以后也只愿说几句自己确实明白了解的话,不去高攀,谈什么问题主义,以免跌重。”他在《文艺杂话》中申明文艺观,“我对于古往今来那班带有使命感的文学,常抱些无谓的杞忧。”
梁遇春的可爱处在于不掩饰,自曝习惯“迟起”,尝借《“春潮”一刻值千金》振振有词趣谈其迟起之“艺术”享受:“现在春天到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五六点钟醒来,就可以看见太阳,我们可以醉似的躺着,一直到躺了好几个钟头,静听流茑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这真是迟起的绝好时光。”而“回味前夜的痴梦——那是比做梦还有意思的事”无疑是该文的“哏”。春日赖床固然惬意,但作者亦首肯“我们青年时期若使是欢欣的结晶,我们的余生一定不会是凄凉的,青春的快乐是有影子留下的,那影子好似带了魔力,惨澹的老年给他一照,也呈出和蔼慈祥的光辉”。
阅尽悲欢泪与笑
《泪与笑》,梁遇春殁后由废名汇编,发行者章锡琛,书名撷取首篇文章篇目,开明书店1934年6月初版,著者已逝故无自序,遂由废名、刘国平、石民分别作序,封面和内芯版式极为素简。
《泪与笑》以笑为楔子,笑的形式莫测,甚至有传递悲剧情调之“笑”,泪乃内核,“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为生活是可留恋的,过去是春天的日子,所以才有伤逝的清泪。若使生活本身就不值得我们的一顾,我们哪里会有惋惜的情怀呢?”“泪尽了,个个人心里都像苏东坡所说的’存亡惯见浑无泪’那样的冷淡了,坟墓的影已染着我们的残年。”这番话仿佛耆老箴言,但本意未必颓唐,诚如其在《天真与经验》中所言天真和经验并非不共戴天,关键是“经验陶冶后的天真是见花不采,看到美丽的女人,不动枕席之念的天真。”
梁遇春洞察世态目光犀利,《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将“伙计”分三种:著书立说欲显身手的大学教授、安分守己随缘度日的中学教师、整天辛苦还被上司克扣工钱的小学教员,嘲讽“伙计是这么死沉沉的,他们以贩卖知识这招牌到处招摇,却先将知识的源泉——怀疑的精神——一笔勾销”,语虽讥诮,鞭辟入里。《一个“心力克”的微笑》嗟叹:“人生的意义若在人生之中,那么这是人生,不足以解释人生;人生的意义若在人生之外,那么又何必走此一程呢? 当此无可如何之时我们只好当“心力克”,借微笑以自遣也。”
参悟人生、探讨哲理让梁遇春耽于沉思,他在《破晓》中写道:“世界里怎么回事一达到圆满的地位就是死刑的宣告,人们一切的痴望也是如此,心愿当真实现时一定不如蕴在心头时那么可喜。一件美的东西的告成就是一个幻觉的破灭,一场好梦的勾销。”《她走了》中之“她”,抑或是“你”,连作者自己都恍惚得难以分辨,“但是我凄惨地相信西来的弱水绝不是东去的逝波。否则,我愿意立刻化作牛矢满面的石板在溪旁等候那万年后的某一天。”
偶尔,某些动物会成为梁遇春借用的意象。譬如,《猫狗》文中比喻“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个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北平却是一只猫。它代表灵魂的堕落。”“若使我们睁大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世界是给猫狗平分了。现实的黑暗和灵魂的堕落霸占了一切。”
梁遇春的散文饱含情愫和愁楚,《无情的多情和无情的无情》谓专注精神、忽略行迹、看似无情实有情的“这类恋爱叫做多情的无情”,但“多情的无情有时逐渐化做无情的无情”。《毋忘草》叹息:“当一个人悲哀变成灰色时,他整个人溶在悲哀里面去,惘怅的情绪既为他日常心境,他当然不会再有什么悲从中来了。”《第二度的青春》里缠绵着春愁、乡愁、父愁。更甚者,《又是一年春草绿》把春愁演绎成惧春,“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我都能够忍受,有时还感到片刻的欣欢”,“世界里年年偏有这么一个春天;在这个满天澄蓝,泼地草绿的季节,毒蛇却也换了一套春装睡眼朦胧地来跟人们作伴了,禁闭于层冰底下的秽气也随着春水的绿波传到情侣的身旁了。”
梁遇春臧否人物与众不同,数落刘备是“千古权奸”,调侃雪莱、济慈、拜伦、屠格涅夫矫饰,揭短形形色色“行家里手”们迂腐。不过,最具争议大概非《春雨》中的戏谑莫属:“在所谓的大好春光之下,人们都到公园大街或者名胜地方去招摇过市,像猩猩那样嘻嘻笑着,真是得意忘形,弄到变为四不像了。”
《CILES LYTTON STRACHEY,8801932》系梁遇春绝笔,纪念病逝于1932年1月21日的英国近代传记学大师奇尔兹·栗董·斯特剌奇,惜甫撰毕梁氏亦撒手人寰。
薪尽火传存微光
梁遇春弱冠未几便遽然早逝,生命短促固然不幸,然诚如其悼徐志摩文中所景仰的那位吻火者,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率性的蹈火者形象,永远“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故尔,与梁遇春同时代的文学家对其不乏中肯评价。
乃师叶公超认为,梁遇春“是个生气蓬勃的青年,他所要求于自己的只是一个有理解的生存,所以他处处才感觉矛盾,这感觉似乎就是他的生力所在。无论写的是什么,他的理智总是清醒沉着的,尤其在他那想象汹涌流传的时候。”换言之,把他看作是一个悲观者或相信命运说者是不恰当的。
梁遇春去世前曾致胡适一封信,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梁去世后,胡适与周作人、叶公超、俞平伯、废名等发起追悼会,着手编辑梁遇春遗译《吉姆爷》,并在《编者附记》中痛惜梁的早逝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
废名同梁遇春熟稔,“常常见面,差不多总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冲天,处处闪眼”,“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
刘国平眼中的梁遇春“耽于书卷比谁都厉害,他不受任何前辈先生的意见支配,他苦讨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这确是最能得古人精髓的人应有的本色,可惜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这本色。我们随便拿他一篇文章来看,立刻就能知道学究的话没有进过他的门限,他口上没有提过学问这两个字,这样他得了正法眼藏”。
北大同窗石民回忆:“厥后来沪,他在真茹(那时有人嘲笑地称他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其实他只是一个助教而已)而我则住在租界的中心,他乡遇故知,自然格外觉得亲热……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每次见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谈的‘口谈手谈’。有时读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或写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总是很高兴地翻出来给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满了他所翻开的书本”。
冯至比梁遇春早一年考入北大预科,半个多世纪后谈及:“那时北大预科在东华门内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上课。我常常看到他。由于他显得年轻聪颖,走路时头部略微向前探,有特殊的风姿,而且往往是独来独往,这都引起我的注意……直到1927年后,才先后在《语丝》、《奔流》等刊物上读到他的散文,并且在1930年知道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春醪集》。”“梁遇春没有创作过诗,但他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
梁遇春是个文学奇才,郁达夫称他为“中国的爱利亚(英国散文家兰姆笔名)”;唐弢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
从出版史角度而言,梁遇春生前、逝后两本散文集均初版于上海绝非偶然,既是彼时沪地出版业繁盛高效的例证,也可见梁氏气质甚契合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泪与笑》系梁遇春辞世不久便由其挚友废名筹划编辑,他携文稿到上海,托石民等联系出版社,原本交新月书店出版,因“新月派”顶梁柱徐志摩意外遭空难,新月书店随之停办,1933年12月正式倒闭,遂将《泪与笑》书稿转至开明书店,1934年6月出版。梁遇春两度与上海结缘,首次是1922年7月,自家乡福建赴上海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报考北大英文系预科,初、复试均成绩优异,录取榜发布于北京《北京大学日刊》,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民国日报》;第二次为1920年代末,1928年北大毕业留英文系任助教,后遇政局动荡,随温源宁教授到上海暨南大学执教,居真如一年余,1930年与温源宁同返北大。
尚需补充的是,梁遇春的散文除入编《春醪集》《泪与笑》外,诸如《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茄力克的日记》《新传记文学谈》等十七篇频密刊载于《新月》月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宣称以“郑重矜持”为出版宗旨,印行文学艺术单行本,力图在左右翼文化纷争之外另辟蹊径,历任编辑、主编先后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罗隆基等,主要撰稿人有沈从文、胡适、余上沅、梁遇春、叔华、英士、胡不归、陈梦家、赵景深、郁达夫等,1928年3月创刊文艺性月刊《新月》,1933年6月终刊,共发行4卷43期。此外,梁遇春还有一些专论翻译文学的篇章散见于北新书局出版的《红花》《厄斯忒哀史》《诗人的手提包》《最后的一本日记》《我们的乡村》《草原上》《青春》《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及开明书店出版的《英国小品文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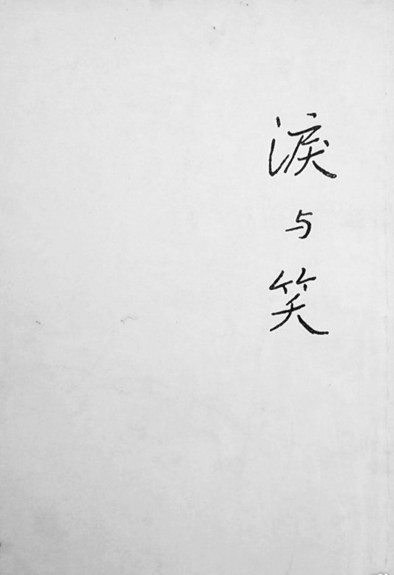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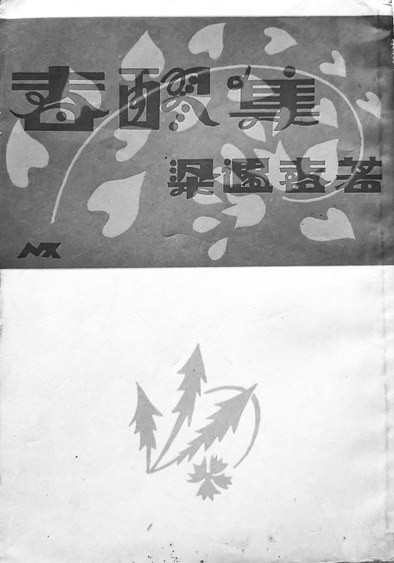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