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华
小斯当东的“东方未远”
面朝东方、思念父母双亲的留守儿童小斯当东肯定不会知道,他多年以后在英国议会上的一番讲话可能影响很大。他与科尔布鲁克等从东方退休回英的学者们创办的皇家亚洲学会,在两百年后仍旧坐落于伦敦市中心,成为东方研究热爱者相聚、交流学术的重要场所。他竭力促进的英国汉学,已成为英国大学中极为重要的学院派、世界化的国际性研究。时至今日,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学者仍旧在书写着英国汉学史。他们在伦敦相聚、在牛津相聚、在剑桥相聚,在距离皇家亚洲学会不远的欧洲东方学研究中心、皇家亚洲学会之“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相聚。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学生,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亚洲、非洲等更为广阔的世界。
皇家亚洲学会活跃在东方的11个分会延续着英国东方学两百年前的基因特质,连点、成线、成面、再成体地建构着英国的东方知识体系。它们与英国本土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一起,再次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英国汉学在创始之初就与东方学根脉相连。那些长期在英属殖民地从事殖民、研究工作的学者,早已在自己的故乡和工作的他乡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们企图从东方古老历史文化的母体中汲取养料、吮吸乳汁,去滋养、哺育英国乃至欧洲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这在客观上使东西方通过学术的方式联系起来。
事实上,对于小斯当东来说,东西方从他思念父母的那一刻就已经联系在了一起。他日后与东方、中国、中文、汉学的关联早在那时就已经注定。他长期投身于中国、东方,似乎是在弥补幼年时父母缺失的遗憾,又仿佛在和身处东方的父亲同舟共济,努力完成着父亲交给他的任务,实现着父亲对他的期许。在小斯当东的眼里,东方不远。他具有东方视野的眼光,使他较早认识到印度、中国与英国之间深刻的联系,认识到东方与西方之间对话、交往的重要价值。他将汉学融进东方学之中,在东方学术史发展背景下规划自己的汉学研究。他的研究、实践因视野的广阔性、前沿性而具有难以抹去的时代价值。
奔向喜马拉雅山之巅
我们既可以说小斯当东和科尔布鲁克是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相识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平原相识的。他们彼此都曾努力攀登着喜马拉雅山,一个从印度出发,一个从中国出发,经过努力,在高峰相遇,共同开启了英国本土的东方学研究、汉学研究。在印度工作了30年的科尔布鲁克,早已从殖民主义扩张的信奉者变为拥有国际精神和学术热情的东方学者。他的野心在于将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众多东方研究成果传输到英国本土,使英国东方学在英国本土扎根,继续威廉·琼斯在印度未尽的东方学使命。同时,将东方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英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使东方学拥有与社会劳动相媲美的价值力量。那些从印度、中国退休回到英国的学者、“中国通”们支持科尔布鲁克的学术理想。作为威廉·琼斯在印度学研究的继承者,科尔布鲁克在梵文、印度学研究上的成果,使他名副其实地被称为西方“印度学之父”;他积极推动英国东方学事业的发展,也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英国东方学第一人。正如他在自传中展露的那样,他的学术道路仿佛是艰难穿越着布满荆棘、充满迷雾的梵文森林,然后不断接近那座他梦寐以求的喜马拉雅山。
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即使科尔布鲁克登上山顶,他也必然会深情地望着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大地。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精力去探索喜马拉雅山另一侧那个伟大的东方国家——中国。在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办计划书中,这样描述英国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情况:中国文学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感受到,这是带着何等的遗憾和期待啊! 科尔布鲁克唯有联通更多的东方学研究专家,不断促进英国的东方学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才能弥补这一遗憾。因此,科尔布鲁克呼吁到:“英国需要创建一个和它的父辈学会(威廉·琼斯创建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一样的学会。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使英国和亚洲一起走向繁荣。”小斯当东作为支持科尔布鲁克创建皇家亚洲学会的重要学者,他在皇家亚洲学会创建的过程中极为主动热情。小型的筹办执行委员会会议,往往相聚于小斯当东的家中。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小斯当东推动了皇家亚洲学会的汉学研究,他是从中国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人,与科尔布鲁克在高山之巅相遇,共同怀揣着东方学研究的梦想。两百年来,他们携手创建的皇家亚洲学会已经成为英国东方学的一个标志。
递给小斯当东的接力棒
但是,在科尔布鲁克和小斯当东所处的时代,“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使英国和亚洲一起走向繁荣”这样的目标何其渺茫。英国走向繁荣是真,亚洲的繁荣又是谁能够给予的呢? 对于东方而言,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英国的殖民主义力量早就下着一盘大棋。在这盘大棋中,老斯当东、小斯当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之间传递接力棒的历史映射出中英关系的变迁。1781年5月26日,小斯当东出生在身为银行家的外祖父家中。在他出生前,他的父亲已经于1781年1月随马戛尔尼勋爵起航去了印度,他的母亲也准备随老斯当东前往东方。作为留守儿童的小斯当东被养在祖母家,直至四岁多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老斯当东抛家弃子、去国万里、远赴东洋开创他的东方事业,对于小斯当东而言,这样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分离并没有消极地影响到小斯当东与父亲的关系。由于小斯当东从小缺少双亲的陪伴,身体较为孱弱。他的父母更觉内心亏欠,愈加重视他的健康和教育问题。小斯当东也倍加思念身在东方的父母。正是因为小斯当东的这份思念,以及老斯当东的这份亏欠,使得小斯当东对父亲的敬重和崇拜贯穿了他的一生。老斯当东将小斯当东引向东方、引入中国,成为小斯当东命运发展的必然。小斯当东自然而然地与中文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贯穿他的一生。他一生的荣誉都与中国、中文、汉学相关。他幼年时期思念着在东方的父母,少年时期与中文、中国结缘。他在中文上的突出表现以及被不断培养出来的散文气质、舒缓状态、包容精神、现实情怀等特质,都为他与中国审美文化的共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老斯当东的育儿观念深受东方影响,他认为:儿童天生的好奇心应该被引导到对大自然奇妙现实的关注上,而不是在童话故事的过度想象中浪费或玷污。小斯当东通过学习实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滋养,使得他对世间万物的领悟和感受是舒缓的、开阔的、长久的、真切的,进而能够保持精神上的年轻和心境上的放松。这为他在面对乾隆皇帝时恰到好处的言谈举止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包容、舒缓、开阔、真诚以及中国审美的散文气质,与小斯当东所具有的审美状态是相契合的。小斯当东的脱颖而出既是父亲精心培育的结果,也是东西方审美文化共同熏陶下成就的外交佳话。
1792年,马戛尔尼使华是小斯当东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小斯当东随使团访华,他在一年的航程中苦学中文,掌握了中文的日常表达,且能够誊写中文,以至于后来使团每份要用中文呈递的文件都要经过小斯当东的手抄一遍。使团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小斯当东的故事得到了中外的关注目光。他的天赋不仅赢得了皇帝的赏识,更赢得了随团人的赞许。然而,作为使节团副使的老斯当东却因这次访华失败而未被正式任命为驻京大使。小斯当东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影响了我日后全部重要事件,而且成为我在世界取得各种声誉(不管是在文化界还是在政界)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我日后一直要实现的目标。”那时的小斯当东早已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相连,他在事实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东方事业的接力棒。
“中国通”小斯当东的快车道
1798年,小斯当东在父亲的帮助下获得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广州文书一职,逐渐地收获了友谊和褒奖。他一方面从事英译汉、汉译英的工作,另一方面处理中英之间的突发问题。他翻译的书籍往往不是纯文学的作品,在内容上也不仅仅局限在一国的范围内,而是包含到更为宽广的国际交流范围,是对现实有所帮助的书籍,极具时代交流价值。1805年,他在一位中国人的协助下,将商馆外科医生皮尔逊先生有关牛痘接种的小册子引入中国,中文译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该书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牛痘接种技术的相关知识,是中英交流的重要媒介。此书在当时对于天花的免疫和预防具有现实意义,其影响力也不仅仅在中国,更是蔓延到了东亚汉文化圈内。对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翻译,既体现了小斯当东对医学、现实、时代问题极为敏感,也显示了他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
小斯当东的语言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突出,被任命为商馆的翻译。在学术层面,他越是深入地研究中国,就越能够把握中国,深入到中华文化内部;1808年6月,他放弃了在广州的工作,返回英国。1816年,他在阿美士德勋爵使华团中获得任命,但是这次出使因“礼仪之争”无功而返。
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赋予他的声誉,比他一生中经历的其他任何事件都要大。他曾这样评价他翻译的《大清律例》:“如今,它在英国东方学文献中占据了一种非常牢靠且受人尊敬的位置。”译本在1810年3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小斯当东对《大清律例》的翻译紧跟着英国东方学发展的历史潮流,与威廉·琼斯、科尔布鲁克对印度法律经典的翻译相呼应。首先,东方国家的法律是殖民外交官、贸易者关注的现实问题,可以帮助殖民者深入认识东方社会、文化等。其次,翻译是早期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形式,目的在于寻求介入东方法律、社会的路径。再次,翻译中国法典可以补充英国在中国法律研究上的缺失,提升小斯当东所从事汉学研究的影响力。
1818年,小斯当东进入英国议会,长期担任下院议员。这是他用知识与经验服务政府的最佳时期。这一位置与他的能力、志向相符,旨在更好地完成他父亲未尽的东方事业。小斯当东在是否向中国开战的辩论中说道:“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由此可知,他的做事逻辑深受父亲影响,同时他的主张也印证了他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立场。
小斯当东的汉学追求
小斯当东的复杂性也在于,他的确推动了英国汉学的进步。他不仅资助了许多汉学家,更促进了英国汉学走进大学,助力了汉学的学科化。如果说马礼逊是典型的传教士,德庇时是汉学家,那么小斯当东更像是一个政客,一位支持汉学、推进汉学发展的政客。小斯当东认为,与自己出于现实需要学习中文不同,马礼逊对中文的专一和坚持不懈使其最终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他将自己做翻译的酬金赞助给马礼逊。此外,德庇时在当时是著名的汉学家,且更偏向学者的一面,他曾被小斯当东推荐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
然而,在英国汉学努力走进大学的时代,需要小斯当东这样的政客。汉学家可以推动汉学研究的进步,政客则能够更好地促进汉学学科的发展。小斯当东对汉学、东方学发展的推动,是他返回英国后最为主要的学术贡献。1823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小斯当东和科尔布鲁克一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小斯当东担任皇家亚洲学会的副会长,他向学会捐赠了自己珍藏的约3000小卷全部中文书籍,以及200部欧洲人论中国的著作,还为学会博物馆捐赠了几件珍品。他捐赠给学会的图书文献目前大部分保存在利兹大学布罗泽顿图书馆,留存在皇家亚洲学会的中文手稿基本上是他的手写稿。这些手稿文献字迹工整,如同中国文人的优美笔迹,体现了小斯当东的天赋以及他将中文介绍给西方的决心与努力。
皇家亚洲学会凝聚起了英国早期的汉学研究者,开始开垦这块“中国文学的处女地”。英国汉学研究的区域视野、东方学视野是隐含在其基因里的特质。1846年6月12日,小斯当东在伦敦国王学院提交了“关于在伦敦国王学院设立中文教授职位的捐资提议”,并获得一致通过。国王学院成为当时英国唯一教授汉语的学院。
小斯当东的“双刃剑”
鸦片战争后,汉学能够使英国更加有效地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和平相处之道。鸦片为中国带来的苦难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文明、科技、启蒙为名,行侵略之实的大英帝国难以阻挡包括英国国内的受压迫者和国外的被殖民者在内的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最终走向衰落。因此,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深入研究中国,很难长久地与中国维持互利共赢的状态。少年小斯当东的散文气质和中文基础为他赢得了乾隆皇帝的好感,他在汉学研究上的努力与成果使他收获了一生的荣誉。他的汉学研究早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而是从整个东方审视中国、把握中国。他极具东方学视野的汉学研究与他的外交、政治志向相融,使其将毕生所学投入到英华关系推进以及英国的汉学发展上。鸦片战争虽然打败了腐朽的清政府,却未能走进中国文化内部,反而变成英国历史上非正义的一笔。鸦片战争带来的,是英国汉学家通过学术努力也难以抚平的中英交往的伤痕。
小斯当东具有东方学视野的汉学研究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刺伤中国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让小斯当东认识到从东方学视野深入研究中国的重要意义。因此,小斯当东创办皇家亚洲学会,推进汉学学科化,使英国的东方学与汉学研究联系起来,走向学科化、专业化,使英国汉学与东方学齐头并进,推动英国东方学、汉学成为整体与部分。事实上,中国与东方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在东方的地位,也很难深入地探索东方,当下的汉学家、东方学家需要反思并剔除英国东方学、汉学中存在的殖民主义思想,研究作为本体存在的中国、东方,进而更好地与中国乃至东方进行沟通与合作。
从老斯当东访华到小斯当东觐见乾隆皇帝受到瞩目到他积极创建皇家亚洲学会,从小斯当东推动英国汉学走进大学到当下英国汉学的世界化、区域化发展,这期间东西方的交流方式似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学术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在进一步唤醒人与人之间包容、理解之情时仍然任重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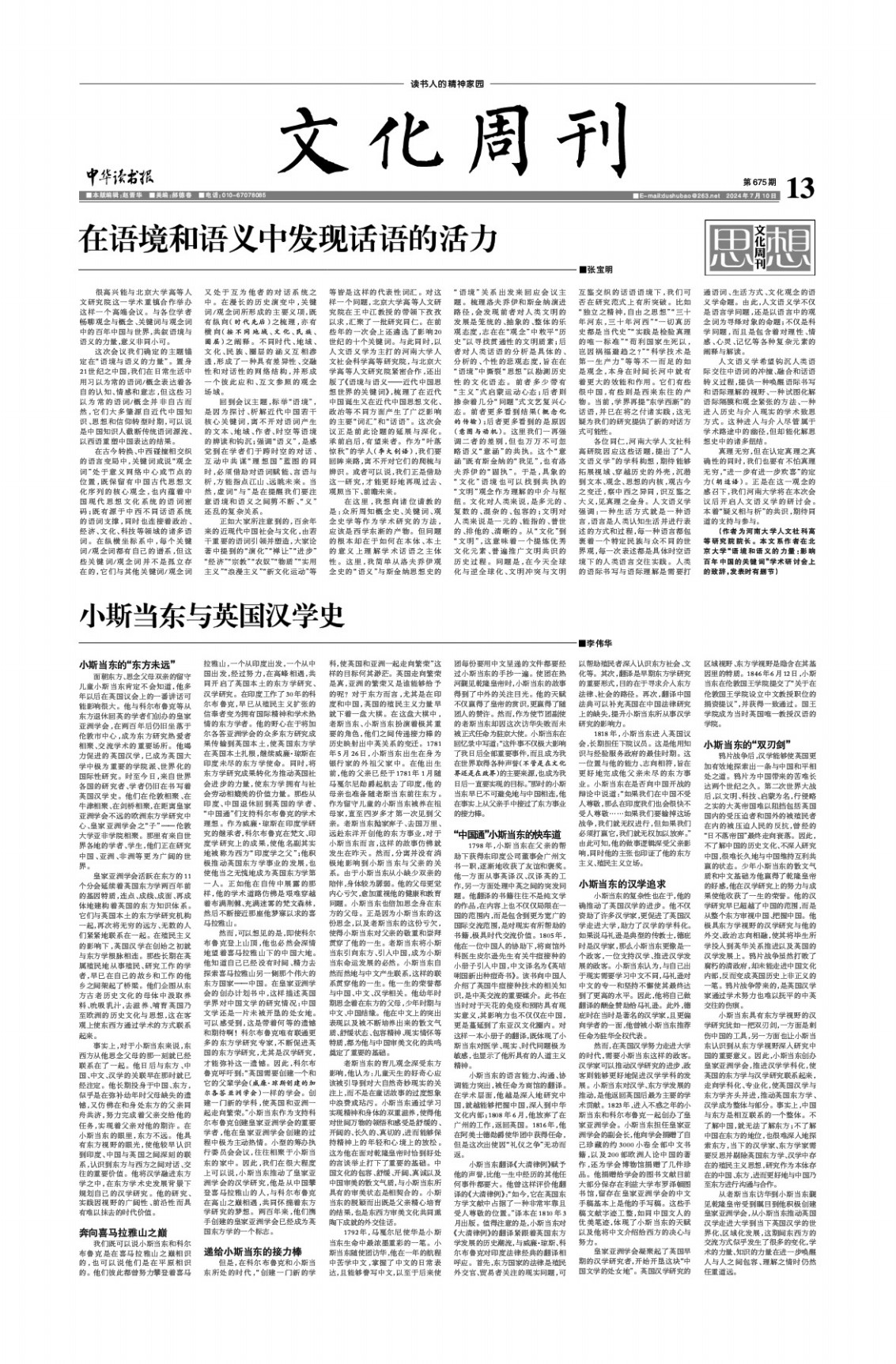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