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
彭明先生的五四情结
今年是彭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光如流、岁月如梭,转眼彭先生离开我们已15年了。我既非彭先生的学生,又不曾与彭先生有过同事的经历,我与彭先生的结缘,纯因两人的共同学术志趣——五四运动史研究。为讨教学术上的问题,我曾登门拜访彭先生,他在书房里热情接待了我,因此我有机会见识了彭先生的“五四书屋”。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60、70周年学术研讨会,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负责筹办。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大提出主办,各方面听此消息,唯北大马首是瞻,乐见其成。为筹备北大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组织了一个包揽在京各方面与五四研究有关的人士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彭先生当然名列其中,因此,会上会下我有机会与彭先生有过几次近距离的密切接触。这次会议没想到小有风波,会前我应召去了一趟相关部门报告会议筹备情况,当时彭先生也与会。会后彭先生、萧超然等先生又应约去相关部门说明、解释。
我与彭先生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他的80大寿祝寿会。在那次祝寿会上,彭先生谦逊而面带腼腆地讲述了自己的治学历程。
在我接触的老一辈学者中,彭明老师是有强烈的五四情结的,看他的《我的五四书屋》一文即可体会到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彭先生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1949年3月他与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先生一起初进北京城,第一个夜晚就住在胡适家的会客室。他回忆这个院落(传达室)电话是“5400”,“这个号码是胡适向电话局要来的,为了‘纪念五四’”。一个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住处号码。1984年5月他的《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调整住房,分配他住林园5楼4号,我想这应是人大对他的奖励。日后,胡华来彭家小坐,笑着说:“你刚进城时住过的胡适住宅的电话是5400。今天,你又搬进5楼4号,将注定你这一生要研究五四了。”这两则故事冥冥之中将彭先生与“五四”联系在一起,彭先生以这种风趣的形式将自己与“五四”并联起来,算是他留给我们的掌故。当然,第一则回忆可再作精确补充,据《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名录》载,胡适家的电话号码为50748,当时北京的电话号码已是五位数。门房电话号码即使是5400,也缺一位数,应在此前加上局号5,即5-5400。
人所共知,五四运动研究在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可谓显学。老一辈从事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学者,多多少少都与五四研究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史教学与研究从何干之(1906—1969年)到胡华(1921—1987)、再到彭先生,这是师承的一条线索。195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邵循正先生为首,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胡华则招收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两校各有侧重,这应是当时的分工。何干之先生是1930年代中期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著有《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7年)。他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和胡华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这两部教材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革命史教材的范本,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在新时期还多次重印。他们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以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可谓中国革命史教材的标准版。彭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史的范式里开启自己的教学与学术研究。1956年他为了编写教材,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1960年代初周策纵先生的英文著作《五四运动史》在美国出版后,彭先生不知从哪里获悉,激起了他写作《五四运动史》的冲动,从1961年撰写写作提纲,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他陆续撰稿约30万字,“算是打下了这本书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彭先生重新启动了五四研究,迅即出版了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两著,这应是他利用、整理积存旧稿的成果。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编辑了一本篇幅不大的论文集,共收文十篇,其中就有彭先生的《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民主、科学与社会主义》和他与胡华合作的《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显然,彭先生是有备而来,充分显示了他在五四运动史领域的研究实力。1984年4月他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运动史》,洋洋50余万字,这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五四运动史专著。中国人民大学虽然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的前辈学者不少,但1960年代以后真正专攻五四运动史的似乎只有彭先生。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他长期从事五四运动史研究,有过相关的多种著作,而且浑身浸透了“五四”情感,他是被五四精神形塑化、人格化的学者,他以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执着地延传五四精神。有人跟我说,彭先生在人大不是主流,意思是彭先生从没身居要职,但据我的观察,他也从未边缘化,他以自己的学术实力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
五四研究的代际递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五四运动史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作为研究题材进入学术界视野,到今天,这支研究队伍粗略计算大致经历了五代:
第一代学者出现于1930、40年代,以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为代表。他们初步探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爆发原因、发展历程、历史意义。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论著,将五四运动置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加以论断,以后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基本上都遵循毛泽东的论断,对五四运动史作出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范式的论述。华岗《五四运动史》(海燕书店,1951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华著现在很少被人提及,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一再翻印”,影响甚大。该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论述,如对五四运动领导者的持论,几成为中国革命史的基调。
第二代学者以彭明、丁守和、萧超然等为代表。他们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学者,彭先生、丁先生1947—48年在华北大学学习过。华北大学是培养中共后备干部和理论队伍的摇篮,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萧先生1949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他们三人都是在1950年代进入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领域。丁先生主编《五四运动文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9、1979)、《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著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初版、1979年修订版),在学术界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四运动回忆录》至今仍是人们研究五四运动史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北京大学校史》(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主编《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相对集中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一主题。通读彭、丁、萧三位学者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史的学术史演进来看,他们可以说仍是“中国革命史范式”在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的持续推动者,但对五四运动具体史实的论述,他们又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细化研究。在他们晚年,丁守和先生高举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成为五四精神的守灵人;彭明先生与时俱进,组织团队研究《近代中国思想的历程》《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积极探求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范式;萧超然先生热衷北大校史研究,回归老北大传统,表现出求真务实、笃学践行的学者本性。
第三代学者以陈铁键、杨天石、周天度、耿云志、唐宝林等为代表。他们是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前期大学毕业后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文革”十年学业受阻,改革开放后重新焕发青春,真正走上学术舞台。耿云志的胡适研究,唐宝林的陈独秀研究,周天度的蔡元培研究,陈铁健的瞿秋白研究,杨天石的钱玄同研究,这些个案研究都显现了新的个性化特点,表现出与传统的革命史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历史解析。如果从年龄上来说,他们与上一代学者只差十余岁,并不构成代际轮替,但学术风格确有疏离,他们在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较上一代人似乎更有冲劲。
第四代是“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学习的我们这一代学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搁,1950年代出生的学人直到1977年以后才获取高考的机会。人们常说的新三届(1977—1979年)大学生年龄跨度甚大,从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出生,挤在一个教室学习。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阶段一方面接受上一代人所给予的革命史教育和训练,一方面又受到新时期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时代大潮的冲洗下,逐渐培养自己的探索精神,乘借19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1990年代出现的“国学热”向前探索,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探究开始出现新的样态,从反传统到中西文化论争,从对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学衡派的重新评价到将五四运动史置于世界视野中去考察,呈现出新的个性化取向。罗志田的《复调的五四:一个自塑旋律的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我本人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五四运动的本事、纪念与诠释》(香港中华书局2023年)可以作为这一代人的个案标本。
第五代人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出生于1970年中期到1990年,也就是现在30—45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学人,他们置身于全新的世界视野之中,接受了跨学科的知识教育和学术训练,在讲究学术精致、学术个性化方面将有可能比我们走得更远。
我个人与上面第二、三代学人和下面第五代学人都有过密切的接触,从自己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从事五四研究的学者浑身充满活力,都有一股思想的激情,都有一本率真的性情,这也许是被五四精神感化所致吧!
五四精神的价值重估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之路。这是新时期的基本国策。新时期的40多年来,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五四运动的评估,对新文化运动的诠释自然也与时俱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与40年前相比确实已有极大的改进。今天我们该如何表达五四,这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不断被提及的一个问题。五四运动处理传统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我们今天也以这种态度来估衡五四,析取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五四精神。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揭橥民主、科学,为新文化运动树立两面大旗,这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精髓的提炼,也是对现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指引。五四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是选择还是背弃民主与科学,其命运可谓大相径庭。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选择看,民主与科学是我们未来仍将应该追求的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现今仍处在五四的延长线上。
五四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传统的倾向,但是否就以反传统,或如某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来标签,这是值得探讨的。五四对待任何事务都持批判性的态度——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不意味其否定一切,实际上,胡适对中国人文学术,如宋代以来的中国文艺复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以戴震为代表的反理学取向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批判性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较为稀缺的资源,它是五四新文化人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五四运动所表现的批判精神,也就是五四运动提倡的怀疑精神、独立思想,这仍是我们时代之需要。
五四运动处理对外关系,是抱持爱国主义与拿来主义相结合。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五四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大背景之下,西方科技领先于世界,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提出我们不能虚骄自大,要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绝不可封闭自守,搞义和团式的排外,当今我们仍要善于吸取这种拿来主义的精髓。
基于上述三点认识,五四研究虽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积累了相当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研究仍有继续努力的必要,有继续拓展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弘扬五四精神,而是真正推进中国学术、社会与文明的进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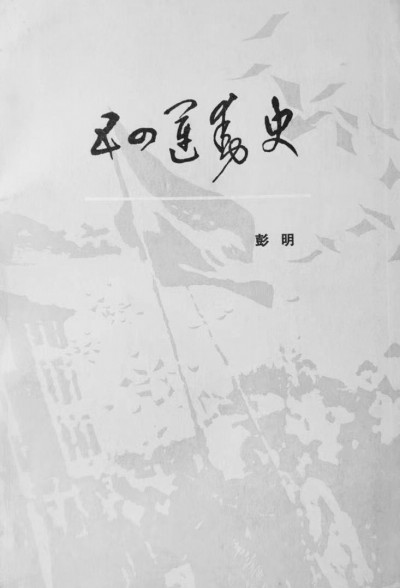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