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岗街道,无论大小,都叫他文叔。
我在宝安下辖的松岗街道见到年过七旬的文业成之时,文体中心办公室的冯主任正叮嘱他,拟安排他春节前下社区去写春联。文叔走到门口,忽又折回,到里间去索要了一款宣纸。他走来走去的姿态,有点跛;下台阶的当儿他告诉我,前一段搬农具不小心砸到了脚。话题便很自然引到了木器农具上,他用粤式普通话与我交谈,才讲几句便叹了一口气,那似乎一言难尽。我的小车从大车川流不息的107国道下面穿过,折入几条起伏不平的窄巷子,七弯八拐,到了他的家门口。一栋局促而高耸的自建房,仅仅一个车位,文叔下车开了锁,放倒铁栅,我才得以小心泊入。
随文叔进得家来,楼房与平房之间形成的一条过道,是他的画室兼会客厅。左手的案台上铺着毛毡与宣纸,右手的矮壁上张挂着他写的字画,尤其是水墨虾画;一张张斗方上钉着一枚枚不同颜色的吸铁石,宛如一个个倒挂的将士布阵。我一大早自福田区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个小时,来到与东莞交界处的松岗见文叔,是想来欣赏他的木器农具的,毕竟2015年获批区级非遗项目的“木器农具制作技艺”,文叔文业成是唯一的代表性传承人,此项目还拟向市级非遗项目申报。他却没有马上起身带我去参观木器农具工作坊或陈列室的意思,沏了一壶铁观音,与我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一段七旬深圳原住民的过往,虽未必惊心动魄,却也折射了一个民族沧桑的背影。
如今客居深圳七八百年的宝安文氏、福永文氏、岗厦文氏……以及香港文氏,都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抗元兵败的文天祥之宗脉,信国公的慷慨赴死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绝唱,更是千古而下,崇仰者不绝如缕。
既是文姓,文业成的祖上不问可知,文氏祠堂是一个大家族的共同宗奉。显赫的背景早已在时代的沟壑里辗转泛黄;凋敝的村貌与贫瘠的生活,才是文叔及其乡亲未曾泯灭的深刻记忆。10年前去世的父亲,在世时种过田,摆过摊,做过饭(人民公社大食堂),收过破烂,染过布——那时候,穿衣与吃饭一样困难,乡下穿的衣服多半是浅色布裁剪的,灰不拉搭的,父亲就挑了一担染桶走村过街上门帮人染布。文业成最深的印象就是父亲的一双手,粗糙还在其次,靛蓝或漆黑的染色深深印进了皲裂的手心与手背,永远也无法洗干净。文业成在松岗念完几年小学,便到6公里外的公明去念中学:早出晚归,一个单程就得走个把小时,那正是全民困难的年代,早晚在家吃得少,在学校又没得中饭吃,挎着书包归家途中,便觉得路途遥远,几乎支撑不住。一些同学见他可怜,不时接济他一只红薯,或者一个小小的饭团,他便觉得是人间至味。如果褒奖与信心能当饭吃,文业成应该时常缅怀短暂而荣耀的初一生活,他的成绩在班级
拔尖,书法尤其成为示范,以至他在同学嫉羡的同时,成了老师的宠儿。下面这个事例,可以说明他受老师青睐的程度:刚进初二,贫病交加的母亲才40多岁就去世了,原本一个六口之家——如果加上双方的老人当然更多,失去了一个善于勤俭持家的主妇,更形艰涩,文业成不得不辍学了。公明学校的班主任得知后,急得次日便徒步来到他家,见到一个家徒四壁的逼仄宅院,老师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本备好的斥责全都咽下去了,吐出来的是一个亮堂堂的主意:我会动员全校老师,每月每人出一两块钱,无论如何你要读完初中,上了高中,最不济也可以上惠阳美工学校啊! 文业成婉谢了老师的美意,一则,学校老师每月工资也就20多块钱,他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二则,困境中的一个家,也需要长子早点出来分挑担子。老师再三劝说罔效,只得一步一回头,怏怏而返。
那是一个全民日夜辗转的心思都在口腹的年代。文业成待在家里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为另外三个兄弟姐妹以及父亲瘠薄的身子里,多增加一点卡路里。尽管家里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任何物品都弥足珍贵,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一床三成新的蚊帐剪成了一张网,四边支起弹性十足的竹篾,扛在肩上,下到河边去捞虾,饵料便是网兜里的一把糟糠。捞上来的小虾,并无油盐佐料,柴灶上清水煮沸,身边的弟妹,顾不得烫手,拈起就放进嘴里,还没有品出味来便滑入了饥肠。他很快想到清早去了水利工地的父亲,抢了几只虾盛到一只粗瓷碗里,盖上,任是弟妹眼馋也不得染指。那些身体剔透,触须妖娆的活虾,不仅陪伴他度过了国运迍邅、穰少仓空之荒年,也慰藉了少年一段精神枯寂的岁月。直到他业余与绘事为伍,虾,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画物,源头盖在于斯。
用竹子或木头做一些简单的物件,一只渔网,一对吊桶,一张凳子……工具或家具,或是从这些身边基本的琐屑之需开始,点燃了他用手工制作来烛照大千,省视内心的微光。包括再普通不过的饮食生活,一箪食,一瓢饮……除了食与饮,还有箪与瓢啊! 他喜欢脚下散乱的散发着草木清香的材料,经过一双糙而巧的手把玩,就弄成了一件件实用的什物,入水可捞鱼,上灶可蒸饭,下田可锄草,秋收可脱谷……
一辈子辛勤劳作的父亲不干了,他知道稼穑艰难,难得温饱,他一个大活人早出晚归,依然养活不了一个家便是证明,他要长子出去觅一份工作。一个社队干部见小小年纪的文业成晒得黑不溜秋的,心生体恤,安排他去供销社搞财务,从出纳起步。那时候恰逢“四清”蓬勃而起,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看到一些平时并无坏印象的财会人员挨斗挨打,生性胆小却敏觉的他,足将进而趑趄,不敢说怕,推脱文化低,没能力,做不
了。父亲叹气道,那你就去学一门手艺吧,总不能一天到晚捕鱼捞虾过一辈子吧?! 他回答,只要不会挨斗,学什么都行,再累也不怕!
父命下达:去学木工吧。
文业成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去松岗木器社学艺了。学徒要吃苦,他懂;学徒要从杂工做起,他也懂。木匠的杂工与学徒,从锯木头开始,任是杉木、松木、樟木、梓木……,任是锯三分板、五分板,长料或短料,方料或面料……,师傅的一声咳唾,一个眼神,都是无上的威严。从春夏锯过秋冬,从东家锯到西家。双手磨出的血泡一次次结痂,双腿绷紧的马步一次次进退,脚下的泥土被汗水濡湿,身边的板材堆成了小山。
如此的虔诚,如此的卖力,三年一弹指,感动了师傅——手艺只能在自家血亲中传承是乡村各类手艺师傅们的共同遵奉——师傅时或给予一些点拨,更多的学习则有赖徒儿的悟性与勤奋。犹记得,第一年月薪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22元。学徒期满,大多数人并不能独立制作一件家具或农具,文业成却基本上都能上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考试,完全合格。这时节,木器社易名农具厂,分为木器、铁器、电器、机修与五金一共5个车间,木匠文业成自然留在木器车间。为了生存,亦是社会需要,木器车间小到盈盈一握的饼模子,大到学校教具——单双杠、木马都做,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农具——牛鞅、打谷机、禾桶、秧船、木制步犁、手摇水车……访谈至此,文业成谈兴渐浓,起身抱过来厚厚一叠翻拍的图片,他说,各种农家具合起来有300多种呢! 手头的这些翻拍图片,尽数黑白,线条斑驳,掩映着一个渐行渐远时代的斧凿之声。
就这样,在木器制作的铿锵声中,在各式木料气味的包裹之中,文
业成一直做到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1978年,先我着鞭的深圳,大面积的农转非,所谓“洗脚上岸,三来一补”,将此前大量的农民“转业”为工人,农具厂歇业了。文业成欣慰中夹着几许惆怅,猝然意识到,木器农具不再批量生产了,以前干活的家什,淡出了历史舞台,便会渐渐成为珍贵之物! 于是,他果断到家家户户去收购——南方多湿,这些农具一是闲置,二是无人妥为保管,不说任其日晒雨淋,就是无处不在的白蚁,也很快会将其一一化为齑粉! 事实上,他在收购过程之中,一些已然被蛀烂。
1978年的文业成,正当盛年,被委任至新办的电子厂做管理之职,仍心系木器农具,在不断收购的同
时,毕竟还有一些种着闲地的村民,不时带着农具找上门来请他修补。木工修补何处寻? 如今唯有文业成! 硕果仅存的木工师傅,居住之地撑不开,房前屋后都是修理场。一是有需要,二是自己喜欢,若问孰轻孰重,还真不好讲呢! 他朗然一笑,遂成低声:整整做了一辈子啊,到今天都放不下啊!
是的,六七十年代饥馑与运动叠加如潮,他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先后逃港。一则为了照顾病弱的父亲,二则也放不下手里的斧钺刨锤,他守护着孝道与岗职的同时,也注定了与贫困为伍。
我与文叔相向而坐两个多小时,他口中念念叨叨的始终是木制农具,我心里越来越渴望看到一个农具的堂堂阵列——说实话,我南来近20年了,在岭南各地的大小陈列馆里,始终没有看到过一个像样的木器农具展。我固然没有天真到,期望在文叔这里看到如秦始皇兵马俑队列的无声风雷一般,木器农具裹挟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烟云扑面而来,却希望此行不虚,可以获得超越那些公办与民间博物馆的木
器农具给我以一份餍足。文叔的水墨虾画与淋漓的行书与篆体,获奖很多,但,这并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些笔墨,我想只能算一个老木工手艺的副产品。
在我的一再邀请下,文叔沉沉起身,径向后门走去,我尾随在后。
后屋窄窄一条路,转右上几级台阶,便是宽约两三米的窄窄一块长方形水泥地。有一位中年女子在压机井旁洗菜,伸过去一接,水温暖手。机井的两边,各搭建了三个不同大小的铁皮屋顶,各有一二十平方米,文叔信手一指道,喏,它们都在这里哟
……
面前层层叠叠的堆放,令我着实吃了一惊。
沉重的牛鞅,仿佛还在传递着水牛犁地时的喘息;手摇水车,吱吱呀呀唱着祖辈耕作的古老的歌谣;木制田耙宽约数米,需几个壮汉合力才能抬下田埂;双轮脚踏打禾机,较之禾桶已有半机械化的意味了……我从小在赣西的城乡接合部生活,学生时代参加过春插、双抢与秋收,深圳乡村的用具大都与赣西相同,却也有不同的,譬如除虫梳,类似一把带柄的大木梳,文叔告诉我,这是禾田除草的工具——那时候既少化肥,亦缺农药,更无除草剂;还如秧盆与秧板,是拔秧之后,在水田里传递秧苗之用;谷磨——一具木凳、篾围与石磨的结合体,20世纪60年代之前常作稻谷脱粒之用。还有一档20世纪70年代之前,农村主要的运输工具鸡公车,木轮、木架、木托,形状类似我在赣西见过的独轮车。赣西的独轮车货物主要放在两侧,鸡公车的货物是置放其上的;还有一个不同,赣西的独轮车主要是铁轮,此为木轮。当年很多乡镇的青石板街镇,中间一道凹槽,便得独轮车年代久远的碾压之功。文叔说,鸡公车是北方带来的叫法,本地叫辘头,因为支起来的货架子,形似鹿角。辘辘,还是一个象声词,勾画起苍凉、婉转而渺远的意境。
几十件农具在这三个无墙只剩顶的堆放处,毫无陈列的意思,难怪文叔始终不好意思带我过来看了。最里间铁皮屋的横梁上,文叔张挂一纸横幅,上书:宝安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器农具)暂时存放室。外间则张贴着手书的《深宝府〔2015〕27号》文件的片段,这个文件我拿到一个附件,名称很长:《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深圳市宝安区第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文业成是文件里7位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项目为“木器农具制作技艺”。这时候,他终于说到自己的苦衷:虽是区级非遗的唯一代表性传承人,接下来还要向市级申报非遗,但却没有一个工作间,没有一个农具存放处。他说:“前年到广东省一个生活博物馆去参观,农具部分的只有5件展品:犁、磨子、水桶、耙子、风柜。我这里保存的农具不仅仅是深圳,甚至也可能是广东省保存最全的,堆在这里,这样的条件,要不了多久,就全完了呀。这块地原本就是我祖上传下
来的,我想建一个木器农具博物馆,将它们好好归置一下,却始终不获批建……我那边还有更多呢。”说着,他带我穿过前门,到路口,左手边一个工厂,他开启地下室的锈锁,一股霉湿之气扑面而来。下到黑漆漆的地下室,墙水滴答,蛛网高张,老鼠四窜,从各处搜罗来的家具、农具和木料尽管悬空放置,其危殆之状况也令人触目惊心。他说,这几年,光被白蚁蛀蚀的木料,损失即达几万元;下大雨的时候,地下室全被水淹,下不去脚。
访谈了一个上午,饥肠辘辘,又被地下室一股浓烈的霉湿气包裹,我想抽身逃离。他却越说越来劲,不管身边人在不在听,管自一件件地拿捏、抚摸与喃喃自语……我忽然感觉,他不一定是要讲给我听,他是要倾诉或言说,他倾诉或言说的对象,就是眼前这一件件来自晚清、民国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农具与家具,它们都是一个老手艺人的孩子、宠儿。一个一辈子没有放下过锯子、锤子、刨子和凿子的老木工,他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用自己方圆百里几乎是唯一的技艺,让它们一一翻转腾挪,活过来,走进一个亮堂堂的博物馆或陈列室。他还想在这个博物馆的楼上加盖一个画室,除了自己爱画的虾,爱写的春联,他还会将一件件农具的修复过程一一描绘下来,让后人知晓全过程。我们都是土地的子孙,后人不应该完全不晓得稼穑之艰,田亩劳作……你看就是这一架鸡公车,运粮食、运猪崽、运种子化肥,他还做过一架小小的鸡公车,专给孩子推、坐、玩耍。
在街头一个客家菜的酒店二楼,我请老人吃罢午饭,答应要为他吁请。访谈之时,正是岁末,写作此稿之时,已入新年。我知道文叔念兹在兹的就是一个场地,他也给我带来了一份他署名的《关于筹建深圳第一家农具博物馆的申请》。于是,我询问一位曾经在街道工作的颇有人文情怀的女干部,她微信告诉我:“……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之前也做过协调未果,涉及宅居地和违建之间的政策和定义,曾多次希望文叔提供更有力的证明,但后来就没有得到他的回复了。”
我想,倘若违建,当然不可取,起而效尤者将势不可挡。如果能帮助找到证明,这块地基确实属于文叔的自建范围,相信以他的日渐衰迈之年,博物馆放在家边,守护与修理会便利许多。况且,农具与人,相得益彰,那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过往啊。即便不能自建,也需要相关方面及时为这些日益残损的农具找到一处栖身之所,在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大厦连云之侧,开办一个深圳木器农具博物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比较、观照与遗存啊!
古人有句: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后生小子们,侧耳倾听,不要让这些老成凋丧之先人留下的物什“如水去”了呀。
(本文摘自《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南翔/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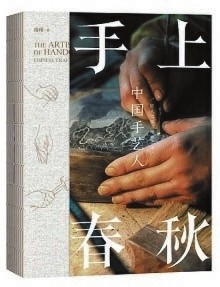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