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群
《诗经》,又称《诗三百》《三百》《诗》,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歌唱诗选集。内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按照音乐体裁和实用功能,分编为《风》《雅》《颂》三类,总共311篇,其中《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笙诗(只有篇名无歌词)6篇。它们原先都是声诗,彼时每首都配有能唱的乐谱。所配乐谱在汉代肇始已全都失传,传留后世的只有文字形态的歌词唱诗。
《风》,也叫《国风》《十五国风》,主要是在村落、宗族家庙、神社、山林水泽等处招神、祭祀活动以及民间聚会诵唱的底层土风歌诗。《雅》主要是周王、诸侯、贵族文人的宗庙、神社祭祀神祇、祖灵礼仪中巫师领颂之宴飨歌舞唱诗。《颂》主要是周王宫廷、宗庙告于神明、祈愿福祉行天子大礼祭神的歌舞唱颂诗篇。
挑选《诗经》精华,以适中的篇幅普及推介,首选其《风》,应该说是最佳选择。因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郭沫若)。美国编纂出版的《大美百科全书》也称“《风》保存了许多农民和工人的口头创作,且往往有集体创作的迹象,是整部《诗经》的精华”。最具青春气质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风》,最能与当今青年读者愉悦亲和的古代民间文学作品还是《风》。
《雅》《颂》重在炫示作为王家、贵族礼乐表演形式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时兼具参与侍奉大祭、构建政治话语的双重属性。《风》则作为底层民间唱诗,主要具备家族、宗族世俗祭祀娱乐表演文本的属性。《风》甚少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干预,也少见官方制式、冗余语言的侵染;彼时尚无诸子杂说纷纭籍籍,没有儒佛道桎梏掣肘,还没产生与现实社会形成倒影对应的神仙谱系;它不媚权,不载道,不帮闲,不虚饰,不宗理路,不落言筌,游离于历史宏大叙事和权力管控之外,民众就是自己诗歌领域自主的统治者。它至简、至朴、至拙、至纯到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
如果试图从《风》中挖掘史籍、理学的需求做“即诗证史”“即诗证道”的确认,至多只能找到一些草蛇灰线。但是,如果欲感知当年的民生民风民情,却是丰富厚实,形貌灵动。彼时留存的记忆,人类典型情感都有所体现,由此可以触摸到《风》中的人们遵循伦理道德、至诚向善的血脉温度、积极用世的搏动心跳,感受古时紧接底层生活的地气和充溢生命活力的元精,是体现普通民众灵与肉的生命彩绘。
《风》诗顺从天命天道天理天意,视自己内心良知的自然本性为理性,于民间立场俯身土俗文化绿洲,造就体现自己旨趣的祭祀唱诗乐土,奠定民歌-民间文化从此与官方文化并存的基壤。自诞生始它就具有长寿基因,从未在中国历史中退场,作为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认同标识,踵事增华煌然穿越时空入今。它是自由灵魂创制的自主唱诗,与当代文明提倡的价值观融洽对接,以“冻龄”的青春、依旧的朝气、仍然的新颖、犹自的率真,睥睨一切反文明、逆人性、悖人情、违真心的文艺。它如一炬燃着,纵万火引之,千百年来,却炬火如故,光焰永不熄灭,当然地成了中华民族和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诗经》文本,有说经过孔子编选、编排,或删汰、修改和配曲。另有考据说,将《诗经》形成过程系名于孔子的介入,是经学家的攀附指派,误导的史实。此考据给出的实证是,“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孔子是公元前551年生的,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其时孔子年甫八岁”(清 方玉润)。也就是说,孔子虚龄八岁之时,《诗经》早已成了三百篇之定型在鲁国演唱了。
日本学者家井真近年对于我国彝器、钟鼎铭文、上古文字和韵文研究,一定程度体现当前国外《诗经》研究的学术前沿水平,他认为“《国风》诸篇基本上是各国的各种降神仪礼诗”。一旦据家井真的观点搬演《风》诗演绎方式,唱诗动机和原著真义大多变得豁然开朗。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巫者(灵媒)引领的。在祭祀之中,营造亦幻亦真的异境,建构与祖神沟通互动的机制,导引人们心灵自由袒露和情绪宣泄。人们沉浸于演颂、献辞、音乐、舞蹈、文学诸种娱悦游艺方式的通感刺激,展开人与神之间虚拟的交互性对话。
后人对祖神亲切如对活着的长辈,既敬畏又亲昵,既拘谨又撒欢。歌诗内容往往率真朴实,讨喜逗乐,放诞掺入肃穆,情色借壳端庄。灵感一飞扬起来,歌抒情、诗言志,庄重便夹杂谐谑,神圣性融入凡俗性,催发、生成了一首首口头创编的抒情或叙事歌诗,演唱者不啻都是诗人。如是起源语境造就了《风》诗,也开了我国民间群体共同口头创制表演性歌诗的先河。
同样体现国外《诗经》研究学术前沿水平的,是德籍美国学者柯马丁对我国竹简、木牍、帛书和纸质典籍的研究,包括对近年考古发掘文本的观察,他发现《诗经》在版本唯一化之前,存在文本间相互渗透互文变异的现象,形成了关联的“语料模块”构成的“文本素材库”。柯马丁揭示的《诗经》文本文化现象,正揭示了《风》的生成符合民间文学创作的规律。我们完全可以遐想,彼时在频密祭祀仪式上表演散作的歌诗精华,是集体创制的运思、主题、题材、唱词的“语料模块”,具有很强的可配置性,经选编、整合,成了多种“复合文本”式的诗篇。这些文本实体,名义是平行的、互相独立自洽的,其实,单独篇章、篇目数量、构成顺序等方面又是互涉的,都不同程度共享有“文本素材库”里的“语料模块”元素。
这些同题的不同文本经历了演变和繁衍,分别从口耳相传转化成文字,转化成篆书或隶书,转化在竹简、木牍、绢帛的载体上,开始以文字抄本的形态流传。但是,欲考察《诗经》诸多流变文本的时间谱系,欲确定谁是发源始祖母本,谁是沿袭拟作,谁是增删重构,谁是原本、副本、抄本,以及欲推导谁是各篇章的原创作者,谁是《诗三百》首次集大成合成文本的编选人,如今已经无异奢望吹影镂尘、炊沙作饭。
在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主流阐释意图和文字、音韵实用语境里,官署与词臣共谋,最终选定了写本的《毛诗》(盛行东汉的鲁国毛亨、赵国毛苌所传的版本)来统摄各种驳杂的“复合文本”,以此作为《诗经》“定本”。原先共时性并存的几可与《毛诗》平分秋色的多元写本,便在历时性淘洗过程中渐次被废置、消抹、湮灭。
最为侥幸的是,先秦之《诗经》,秦时“焚书”不在禁毁之列。汉时定本之《诗经》,难免经由再次甄选、修改,但是,其《风》毕竟最终得呈独异的风貌和品性,以自己的民间立场、创制旨趣、诗性特质,与《雅》《颂》大相径庭。从此,它披着如是汉代衣冠特立独行,秉持昔日周时民间赋予的素朴风仪、群体精诚、刚健气质、青春神韵、诗性境界,凌空独亮,明示自己不入孔孟、经学之彀,截然与其后的骚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时代文人化、个人化、应制化、纪史化的文学向度不同,品格不同。尽管每首精短涓细,一旦汇流成《风》,整体却呈“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之气象,堪称空前绝后的奇观,再难奢望还能有这般精神自由的群体口头文学作品选集重生。
《风》诸多篇章句子和词语呈现着涵义的不确定性,在表体文字后面蕴含着宽广深叠的解读空间。《风》毕竟是诗,“诗者,吟咏性情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读解的进路惟应还是归于诗歌去行远自迩。
胡适说,“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也。《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
拙作取名为《天魅地香——〈诗经·风〉与新民歌的古今交响》(漓江出版社2024年6月),倒不是以出版年月新近来示好,而是确实有摆脱经学家的桎梏,回溯《风》的不老生机,亲和年轻读者的念想。读《诗经·风》,固然是读其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读其人,那彼时制作它的,以及享用它的时人。它那历久弥新的感情抒发,保留着时人热血的温度,足以感应到“《风》中之人”的青春神采。今日的研读,如果不能揭示《风》昔日的鲜活、鲜灵、鲜亮,如果没有体察入微的见识,只是低层次重复把玩其古旧,那是太没劲了。恃青春青涩、青春梦多、青春无忌似的勇气,将一股活性冲动注入新译和新说,在理念气质的体现与内容器质的营构方面,追求构建自己的传述个性,再现原著禀赋的古老而朝气蓬勃的青春气质,才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笔者在前人砌垫的基座上,试图再度思考《风》的创制语境、演绎秩序、生成方式、文本结构、内容解读、精义阐释、诗情所在,尽力拓宽对《风》的观察视野,寻找更多元、更宽容的释读可能性,复原其可与当代思维共鸣、共振、连通、吻合的情绪。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研究、诠释《诗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先哲们始行于学术荒漠,拔钉抽楔,疏通路径,洞幽发微,渐次破解上古艰涩文字的阻障。许多学者循本从始,让《诗经》的当代汉语翻译一路生花……尽管如此,前人都谦称自己的著述和翻译距离至是至当尚远,叹息尚有许多未来得及曲尽酣畅之处。这正体现了这部伟大经典魅力无穷,含蕴宏富,难以穷尽真义,仍然存在大有可为的有待填补的空间。
古《风》逢时又青春,含英咀华更宜人。“君诗如民谣,能共天公语”(宋 苏泂),一首首《风》诗,如同霁日高天云中飘浮的雨丝风片,泛着七彩光艳,飘传袅袅天籁;笔者的新译新说,试图跨越时空去追接那瑰丽的风片雨丝,近切折射那光艳七彩,回响那天籁袅袅。很期望牵手读者去会见那些永远不老的云上“《风》中之人”,达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的境界。
(作者系漓江出版社原总编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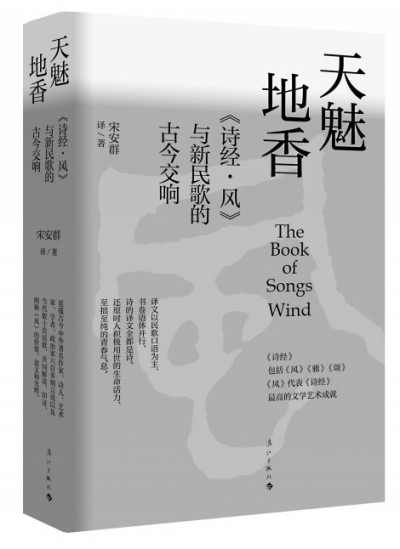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