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勤俭
白石老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勤俭相始终。他一辈子持家和律己,处处不忘“勤俭”两字,他的生活,勤奋、朴素而严肃。他每天起床很早,夏天,清晨四点来钟就起来了,冬天,也不过六点钟。无论冬夏,他起身总在天刚放亮、晨曦未上的时候。晚上入睡,差不多在九点钟前后。除了身体不适卧床患病,和偶或在外看戏应酬以外,从不晏起晚睡。他作画是每天的日课,向来没曾间断过,从早到晚,不是默坐构思,就是伏案挥毫,尝有诗句道:“未能老懒与人齐,晨起挥毫到日西。”又有诗道:“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只有几次大病和遭逢父母之丧等不幸事故,才停笔过几天。平常日子,偶因心绪欠佳,停了一天或三两天,事后总要补画的。他题画时尝写道:“昨日大风,未曾作画,今日作此补足之,不叫一日闲过也。”他常对学生们引用韩退之“业精于勤”的话,自勉勉人。并说:“我由木匠而雕花匠,又改业画匠,直到如今,靠着卖画为生,略有一点成就,一句话概括,就在一个‘勤’字。”他的画上,有的题着“白石夜灯”四字,都是在晚上灯光之下画的。到了晚年,目力衰退,往往戴着两副眼镜,照样工作。
老人的衣食用品,向来是力求俭省。穿的既不讲究(一件衣服总得穿上好多年),吃得也很简单(平日喜欢吃的,是炒倭瓜酱和丝瓜烧小鱼之类普通菜)。七十岁以前,尚能咀嚼花生,常用盐水煮了来吃,还时常买些“半空儿”(即花生,因有的有实,有的无实,叫“半空儿”)的用来待客。七十岁后,牙齿不行了,喜欢吃面食或稻米粥,荤腥更不常用,专吃些蔬菜。他早年在家乡时候,一年四季吃的瓜果蔬菜,几乎都是自己种的,很少花钱去买。定居北京以后,沿着旧例,照样栽种。他住的跨车胡同宅内,有株葡萄就是他亲手种的。秋天,客来访谈,他总要摘些葡萄,请客尝尝。院内空地,又种了许多瓜菜。尝有《种瓜忆星塘老屋》诗云:
青天用意发春风,吹白人头顷刻工。瓜土桑阴俱似旧,无人唤我作儿童。
又题画芋头的诗云:
叱犊携锄老夫事,老年趣味休相弃。自家牛粪正如山,煨芋炉边香扑鼻。
又云:
万缘空尽短灯檠,谁识山翁不类僧。但得老年吾手在,芋魁煨熟乐平生。
这几首诗,都写出他种菜的意趣。他又有“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香”的诗句。三十年前,他画过一页《白菜》扇面送给我,题着:“他日显扬,毋忘斯味。”又尝题画云:“余有友人常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画之似,何也? 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他总认为咬菜根是人之立品的要着,而所说的“蔬笋气”,确能道出他的个性。他有《燕市见柿,忆及儿时,复忆星塘》的诗句云:“紫云山上夕阳迟,拾柿难忘食乳时。”他幼年贫苦,拾柿充饥,到了老年,景况虽是好了,依然不忘寒素,不忘自己是在贫农家庭生长的。
老人平日居家过日子,件件事情都得由他亲自经手。门户箱柜都加上了锁,大小钥匙一连串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家里人买点东西,无论用钱多少,必须临时去向他要,他认为需要买的,才亲手去开锁取钱,从来不叫别人代劳。他深深地体会到物力维艰,对任何东西都十分爱惜,决不轻易毁弃。他作画所用的画笔,有时笔头掉落或笔杆裂开,只要还能对付着用,他总是亲手用生漆涂上,阴干后拿来再用。他做了一首《笔铭》:“破笔成冢,于世何补。笔兮笔兮,吾将甘与汝同死!”他惜物的心理,简直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向来书画家所用的印泥,都是很讲究的,因为印泥讲究,印泥的盒子也力求精致,不用古瓷,也得用细瓷。我曾在南京买得一只康熙官窑五彩大印泥盒,配有硬木座子,拿去送给老人,他见了虽很喜欢,却对我说:“印泥盒子瓷的不如玻璃的好,玻璃的不吃油,久藏不变质,价格既便宜,又合实用。今人爱用旧瓷,还看重官窑,这玩的是古董,和作画张口宋元一样是装门面的。”
小住张园
明督师袁崇焕的故宅,在左安门内龙潭南岸,今称新西里3号,内有“听雨楼”等名迹,清末废为民居,荒芜不堪。民国初年,先父购置为别业,修治整理,种了不少果木花草,人都叫它为“张园”。老人很喜欢这个地方,说此地“有江南水乡景色,北方是很少见到的,住在那里,可以洗涤身心”。先父在世时,常常请他来此消夏。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他来住了些日子,我向先父建议,把后跨院西屋三间借给他住,又划给他几丈空地,由他去莳花种菜。他非常高兴,在屋内挂了一张他亲笔写的“借山居”横额。每天作画刻印,清晨和傍晚,常在房前屋后散步消遣。他那时画了不少幅鱼虾草虫,都是在那里实地取材画成的。有一次,我陪着他在附近池塘旁边站立了很久,我知道他是观察池塘里鱼虾活动的姿态,不去打扰他。第二天清早,他画了一幅《多虾图》,许多的草虾丛集在一起,多而不乱,生动得很,简直同水里的活虾一样,令人看着,有悠闲的意趣。这种笔墨,可算得前无古人的了。他说:这幅《多虾图》,是他生平画虾最得意的一幅。他画成之后,挂在“借山居”中间的西墙上面。到一九三三年的秋天,他又来到张园,在画上补了题跋云:
星塘,予之生长处也。春水涨时,多大虾,予少小时,以棉花为饵,戏钓之。今越六十馀年,故予喜画虾,未除儿时嬉弄气耳。今次溪仁弟于燕京江擦门内买一园,名曰张园,园西有房数间,分借与予,为借山居。予画此,倩吾贤置之借山居之素壁。
又在《张园春色图》上题诗云:
四千馀里远游人,何处能容身外身。深谢篁溪贤父子,此间风月许平分。
他给我的胞弟仲葛画了一幅《葛园耕隐图》,题诗云:
黄犊无栏系外头,许由与汝是同俦。我思仍旧扶犁去,那得馀年健是牛。
翌日,又补题了一首诗:
耕野帝王象万古,出师丞相表千秋。须知洗耳江滨水,不肯牵牛饮下流。
诗后附跋云:
画图题后,是夜枕上,又得此绝句。
他说这些诗句都是他的由衷之言。他在张园“借山居”的墙上,挂上自己的照片,作了一首《示后裔》的诗,写在相片的旁边,诗道:
衡湘空费卜平安,生既难还死亦难。后裔倘贤寻旧迹,张园留像葬西山。
他因民初在故乡不能安居,避乱来到北京侨寓已逾十年,有家归未得,思乡之念总是不能免的,而对于我家张园,却很有点恋恋不舍之意。
张园的北边,有袁督师庙,也是先父出资修建的,相传庙址是督师当年驻军之所。庙东池塘的边上,有“篁溪钓台”,是先父守庙时游憩的地方,老人和先父在那里一起钓过鱼。后他同他的弟子瑞光和尚合作画过一幅《篁溪归钓图》,送给先父。并题诗云:
竹绕渔村映晚潮,西风黄叶渐萧条。篁溪日暮持竿去,芦荻闲洲路未遥。
他在张园小住的时候,常同先父和我遍览附近法塔寺、太阳宫、万柳堂、夕照寺、卧佛寺等许多古迹。袁督师墓在太阳宫东北,每年春秋两祭,我们广东同乡照例前去行礼。他应先父的邀约,也曾参加过。夕照寺墙壁上,有陈崧画的松树,笔法苍秀高古,他每去总要流连很久。而卧佛寺则相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家道中落之后,约在迁居京西香山的前几年,曾一度在这里住过。老人他慨叹曹雪芹的身世,曾经根据我作的诗,画过一幅《红楼梦断图》,并在图上题诗云:
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
诗前有小引云:
辛未仲夏,与次溪仁弟同访曹雪芹故居于京师广渠门内卧佛寺,次溪有句云“都护坟园草半漫,红楼梦断寺门寒”,余取其意,为绘《红楼梦断图》,并题一绝。
他送给我的这幅图,我早已丢失,不胜惋惜之至。
交游种种
一九二〇年九月间,老人和梅兰芳相识,是由齐如山介绍同到梅家去的。那时,梅家在前门外北芦草园。梅兰芳正式跟他学画草虫,则在一九二五年。据说,老人画草虫是从长沙一位姓沈的老画师处学来的。这位老画师,画草虫是特长,因为没有儿子,把自己生平的绝艺,都传给了女儿,不肯传给别人。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老画师早已亡故,他认识了老画师的女儿,得到了老画师画草虫的底本,专心研习。后来他的草虫画就出了名。梅兰芳虽是从他学画,但他并不常去梅家。梅兰芳的书室“缀玉轩”里,经常备有很精致的笔墨笺纸和颜料印色等,是专备客人中的书画家随时挥洒用的。老人平日作画,章法构造总是十分慎重,有了腹稿,也要再三斟酌,非得认为没有什么疵累,决不轻易动笔。所谓“急就章”,他向来是“敬谢不敏”的,这原是他对作品负责的优良作风。梅兰芳交游广阔,家里常有宴会。那时的风尚,宴会多在晚上,往往直到深夜始散。老人有早睡的习惯,也就不能常去参加。他曾对我说过:“听戏熬夜,还算值得,朋友应酬,大可不必奉陪。”实则另有一个原因:他是不喜欢和人多作周旋的,尤其在生客丛中,更是视为畏途。王湘绮给他印草作序,曾说他:“朋坐密谈时,有生客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有人说他性情孤峭,就是为了这一点。但是梅兰芳对他始终以师礼事之,数十年间,从未怠慢。老人自创红花墨叶的画法,所需红色颜料喜用德国出产的,所谓“洋红”。梅兰芳每次从南方回到北京,总是带一些来送给他。抗战期间,北方市场上很不容易买到洋红,梅兰芳先在香港,后住上海,也是常给他买些寄来。
老人常对我说:同乡中对他的画几乎都很称赞,唯独对他的字,却有不少人不十分赞赏。新中国成立后,章行严(士钊)师来到北京,老人画了一幅画送去,没曾落款,也没有题识,就是因为不知章是否喜欢他的字的缘故。实则行严师并无这种成见,这是他的多虑。行严师曾把他的近况偶向毛主席谈起,主席派人和行严师到他家里,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去晤见。这时是一九五〇年的四月间。据行严师事后对我说,到老人家时,老人正吃午饭,吃的是一碗面条,一小碟萝 卜,生活异常俭朴。他一生都是过的这样俭朴生活,凡是跟他接近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天,他见到了毛主席。丰泽园内海棠盛开,主席请他赏花,和他谈了很多的话,还一起进了晚餐。他回家后,兴奋到了极点,逢人必告,谈得津津有味。他还说:“我一辈子见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并不在少,哪有像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行严师有诗纪事,说:“北京故宫丰泽园(旧时皇城包括中南海,故章士钊有此说法),有海棠两株,各高三丈馀,庚寅三月花盛开,毛主席约余与齐白石共赏之,余即席成五绝句。”诗云: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
(原注:东汉纬学家谓春秋为汉制作,赤制字见《史晨碑》。)
微生也解当王色,粉粉朱朱壮海棠。
棠梨本色自婀娜,海外移根作一家。莫怨东风多顾藉,却教异种出檐牙。
故苑春深花满畦,重来亭馆已凄迷。残年不解胡旋舞,好下东郊入燕泥。(原注:海棠花入燕泥干,剑南句。)
七年曾住海棠溪,门外高花手自题。(原注:重庆故居,余咏海棠诗甚夥。)高意北来看未已,分甘原属旧棠梨。(原注:用荆公句。)
相望万里羽音沈,海曲羁人怨诽深。几度低回旧词句,海棠开后到如今。(原注:时余将于役香港。)
老人一生,原是从艰难困苦中经历而来,在旧时代,受尽了欺骗、剥削和压迫,直到暮年,光明来到眼前,才过着真正幸福的日子。虽说他享受幸福不过短短的几年,但是:“太平看到眼中来”,他若回忆旧作的诗句,一定可以含笑瞑目了。
(本文为张次溪写于一九六四年,摘自《白石老人自述》,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北京出版社2024年1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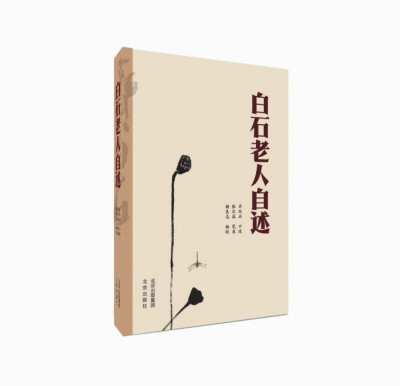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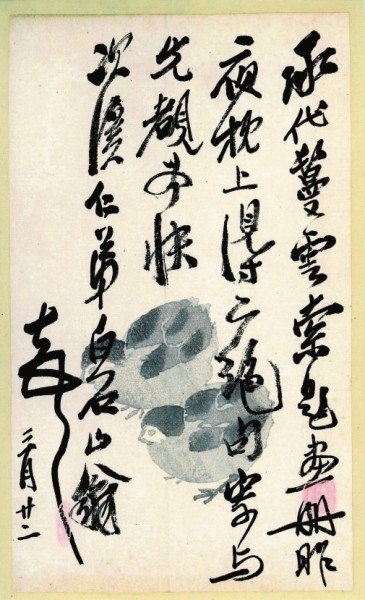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