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舒晋瑜
在获鲁迅文学奖的众多作家中,张雅文大概是唯一一位从运动员转行成为作家的。一位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的作家,以顽强的拼搏精神,自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文科课程,写出了二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早年因伤病从滑冰队退役的张雅文,走上文坛只是换了一个跑道,她身上那种运动员的拼搏劲头儿在文学界发挥到极致。有评论家说,张雅文有崇高的情怀。她觉得崇高是人类精华的根基,所有的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都受这一情怀的驱使,家国情怀和人性崇高之美,是她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新作《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也不例外。
中华读书报: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时,您已经35岁。后来您陆续出版长篇小说、传记、报告文学集《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绿川英子》《爱献给谁》等多部作品。在选择题材上您是怎样考虑的,不同体裁的创作经历有何不同?
张雅文:我开始时也写过小说,写报告文学更符合我的个性。起初我完全靠激情,像换了一个运动场,在文学上的拼命劲儿绝不亚于当运动员。这种激情持续多年。后来创作上渐渐成熟,我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每一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写《妈妈,快拉我一把》,我跑了全国十几个监狱,采访了240多名少年犯,与一个个满脸稚气的孩子面对面地交谈,常常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同被采访的孩子一起流泪。我是在一次次残酷的追问中完成这次漫长的采访,一种远远大于作家的母性责任,强烈地呼唤着我,必须完成这次艰难而痛苦的采访与书写。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没有成长好是父母的责任。
中华读书报:每一部作品对您来说都是新的挑战,但您总是无所畏惧。
张雅文:是的,的确如此。比如《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我并不想写这部书,因为不了解香港,文化底蕴不够。我爱人一再鼓励我,我才接下这项任务。报告文学,必须全面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有深度;作家的格局决定着作品的格局,作家的思想深度决定作品的思想深度。我写《为你而生——刘永坦传》遇到了创作四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难题,觉得这座山太高、太陡峭,不是我能爬上去的。我只好寻找老院士生命中的闪光点,寻找支撑他人生的支点,那就是强烈的家国情怀,所以在《为你而生——刘永坦传》中,我描摹出一个崇高的、可亲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二战期间中国留学生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德国将军营救出了一百多名将要被纳粹处死的比利时反战志士。二战后,她被比利时政府授予英雄勋章。我认为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好素材,费好大的劲儿才获得比利时领事馆的批准。当时我对爱人说,我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我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旅馆,住过没暖气,连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也受过委屈,哭过鼻子。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及华侨的帮助下,我终于敲开了钱秀玲的家门,从而挖掘出这个百年不遇的好素材。
中华读书报:谈谈《永不言败》吧,采访了那么多奥运冠军,搜集了很多宝贵的素材,您是如何取舍的?
张雅文:写这部作品,等于我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这些明星人物被写得太多了。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每一个人物的独到之处挖出来,如果我还像以往的叙事那样,我就是把自己打败了。我认为比较满意的是,开篇就把作品的格调定下来: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奖牌、奖杯的问题,而是综合国力的反映。1932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只有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参赛。1936年,中国足球队战胜了日本,直接进入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却拿不起路费,一路靠与当地球队比赛卖门票赚路费。中国所经历的奥运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发展史,这是一般的体育作品所没有关注到的。还有一点,我最担心的是,运动员的人生经历都差不多,必须挖掘出每个鲜活人物的特质。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是运动员,我想采访奥运冠军时您一定有特殊的感受,他们的成长有什么共同点吗? 有的采访对象比如教练孟庆余已经去世,您仍然通过多方面的搜集抓到了很多细节,特别感人。
张雅文:运动员比较直爽,这是他们的共性。我是他们的冰友,所以运动员说行话我也了解。尤其是我写的这几位运动员,大部分来自普通家庭,父母艰难地培养他们,孩子们都很能吃苦。孟庆余去世多年了,我只能通过采访他的爱人、他带过的运动员回忆他的生平。在孟庆余留下的铁柜子里,只有几件破旧的运动服,两双带补丁的袜子,一副待修的冰刀,一堆修冰刀的工具,还有一沓厚厚的小队员们打的欠账,一本工作日记,一本账本,记录着运动员的各种花销。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唯一一张存折,上面除了当月发放的教练工资,没有一分钱存款。可是他带领的滑冰运动员曾获得国家级金牌535枚,世界级金牌177枚,16次打破世界纪录。孟庆余的一生没有虚度,而是为他所追求的梦想、为他所酷爱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了一生。孟庆余作为冠军之父放在了本书第一篇,这个人物是值得大写特写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特别擅于捕捉细节,比如徐梦桃屡败屡战,文章中写“天道酬勤”这句话有时也会骗人;范可新的母亲没有协助女儿(骑在女儿脖子)上进行蹲腿训练,是“怕给女儿带来晦气”。您如何看待细节在作品中的作用?
张雅文:细节是作品的灵魂。我特别欣赏短道速滑冬奥冠军张会。张会从小不被人待见,她追梦的动力很简单,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崇高:为国争光,升国旗、唱国歌,她只是想:“我要好好滑冰,将来要有出息,就不用像父母那样整天起早贪黑地做豆腐了! 我要给爸妈争脸。”除了拼命训练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拼出好成绩才能有出息,才能对得起父母,才能帮家里还上那笔沉重的外债,才能不辜负教练和体工队领导的培养。她年龄太小,梦想是现实的,孩子气的。随着老师的启蒙和年龄的增长,她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人生的理想也越来越崇高了,但丝毫没有改变的是无坚不摧的毅力,以及严格自律的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拼搏劲头。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冬奥冠军韩晓鹏小时候特别淘气,爸爸为了儿子有出息,借了十几万外债买了台旧卡车跑长途,有一次父亲开车接晓鹏时有一段对话,父亲说:“咱家没钱,这辆旧卡车还是借钱买的呢。等爸爸以后挣钱了,一定买一辆小车。”晓鹏却打断了父亲,说“等我长大以后,一定给你买辆小轿车!”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是细节第一。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在行文中描写自己在看运动员参加比赛时的心情,“听到高亭宇的名字,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怦怦直跳,好像我在比赛似的,攥紧了拳头,两条腿下意识跟着使劲儿……”在您的作品中,常有“我”出现。运动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使您在采写中有怎样的优势?
张雅文:因为当过运动员,我下笔时倾注了很多的情感。我对运动员很有感情,他们做的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写的时候有特殊的带入感,不由自主地就把自己写进去了,很自然地进入到情境之中。
中华读书报:您的语言节制、简洁、质朴,却非常抓人,一看就停不下来。
张雅文:我不想故作高深。我希望自己的语言纯朴、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我习惯一再推敲,一篇文章修改二十遍不止。有时候都写完了又全部推翻,直到自己感觉满意才行。说心里话,作家一生能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我有时候看着文章甚至常常想: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中华读书报:您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写出的作品照样叫好又叫座。
张雅文:我特别羡慕受过系统教育的作家,觉得他们心里有底气。大学的氛围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不仅是学知识,年轻人在一起激情四射的氛围是难得的机会。我曾经有机会进作家班学习,也特别渴望进作家班充电,结识朋友。但为了孩子的成长只好放弃了。我觉得所有的毕业证和孩子的成长教育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此我一点儿不后悔。我去过多所大学讲课,每次讲课前,我先对同学们说:“我终生没有一张毕业证,小学的也没有。我深感遗憾。但是,社会的大课堂却为我提供了丰富知识。”在我的人生路上,多少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前不久还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念那么点书能当作家? 他们不知道,我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读大学。我把中学的、大学的文科课程全部自学了。
中华读书报:《永不言败》完成度很高,让人爱不释手。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何特殊的意义?
张雅文:这部作品完成了,我觉得对得起老伴,对得起冰友了。下一步书我会写我和我爱人的故事,不写出来,我永不瞑目。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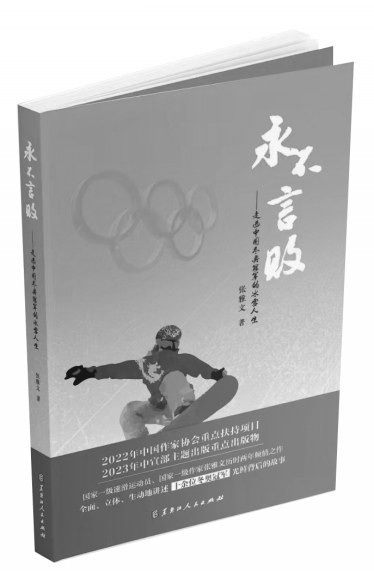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