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一
每年返乡,我都会带上一两本书,消磨在列车上长长的时光。今年我选择带上《问道江南西》,作者阿痴。惭愧的是,此前我并不熟悉这个名字,按书中介绍,阿痴本名徐芬,江西人,曾有小说见于文学期刊。书中的作者介绍并不浮夸,没有像许多期刊出来的作者介绍那样,罗列一大堆奖项和头衔,取而代之的是两句话:“人生何处不道场,灵山远求灵山消。此间红地此间曲,明得此意走四方。”
何为江南西? 在翻开这本书前,我想到了江西、江南西道,乃至广州有一个地名就叫江南西。读到此书的介绍,我有了眉目。此书有两个重要坐标,江西和上海,两个主角,一是告别艺术理想的画家叶长鹰,二是与叶长鹰成为忘年交、扎根于红土的陈报生。
叶长鹰来自上海静安区,爱画油画,他年少时看到的是“黄浦江上的各国轮船、沉默宁静的小洋楼、繁荣奢华的街市”,因为时局,他和许多知青一样,被卷入上山下乡的行列,去农场管一千来只鹌鹑,养到第五年,厂里招工,他进入钢厂,成为一名工人。书中第九节“鹌鹑”就是叶长鹰的自述。他喜欢画白色的、柔弱的、纤细的花,他从花中看到自己,“苍白,纯洁,骄傲,还残存风骨”。
书中有一大段对叶长鹰住所的描绘,看似闲笔,其实是在暗衬他的心境。在他劳作于钢厂的岁月里,他忍耐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但内心仍留了一座明堂给自己的艺术理想,他在巨变的岁月中消磨了青春,当周遭满是认命、屈从的叹息,他仍要把自己的住所装点得富有格调,在那老上海的韵味中,张扬的是一颗不屈服的心。叶长鹰骨子里的清冷和骄傲,不响而响。书中写叶长鹰梳头剃须,作者不紧不慢地写这派头,看似装腔作势,其实是一份来自于逆境者的倔强:“他用木梳沾上头油,将自己那一头茂盛浓黑的头发向后梳得油光锃亮,而后放下梳子,仰起脖子,使劲甩了甩厚重的头发,就像森林中的狮子使劲甩头,把重量感甩出来。白衬衣是他自己熨烫的,挺括坚硬,他再三扽领口,同样是体会那种重量感。头面衣服都整顿结束,他弯腰穿上大头皮鞋,套上灰蓝色工作服,走到灶披间做上班前最后的思考。”
相比之下,陈报生出生于工农家庭,他的父亲在上工时遭遇车祸,落下终生残疾,母亲带他进城,成了厂里卸车皮的女合同工。报生三岁多进入农民房大社区生活,早早分担家务活,而他从小又得到叶长鹰这样的长辈的关照,这使得他纯粹的性子不至于过早被摧折,作者通过穿扮带出了陈报生的气质:“脚上是自做的布鞋,裤子是改小的工作裤,毛衣是接了好几段散毛线的硬毛板子,他却丝毫不在意,说话做事之沉着泰然,有时候连大人们都会被比下去。”
这本书就这样娓娓道来两个人交织的人生,过去与当下交织,若你以情节流小说去看待,你会感到这部小说前三分之一的情节推进很慢,作者用了大量笔触写环境,写人物所处的局面,并不急于展开情节。若你像是欣赏画一样进入这篇小说,这种慢便不是慢,而是画师描摹精细所需要的功夫。此书有五十七节,便是五十七幅画,每一幅画,又由多个对日常生活局部的细腻描写组成。
在结构上,《问道江南西》不是单线顺叙叙事,而是双线叙事结合“穿插藏闪之法”。鲁迅在评价《海上花列传》时曾赞曰“平淡而近自然”,认为《海上花列传》“记载如实,绝少夸张”,而作者韩邦庆在结构上运用的就是“穿插藏闪之法”。所谓穿插,乃是“几组故事平行发展,穿插映带,首尾呼应,构成脉络贯通、立体交叉的整体布局”;所谓藏闪,乃是藏头露尾,文笔绵密却有留白空间。如果按照顺序时间线,此书当从清末民初的傅抱石故事开始,但此书的开头便进入到已经进入工厂劳作的叶长鹰,作者不急于交代主人公为何到此境地,而是耐心地描写工厂生活和叶长鹰的行为。在编排上,书中前十八节都在写叶长鹰与报生的故事,第十八节回到1912年除夕,概述画家傅抱石故事。第十九节又回到报生视角。由此可知,此书的主要视角就是叶长鹰和报生交替,中间穿插傅抱石等人的往事,经营出岁月感。又因傅抱石与叶长鹰等人的执念其实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命运在时间之流中产生呼应,写傅抱石是对应叶长鹰的“我执”,写叶长鹰则暗示傅抱石的另一种可能,小说因此有了回旋往复之感,所谓命运弄人,小说的气质随之开阔,也随之苍凉。
除此之外,此书在结构上也做了其他尝试。比如第九节“鹌鹑”转变为叶长鹰第一人称叙事,前十八节叶长鹰与报生的交替视角叙事。其写作结构使我想起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巧的是,书中第“二十五节”出现了一位爷叔,而我刚好在春节前看完王家卫改编版的《繁花》,游本昌饰演的爷叔令人印象深刻。而在《问道江南西》一书里,爷叔是一个出场不多、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繁花》是金宇澄对上海话和白话的改造,而《问道江南西》看似平实的白话表达,也融合了一些江西、上海等地的特色词汇。然而这本书的风格不在于鲜明的地域叙事,它没有故意堆砌方言表达的冲动,它承接的是世情小说的传统,用一种冲淡柔和的口吻,将人世间的悲喜苦乐、执着与放下娓娓道来。
当然,我对这本小说的细节处理也有一些商榷之处,尽管我喜欢这部小说的气韵,但仍提出来供读者参照。试举三例。
其一,一些解释型句子稍显多余。譬如第二节“晚班”中出现的“这是钢城独有的天空”“黏腻腻的晚班生活,这就算是第一步了”等句子,删除后,文本更紧凑,意境不会被突然打断,作者插入的解释,是对读者的不够相信;其二,小说写到傅抱石故事,中段写到了国企改制和叶长鹰跑市场。但跟作者对于书画艺术的细腻描绘相比,对于国企改制等情节的描写显得潦草;其三,人物与人物转场的衔接处有时突兀,尤其是时间跨度较大的人物。
我直言自己眼中书里面存在的缺憾,但也在细读此书后诚挚地认为,在品目繁多的新书中,这本书会是今年也许不那么有名气,但值得被看见的一部原创小说。《问道江南西》写文人,不自恋,写工人,无自上而下的审视,涉及知青故事,但并非怨恨或感伤的腔调,而是如清水过大街,有透明,有杂质,也有光亮。阿痴着力经营的是一种哀而不伤,我心自得的气度,这种对于文体气质的经营,叩住全书题眼“问道”二字。无论是生逢巨变、理想搁浅的画家,还是盲人戏班暮年的歌者,都在这红尘俗世,寻自己的道,而道看似缥缈,却可能近在眼前,于是书中写道:“人生大误,就是像他这样,以为道在繁华,而其实道在田间一盏灯下,一人忘我地唱牡丹亭,其他人忘我地听。”
或许也正因为对江西的情结,阿痴在小说中对这片土地有细致的描绘。比如她写冬天的江西:“冬天,冻到极致,反倒令这座城市难得地,拥有了一种儒雅安宁的气质,这在平常,喧嚣和污染之下,是见不到的。这块江南以西的地块,在寒气之下,似回到一千多年以前,宋时,此地是无数文人墨客的家乡。江西诗派,曾经一时风头无两。滕王阁大宴宾客时,王孙贵族举杯畅饮。南昌郊区的庙里,朱耷画了一只独立孤石的臭脾气鸟儿,翻了一只大白眼。”
阿痴写报生和叶长鹰,其实也是创作者的一种自我追溯。正如阿痴在谈到他们时指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既有报生的一面,也有叶长鹰的一面,就像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其实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而他们所追求的道,在人心,在土地,在寻找的路上,看似路途遥遥,其实,“道在田间一盏灯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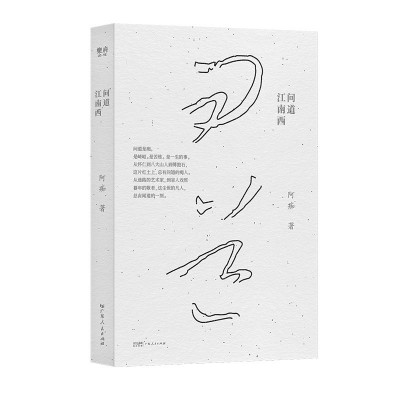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