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郑板桥于其所画的《风竹图》中题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时任山东潍县县令的诗人于衙斋高卧,听窗外风吹竹动,萧萧作响,于是联想到民间疾苦,不能释怀。此诗写一个时刻不敢忘记自身责任的官员心态,于古人可谓之循吏精神,于今时可谓之专业精神。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道出这一精神的具体内涵。读罢查屏球教授新近由凤凰出版社梓行的《三余书屋话唐录》,深觉其中所展示的一个唐代文学研究者的专业精神与古人有相通之处。此书分“堂下蹑尘”“学林撷英”“海外揽胜”“丛札漫忆”四辑,收录作者的书评、札记、随笔凡二十六篇。书中一部分文章缘于师友之谊而作学术评论,一部分文章因日常读书有得而写学习感受,部分随笔、札记则是日常闻见之间的有感而发,其共同特点是皆与查教授自己研究的唐代文学相关。以“话唐录”作为书名,可谓名副其实,也正见其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学术研究的专业精神。
查教授早年亲炙于刘学锴、郁贤皓、章培恒、王水照诸先生,诸师既引领其进入学术研究之门,他们的学问和风范也为查教授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堂下蹑尘”中收录的六篇文章即为查教授再次向乃师学习的心得体会。查教授在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十卷本)出版座谈会上曾言:“听师一年课,定我一生业”,并回忆了自己早年在安徽师范大学跟随刘先生学习唐诗的所见所感,指出了刘先生对自己学术兴趣培养和后来职业选择的重大影响。正因为对老师的学术研究经历和日常教学方法非常熟悉,其对刘先生以四年时间纯手工书写撰成的《唐诗选注评鉴》的理解也较一般人更为深切。如其对该书艺术性、可读性、完整性的选诗标准的把握,对该书以文本为中心所构建的诗家与诗家交流、读者与作者交流、读者与读者交流的鉴赏模式的总结,以及对刘先生解诗时注重作品意脉梳理所展示的传统串讲式鉴赏方法的独特意义之理解,皆融入了早年问学时的记忆和感受,非一般书评泛泛而谈者可比。与对刘先生著作的评论类似,查教授早年拜在郁贤皓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对乃师近半个世纪专研太白的甘苦深有体会,因此更能理解郁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博览精取、解难为易、原创出新背后所付出的辛劳。如郁先生对李诗训诂笺解之准确,实是缘于其担任《辞海·词语分册》主编打下的专业素养;该书体例上之所以迥出其他同类著作,乃是缘于郁先生早年选注《李白选集》的成功经验;郁先生对李白交游及诗歌系年发覆甚多,乃是因为其早年为解决此类问题曾专门撰写《唐刺史考》《唐九卿考》《李白交游考》等著作,对相关问题早已了然于心。查教授在品评时所提供的诸如此类的信息,使我们对郁先生穷一生之力、聚一世之学、注一家之书的壮举和执着精神,更增添了一份理解之同情与感佩。
朱光潜先生曾云:“欣赏一部书,如果那部书有文艺的价值,也应该是在心里再造一部书。一篇好的书评也理应是这种‘再造’的结果。”(《谈书评》)就查教授对刘学锴、郁贤皓诸位先生著作的评论来看,我们从这些书评文字中既能发现查教授的的学术起点,也可窥见其从老师那里继承的学术理念,如其对诸师解诗注重意脉的推重,对诸师研究过程中注重读者体验与学者考辨结合之方法的深切理解,在查教授自己的著作《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等书中也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查教授在诸师“堂下蹑尘”之所得,对他自己的学术研究而言,无疑也具有“再造”的功能。
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得益于地下新出墓志与域外汉籍回流所提供的新材料,显示出新的格局与气象。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查教授治学也有明确的“预流”意识,不仅自己进行相关的研究,对最新的学术进展也颇为关注。“学林撷英”与“海外揽胜”中收录的十三篇书评、札记即与此相关。就“学林撷英”中的诸文而言,查教授的品评除了一般性的评论外,往往能结合诸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些饶有兴趣的话题。如胡可先教授指出石刻挽歌、长沙窑唐诗在立意和结构上具有诸多相似性,查教授进而联想到苏轼《江城子》“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等向来被视为独创性的经典语言与于鹄《古挽歌》中“孤坟月明里”之间可能存在前后因袭关系,这种语言上的模式化构建了古典语库的素材并影响到后人的创作。又其在评陈翀《日宋汉籍交流史诸相》一文中就作者指出的李白《静夜思》、王之涣《登鹳雀楼》等诗句在《艺文类聚》收录的前代诗文中都能找到出处的现象,进而指出这些情景、思维、用词具有类似特点的语言在后人看来极具原创性,在当时则可能是习语。之所以有这些独特的发现,笔者以为当与查教授自己的研究兴趣相关,如其早年发表的《“赵倚楼”“一笛风”与禅宗语言——由杜牧等人对语言艺术的追求看经典语汇的形成》即关注此类问题。在他人著作中发现自己也感兴趣的话题,“德不孤,必有邻”的感受,应是读书人最大的乐趣。
就“海外揽胜”中的诸文而言,由于查教授长期在日、韩等国任教,本身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韩藏唐诗选本研究”首席专家,其关注域外汉学的研究现状是自然之事。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主要国家,文化上的互动十分频繁,但近代以来,三者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就学术研究而言,同样是研究唐代文学,日韩学术话语作为邻人的眼光,多能以独特的视角开拓新的学术空间,或许有“旁观者清”的价值。作者带着这样的心理审视域外汉学,其实也蕴含着对于中国学术国际化问题的思考。当然,作者关注的也并非纯是学术性问题。如其注意到与日本京都醍醐寺相关联的空海大师、醍醐天皇、丰臣秀吉三人,不仅代表了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展示了古代日本与唐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当代作家平野启一郎《日蚀》《一月物语》两部小说引用李贺《苏小小墓》一诗,其中奇幻炫迷的特色显然与李贺诗歌有某种共通性。两事分别从古今角度,于细微处阐明了东亚文化共同体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文化因缘。至于其在《甲午日本汉诗选录》的前言与后记中对该书选编过程和目的说明,则让人感到“学术无国界,学者有国家”这句话绝非虚言。近代以来,日本侵华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对文化母国何以欲亡之而后快? 彼邦人的心态究竟如何? 作者试图在数量众多的甲午日本汉诗中寻找答案。当然,作者在面对这些“恶之花”时的心情是沉痛的:“我们曾天真地想象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战争诗中,或许会有表现厌战或反战的作品,然而,几经搜寻,无论是在总集中,还是在诗人别集中,竟然未发现一篇,大感意外”,“我们在清理这部分文献时,既多有国殇之痛与被辱之愤,也时生太息扼腕、伤心顿足之叹”。笔者在阅读这些汉诗时,深有同感。
与前述三辑多为严肃的学术性文章不同,第四辑“丛札漫忆”则要轻松活泼很多,但依然不离专业范畴,应属于典型的学者散文。作者或以散文笔调论李白之大唐梦,或从民俗角度赏张夫人之《拜新月》,或满怀感情地追忆师长。其中所记祖保泉、王运熙、任铭善诸先生的掌故,可一窥前辈学者为人与为学之风范,尤有趣味。
据查教授在书序中介绍,书名中的“三余书屋”乃其家旧时书斋之号,取自其故乡的地名三余圩,同时也与古人所谓冬、夜、阴雨之“三余”苦读精神相关。查教授沿用这一书斋名,既示不忘乡梓、不违庭训,同时也有自勉之意。作者研治唐代文学三十余年,自言“心无旁骛,唯以此为业”,可谓念兹在兹,与唐诗唐文须臾不离,颇类韩愈《答李翊书》中所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状态。今观全书,其中最早的文字写于1995年,最迟的则写于2022年,一字一句关唐声。“三余”之意,足以当之。
(作者系江苏海洋大学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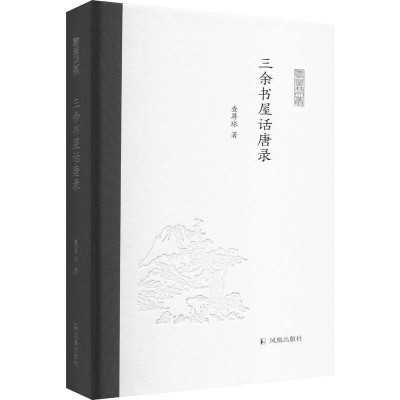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