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罗曼·罗兰的《母与子》,罗大冈的中译本,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名义于1990年8月出版的。它被列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皇皇三大卷,一百二十余万字,属“长河小说”。遂甫一出版便买下,但怯于卷帙浩大,翻翻梗概就“冰藏”了,留给了时间与机缘。
退休之后,有海量时间,便想读大书。选来选去,终选到《母与子》,因为它描摹“灵魂”,探讨生命的意义。这与退休后的心境暗合:退休前看重声色,追逐名利;退出职场,生命有了自然的状态,“回归”本质,想追究一下,人的一生究竟是为什么而活。
书搁置得太久了,凡尘蒙面,书页暗脆,有驳杂的黄,一如秋树红叶。赏红叶的心境,是从容而珍惜的,便一行行、一字字地阅读,不想放过每一处齿裂和每一寸筋脉。这也符合生命伦理:人生既然已没有了多少可以敷衍浪费的时光,便要看重每一寸光阴、过好每一个日子;这一如牙齿松动,不能饕餮,正好慢慢咀嚼,吃下一口是一口。
如此一来,《母与子》就成了我的阅读史中,读得最精细的一种。窗外的阳光照在案头,暗淡下去之后,便继之以灯光,书页上总是亮的,便每一页、每个字都有意义地闪光。整部书,从头到尾,都是清晰的逻辑、向上的精神、不屈的意志,没有一丝暧昧、没有一丝阴郁、没有一丝哀怨;事物都是按节律生长而没有一丝扭曲和变异,人物都是自主地生活而无一丝攀附和变态,便处处打动人心。
主人公安乃德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衣食无忧,得以正常生长,身体便出落得异常健壮,前额宽阔,胸脯丰厚,虽不漂亮,但也属端庄,一坐一立,都落落大方;她又饱读典籍,有精神的涵养,早就有了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的能力。于是,安乃德便有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且非常正直、非常自我,自我意识的强烈,甚至趋于固执,很难被别人打动,根本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牵制。年轻时,由于一时冲动,与未婚夫洛瑞发生了关系,怀了身孕。她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但却拒绝与洛瑞完婚。因为她发现,洛瑞很自私,而且没有健全的两性伦理,他认为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要成为男子的附属品,不必保持良心的立场和人格的尊严,更遑论自主的意志和精神的独立。她对洛瑞说:“身体你可以拿去,但灵魂给我留下。”
这一声石破天惊的独立宣言,宣告她必然要走上异常艰辛的生活道路——她一个人生产、哺育、抚养,全不顾社会舆论的话语侵犯。这期间,不良经纪人的贪婪操作,使她彻底破产,靠给别人打工、做私活,做自食其力的跋涉。由于灵魂上的自由,生计上的艰难,并没有摧毁她“生”的意志,反而觉得自己特别有力量。她每天都乐呵呵的,用玩味的心态,体验底层人的生存境况。这样一来,她发现,她比其他女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因为她有知识、会思考,能迅速适应环境,并与雇主做有效沟通,遂被这些女人嫉恨。这让她警惕,觉得自己虽然悲苦,但那是自己自主的选择,而别的女人的悲苦,是不得不的被迫承受,本质是不一样的,于是,便心生大悲悯,主动把机会出让给她们。这就让那些女工大为感动,觉得她“轻贱而品重、位卑但德高”,便把她视为精神上的教母。
安乃德的这种精神上的自主(自治)也同样作用于她与自己的儿子玛克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西尔薇的关系。在她的带动下,西尔薇有了卑微而向上的勇气,玛克也追求正义而走上了反战的道路。他们一家人,整体地具有了恪守良知、公平、正义的生命气象,以精神上的高度契合,结伴而行,活出了人的高贵与尊严,以至于始终都不被命运所左右,成了打不垮的人。
当爱子玛克被好战的暴徒刺杀,安乃德在悲伤之余,毅然决然地拾起从玛克手里跌落的反战大旗,踏着儿子的血迹,勇敢地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斗行列。最令人动情的是,儿子在他怀里合上眼的那一刻,她一下子就领悟了人间所有的悲欢苦乐,不禁发出了一声充满创痛而又充满柔情的低语:“小娃娃,世界这个小娃娃,你在我身上不是很好的吗? 为什么你要从我身上出来呢?”这一刻,她不仅是儿子的母亲,而且把自己当成了所有人的母亲,当成了世界的母亲!
因为有了人类的大爱,她便有了为普天下被奴役、被压迫的人活下去的博大情怀,一切苦难与不幸,在她看来,都是生命的养料,她在大地上升华了。
读罗曼·罗兰的这部《母与子》,我一刻都没有平静过,始终在心潮起伏、灵魂激荡的状态之中。这是一部生命之书、灵魂之书。它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精神的符号,每一个章节,都是象征的意象——他呼吁人们从肉体上解放,在精神上飞升。罗曼·罗兰从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就想对这个“但愿姿态美,不问灵魂好”的时代,予以强烈的反驳,他要让信仰和灵魂登场。他所据的理念是:道德行为准则只有一条,那就是认识自己,忠于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如果想帮助别人,那么自己首先要拥有自我的意志,被欲望左右的爱、受人控制的爱,是毫无力量、甚至是毫无价值的。
落实到安乃德这个人物身上,身体上的痛苦,她处处都可以忍受,心灵上的折磨,人格上的挤压,她须臾不可接受。面对生活(身体)的磨难,她乐观豁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痛苦从来不妨碍我欢笑,欢笑也不妨碍我痛苦”。但是对心灵的冒犯,她立刻就报以激烈的反抗。她信奉歌德的一句话:“我的心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某一个角落有一座封闭的城堡,任何人都无权进入。”这座“封闭的城堡”是什么? 在安乃德这里,就是道德的纯粹、心地的纯净、精神的纯真。这些,是她信仰的标志、自由的保障、灵魂的命符。
《母与子》,绝对是一部灵魂的写意,即便是完成于一百年前,放在当下,也有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生存的自由从来不取决于肉体(物质)上的种种满足,而是取决于灵魂的硬度。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奴在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奴在心”,因为人格和精神不能自立的人,永远消极在怨天尤人之中,丧失了向上生长、自我救赎、生命圆满的能力。
感谢罗曼·罗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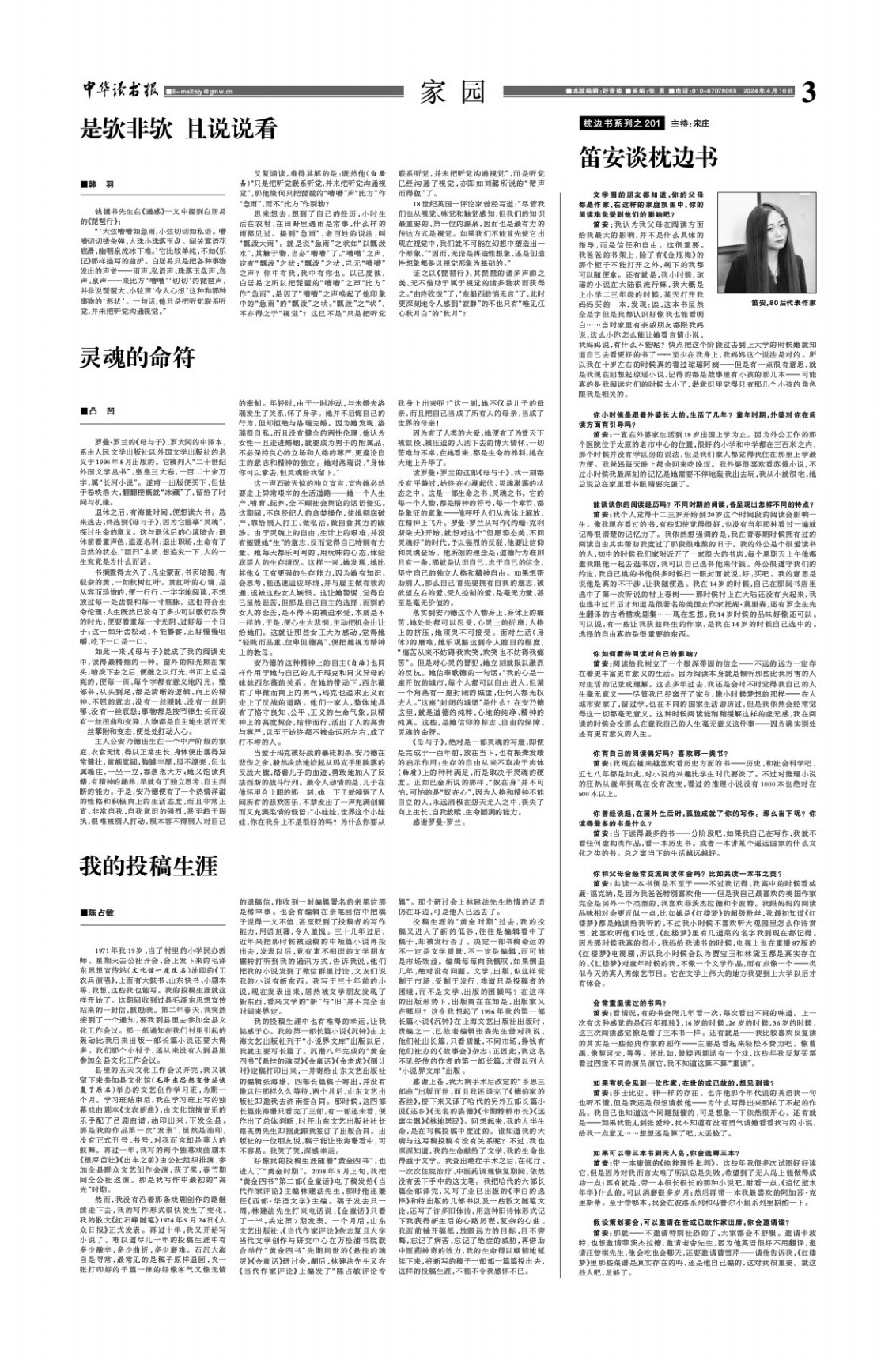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