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江南细雨蒙蒙。借《郴州通典》发布式和研讨会召开,我应邀来到湖南最南边的郴州市。“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会后的的考察、参观,仿佛沉浸在远古帝舜孝道文化的氛围里。我不相信这是舜所作的诗歌,认为应是后人为了记念这位先帝圣德的寄托之词。在以九疑山为中心的临武、宁远一带,帝舜孝道故事以及南巡而崩广泛流传,有许多文化遗迹,如九疑山有帝舜祠,临武县有帝舜山,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
令我更感兴趣是,2300前的伟大诗人屈原放逐的行迹以及和屈原相关的文化遗存。不用怀疑,屈原足迹到过郴州的临武县,到过九疑山,《离骚》不是明确写了么?“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是帝舜的名。这分明告诉了我们,他曾登上了九疑山,瞻仰过舜祠。那时的九疑山,在楚国最南端的边陲,属于临武县管辖。屈原到了九疑山,等于说到了临武县。
但是,学者对此深表怀疑,理由是屈原可以陈诉的神庙,在楚国境内多得不可胜举,怎么可能大老远地来到九疑山向帝舜陈诉? 以为《离骚》陈词一段,视如“假托”之词,属于艺术虚构,未必实有其事。在当今《楚辞》研究的群体中,我算是一个守旧派。所以,在以往的著述中,我也这样理解。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2022年9月底,我不幸肠梗阻。10月中旬,旋即在杭州手术治疗,总算捡回了一条老命。经过两个多月调理,渐见恢复。当时,我正撰写一部题名“屈宋辞赋笺注”的著作,对自己历年《楚辞》研究,做个总结。因这场大病,中断了三个多月。12月初,开始重操旧业,继续未了之事。正好笺注到《涉江》开头“余幼好此奇服兮”一段。谁知不测风云又降临我身,被染上了“新冠”,无奈又被迫躺了下来。旧疾未愈,新病继起,何其不幸! 染病的第三天,高烧已至40.3度,那晚彻夜未眠,昏昏沉沉,喉咙灼痛,异常难受。但是,脑子依然活跃,思绪在《涉江》开头的那段文字中间辗转。
《涉江》承接《哀郢》而来。《哀郢》记叙了从郢都的“夏首”至“夏浦”(即沔阳)的路程,《涉江》继叙自“鄂渚”(今武昌)至“溆浦”经历。而开头这一段,令人费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崑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云里雾里,实在寻找不到和屈子流放事迹的系联点。闻一多先生苦苦探索,定为“错简”,说这段文字本是《惜诵》一篇的“乱辞”,被窜乱到《涉江》开头。闻先生的揣测,没有文献支撑,不甚靠谱。学者至此多绕开不谈。屈原在此到底想述说什么? 忽然,冥冥之中似乎有人提醒了我:峨冠带剑,“驾青虬兮骖白螭”,这样的奇妆异服,非现实中的屈原。因为现实中屈原,《渔父篇》已有描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完全是一个被迫害的政治囚犯的模样。这个形象和《九歌·东皇太一》的那位“祭司”稍加比对,“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何其相似乃尔! 屈原这身“奇服”,乃是祭祀神灵之服,是他想象中的妆束。那么,他到底想要祭祀何方神灵?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一句,道出了沉藏二千三百多年的秘密:原来涉江的目的,要去祭祀重华。重华即帝舜,传说南巡至九疑山而崩,葬于九疑山,山下有帝舜的祠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过《舆地图》,以山形线条及鱼鳞状纹画九疑山的地貌,山南画着像石柱样子的柱子九根,大概指九疑山的九峰。柱石下有庙,右边题写了“帝舜”二字,说明汉初舜庙之所在位置。《水经注·湘水》谓九疑之山,“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所画九柱石,即舜庙前九碑。根据地图所载,在战国之世,南楚风靡九疑一带盛行祀舜之俗,帝舜神祠肯定不止一处。远离九疑山一百多里的临武县有“帝舜山”,山顶之上也有帝舜祠。此时屈原本已失去自由,不是说他想去九疑祭帝舜就能去九疑,去九疑乃是楚国朝廷的决定,是其放逐的终极之地。于是我不禁“坎其击缶”,叹为观止,思路豁然开朗,几十年没想明白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屈原以这种特有的祭祀帝舜方式告示后世,他的流放终极之地即在九疑山。高超的文学家往往独运匠心,文字里边隐藏着意想不及的讯息,其魅力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此。顿时,我真是兴奋极了,全身大汗淋漓,畅快无比! 感觉已在发汗,轻松了许多。生怕遗忘,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刚才“解秘”的过程。
自那以后,我一直就存有考察临武、九疑山的奢望,希望在有生之年亲临屈原流放之地,感受一番屈原作品中所描写神奇山川及气候多变形态。衷心感谢《郴州通典》总纂雷晓达先生,专门为这次考察活动作精心设置、周密组织,使得我这个年届八十又一的老翁,终于圆了朝思暮想的考察之梦。
此行我们去了“天下第十八福地”的苏仙山。登上山顶,在囚禁张学良的斗室里徘徊许久。又到半山腰的苏仙祷雨处及米襄阳为秦观《踏莎行》书写的碑刻,得知这里也是秦少游贬官地。那首脍炙人口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传颂至今,成为郴州一地的文化标记。贬官对于秦观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文学创作则是大幸。苏东坡赞叹不已:“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意思是说,秦观这首词真是绝了,纵然万人万作也赎不回来! 设若秦观不贬官至郴州,绝然写不出《踏莎行》这样的绝妙好词,也留不下米芾这龙腾凤飞的书体。屈原何尝不是如此? 徜若没有放逐临阳的经历,何来千古不朽的《离骚》?“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那种朦朦胧胧的流动气态,似烟非烟,似雾非雾,似雨非雨,倏忽无定,秦观把郴州的地貌气候描写到了极致。这种奇特的气象变化,屈原作品中也有描述,“观炎蒸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回风》)过去,不理解“烟液”为何物,这次总算在郴州感受到了,也深切领悟到“烟液”二字,是那样神奇和微妙。
临武的历史比郴州悠久,即是《鄂君启节·舟节》的。这个字从邑、从㐭。㐭,即古代的廪字,据许慎《说文解字》,本义是专门贮藏军粮和赈灾救济谷物的仓库。有人将它释读为“鄙”,是不正确的,因为㐭、啚的古字完全不同。后来逐渐发展为以仓廪为中心的县城。郴的古城应在临武。临、林、廪古字通用。根据马王堆汉墓的《舆地图》标示的名称,临是水名。城治在临水的北面,故又称临阳、阳、林阳。临、林、㐭和“陵”古字也相通,屈原《哀郢》说:“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这个“陵阳”,原来就是现在的临武啊,是他流放的终极之地。屈原到了九疑山,意味着他来到了临武。登上旧县治之西的舜峰山,山上有祭祀虞舜的祠庙,祭舜是当地的传统风俗,起于何时,已不可考。庙门紧闭,环境荒芜,有待开发。山不甚高,岩崖陡峭,古木参天,遮蔽天日。我竚立远眺,四周群山峻高,几与天齐,“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儵忽而扪天。”其地理形貌特征,和屈原作品中所描述基本吻合。于是暗自遐想:屈原到了临武,“就重华而陈词”,会不会就在眼前的这座简陋的古庙? 多么希望这里能留下一星半点的“雪泥鸿爪”! 遗憾的是,没有寻找到一点踪迹。这不奇怪,屈原是以重罪流放此地,比起后来的贬官惨多了。贬官大小总算还有个官职的名份,而屈原是一无所有,纯属是戴罪放流的囚犯,在当时,谁会把他当一回事呢!
《涉江》所述,屈原到溆浦的时候,已经是“霰雪纷其无垠”寒冬季节,于是没有继续前行。大约在第二年,即楚顷襄王五年的春天,他到了临阳。《离骚》说:“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王逸注:“鹈鴂,常以春分日鸣也。言我恐鹈鴂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春分日,是暮春三月。屈原到九疑陈词的时间,即在作《涉江》的明年春三月。这些作品在时间上可以相接的。所以,我确认《离骚》作于陈词重华之后,是在放逐至临武以后创作的。《离骚》又说“老冉冉其将至兮”,古代年五十方可称老。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庚寅,至楚顷襄王五年(元前295年),年四十八岁,“其将”二字,说明作《离骚》,不及年五十,与此完全符合。《离骚》是屈原代表作,全副精神,十分笔力,尽萃于此。过去我也曾经说过作于怀王时。那时没有放逐的经历,仓卒作自传,未免嫌早。惟于此时此地,屈子放逐至陵阳,绰有闲暇,可以从容摅泻其胸中怀抱,总结其一生行迹。《离骚》作于临阳之说,应该没有问题。屈原在临阳又创作了《悲回风》《卜居》《橘颂》等。自此以后,屈原一直被遗弃在临阳,无人过问,令他非常绝望。百无聊赖之际,却给了他一个整理、编纂生平作品的机会。屈原辞赋的修改、定稿、结集,应都是在放逐临阳后完成。惟在此时,屈原有充足余暇与精力。这一切,虽文献均无记载,依据其生平经历所作推测,是合乎情理的。
在临武百余里外的九疑山,我们荣幸地参与了当地民间的祀典虞舜的活动。在司仪引导下,众人整顿衣裳,肃立在享殿前,进献三炷香,行三鞠躬礼。敬捧酒杯,举过头项,行酹祭礼。虔诚跪于帝舜陵前,行三稽首拜祭礼。此时,我默默地念着《离骚》“陈词”一段的诗句,心潮激荡。遥想当年,被押送至临阳的屈原,满腹寃屈,“跪布衽以陈词兮”,在帝舜神尸之前,一字一泪哭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陈词结束,帝舜也无可柰何,似乎告诉他,“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怪他时运不济,没有遇上君明臣贤的际遇之日。屈原自认倒霉,“哀朕时之不当”、“霑余襟之浪浪”,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到天上去追求帝高阳了,结果也是一场空忙。反顾四周,群山环列如簇。那时候环九疑一带,人烟稀少,鸟兽成群,“闻省想之不可得”,寂寞、孤独、痛苦,陪伴其终生。在此间,我询问当地一位民间学者,屈原来过九疑山没有?他直率地告诉我,完全有可能,说湖南著名学者林河先生作过大量调查、考证,作出的结论是:屈原到过九疑山。林河,真名叫李鸣高,侗族人,是我早年朋友啊,后来失去联系,据说本世纪初已去世。真没想到,林河早已在探究这个千古之谜,像屈原一样,孤立无援,没有引起学界重视。我步其后尘,希望能完成林河先生身前的未竟之业,于是不禁大声疾呼:若屈子地下有知,敬请“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开启了与北方《诗经》完全不同的、极具南方浪漫特色的文学传统。屈原的不朽思想、爱国精神、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的“国魂”! 当时即口占三绝,表达考察感受。诗曰:
千里驱车到九疑,欲寻逐客登舜祠。一腔孤愤凌霄汉,凝作离骚千古诗。放逐临阳路迢迢,陈词帝舜赋离骚。行人到此迟疑处,隐蔼烟云山峻高。离骚原本舜之歌,凤鸟啾啾箫笛罗。藉尸还魂新体式,至今沿溯泛清波。
短暂的考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返程中,我频频回顾九疑山的迷人景色,屈子行吟的图像又在心中腾起,预将在郴州大地不期而遇,使郴州大地的帝舜文化传统平添几分屈原放逐文化的斑斓色彩。我将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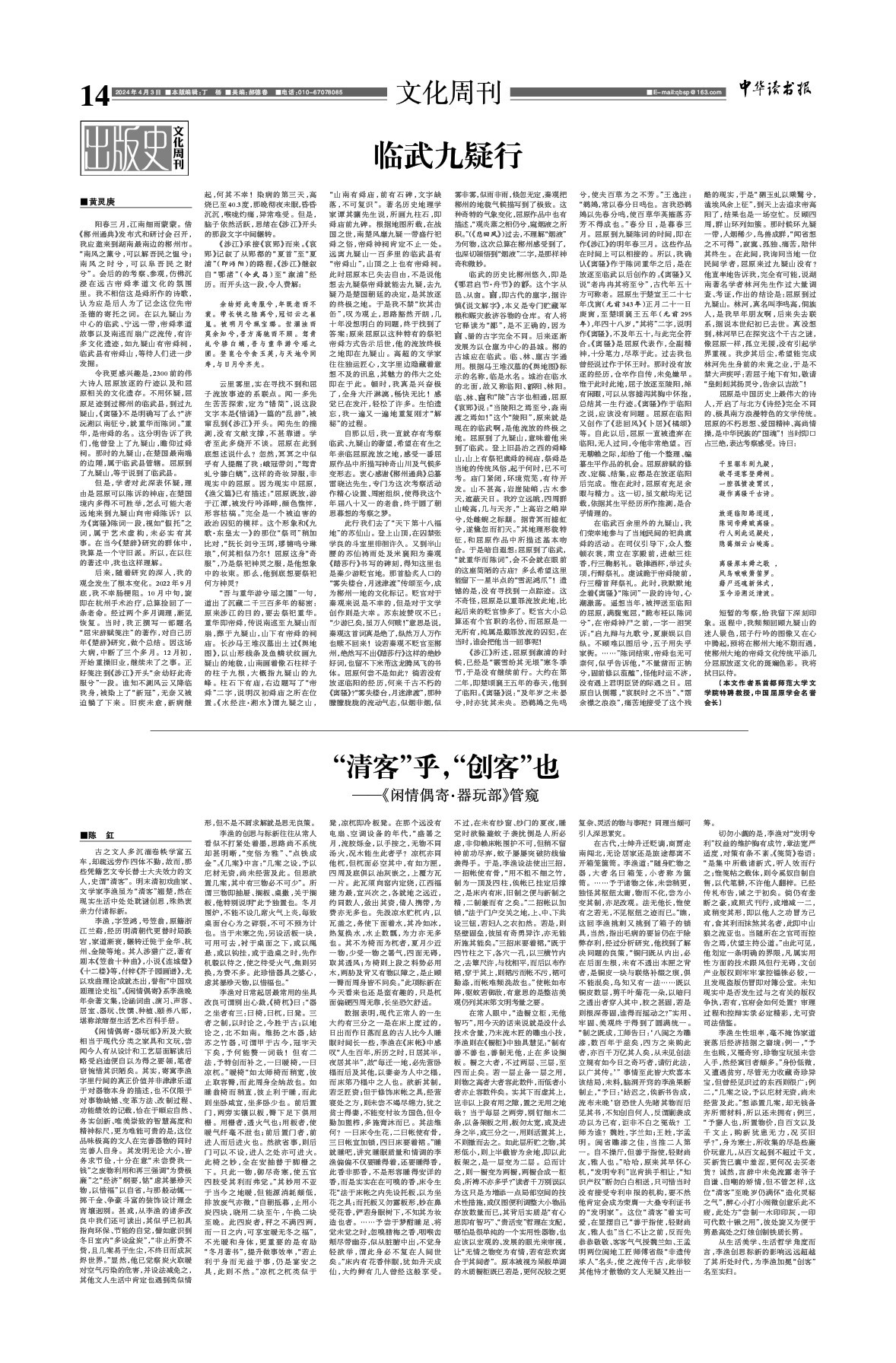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