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现代新诗生成不过百年,却是对三千年中国诗歌传统的一次革故鼎新。但她在草创初期的情形是怎样的? 进行过哪些探索? 产生过怎样的争论? 抑或什么样的新诗才算好诗? 新诗到底该怎样写?“朱自清别集”最新两种《新诗杂话》与《毁灭》就厘清上述问题贡献了鲜活具体的资料,为人们谛听现代新诗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脉动,提供了清晰的心跳声。
“朱自清别集”计划出版24种(光明日报出版社),由著名作家陈武主编。陈武既是当代实力派作家,又是朱自清先生同乡,还是俞平伯、沈从文、朱自清等现代名宿研究专家。《新诗杂话》与《毁灭》彼此构成了互证关系,表征朱自清先生作为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和学者,不仅是现代新诗发轫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同时还是富有力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朱自清先生曾于1944年自编《新诗杂话》,收入文章十五篇。陈武根据《论雅俗共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版)、《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版)、《语文零拾》《诗言志辨》(岳麓书社2011版)中部分篇目,新辑朱自清先生8篇谈论新诗的文章,同时将原序与附录译文一并收入。现版《新诗杂话》中的25篇文章,起讫时间约为1922年至1944年;内容为现代新诗生发缘起、语言形式、艺术手法、题材内容等问题的“杂话”。这些文章中呈现的见解与理念,以及他编选“新文学大系·诗卷”时设定的尺度与标准,可以视为朱自清先生推动现代新诗演进的建设性实绩;而书中文章折射的诗歌现象与思潮,则可视为现代新诗发轫史实的同步还原。
关于现代新诗的生发缘起,朱自清先生在《真诗》一文中直指“新文学运动实在是受国外的影响”,是“借镜于国外”。在《论中国诗的出路》中,他更是历数现代新诗草创期的外来影响因素,包括佛音翻译、日本俳句、泰戈尔的《新月集》以及欧化白话等。当然字里行间中朱自清先生也流露出担忧:“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同时表示:“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是顺的。”这种担忧其见也高,其诚可鉴。
但是,现代新诗在草创期何以既不师法传统诗词、又不借镜民间童歌(童谣、山歌、俗曲)? 朱自清先生在《诗的形式》中作了辨析:“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直到现在,新诗的提倡(也)从破坏旧诗词的形式下手。”鉴于“新文化运动”中“去文言”思潮的影响,前有胡适白话诗《尝试集》试水,后有郭沫若《女神》狂飙突进式的推高,朱自清先生认为新诗若要借鉴传统,“胡适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论中国诗的出路》);至于“新诗不取法于歌谣,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外的影响”。作为现代新诗同侪,朱自清先生调侃道:“一翻《尝试集》就看得出,他(胡适)虽然一时兴到地介绍歌谣,提倡‘新诗’,可是并不认真地创作歌谣体的新诗。”因此结果便是,“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朗读与诗》)。
说到现代新诗的语言,便进入了形式技法范畴。朱自清先生在《新诗的进步》中说:“十年新诗,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是在进步的;也许是。”这里的“也许是”,显现出他对新诗肯定的有限性或不确定性。在《关于“新诗歌”的问题》一文中,朱自清先生对“过分欧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顺口的长句不满意”,原因是“不扼要,啰唆”;盛行的短诗,则是新瓶装旧酒,且太滥、平庸敷泛,不痛不痒,无余味可咀嚼(《短诗与长诗》),甚至批评道:“如今区分诗与散文的形式,便只剩下分行了。”(《论中国诗的出路》)他还披露自己曾记下这样一首“新诗”:“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 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新诗》)足见现代新诗草创期的争议之大。
那么,什么样的新诗才是好诗?在朱自清先生看来,《女神》《志摩的诗》都是“有光彩的作品”(《新诗》)。他在1927年生成的这一见地,现已达成文学史界共识。朱自清先生还举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姚蓬子、冯乃超、戴望舒、卞之琳和冯至等人的作品为例,扣住文字机理条分缕析,认为他们的诗作均有法度可观。特别是他在具体分析林徽音《别丢掉》和邵洵美《距离的组织》等作品时,依形象脉络作深入浅出解析,更是堪称诗歌鉴赏范本(《解诗》)。因此,1935年学界与诗界公推他主编《新文学大系·诗卷》,完全是众望所归。尤为令人感佩的是,在《爱国诗》《闻一多先生与新诗》和《北平诗》等文章中,他对闻一多《一个观念》《一句话》、郭沫若《炉中煤》和马君玠的《北望集》多有赞誉,不仅显现了他所肯定的内容向度,表达了坚定的爱国情怀,还预示着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必然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的崇高气节。
说到底,现代新诗到底应该怎样写?《新诗杂话》中的诸多文章都颇有创见。在《唱新诗等等》中,朱自清先生认为“新诗无乐曲、歌谣基础,但至少总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这是在对新诗语言韵律问题作提级探讨,并肯定了闻一多“新韵律”诗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努力。在《诗与感觉》一文中,他提出“想象的力效”概念,认为想象的素材是感觉,要到大自然、人的悲剧和爱里找诗的感觉;写诗是感觉-组合-想象的形象思维过程。在《诗韵》一文中,他结合具体作品探讨了韵律与复沓手法之间的机理关系;在《新诗》一文中,他认为“新诗无味,在于诗人的生活无味”,因此要拓展生活;进而提出“新诗与大众的关系”,认为“诗走向人民是道路”(《今天的诗》),同时也要注意不因“侧重‘群众的心’却忽略了‘个人的心’”,认为林徽音的“《再别怕了》也许是一面很好的借镜”(《诗的趋势》)。这些可贵的理念,对于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都是极具建设性的创见。
《毁灭》收入“新诗”“歌词”和附录“译诗”共74首,不仅系统反映了朱自清先生的新诗创作与译诗成就,而且呼应《新诗杂话》中的一系列观点,成为他诗学理念的有力实证。
长诗《毁灭》是诗集中的重量级作品。陈武认为,这首创作于1922年的长诗“在朱自清先生的生命史与创作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也是为新诗贡献的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的确,作为当时影响广泛的长诗作品,朱自清先生在诗中将自己对过去纠缠与挣扎后的决绝、对当下生活的务实及对未来的追求,用复沓、漫衍和铺陈的手法,在中心句引导下书写得长波逐浪,从而使诗人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责任的精神探索,得到富有表现力的映射;那也正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
朱自清先生不仅长诗出色,短诗也灵动精巧,令人爱煞。诗集《毁灭》收入的第一首诗《睡吧,小小的人》写于1919年初,那正是中国现代新诗草创初期。朱自清先生使用“复沓”手法,以中心句“睡吧,小小的人”引领全诗,将母爱抒写得涟漪荡漾。第二首《小鸟》写于1919年底,以拟人手法表现生命的欢乐,末句极为鲜活跳脱:“我们活着便该跳该叫/生命的欢乐/谁也不会从我们手里夺掉。”同期所写的《光明》一诗更是当时名篇,令人极为称诵:“光明?/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传达出积极进取的理念。他1920年初所写的《煤》甚至早于郭沫若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炉中煤》,表达了对煤的赤热奉献与感召力的歌颂,同时揶揄了社会的看客心理。而写于1923年春的《细雨》,用灵动的比喻将春雨写得真切活泼、令人过目难忘:“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如果将朱自清先生的长诗《毁灭》与短诗《细雨》对照参看,便可以透彻理解并且完全认同他“短诗以隽永胜,长诗以宛曲尽致胜”(《新诗杂话·短诗与长诗》)的现代新诗理念。
无论《新诗杂话》还是诗集《毁灭》,均可以见出朱自清先生现代文学大师的风范。他的文章语言清新活泼、朴素隽永;论诗说理更是精准恺切、鞭辟入里。如果说《新诗杂话》是新诗鉴赏与写作的入门指南,那么《毁灭》则堪称新诗创作的出色范本。要而言之,“朱自清别集”中的这两本新书,不仅是他推助现代新诗正向演进的建设性产物,让我们具体触摸到现代新诗发展的脉搏,听到现代文学史中新诗的心跳声,还显现了他作为文学大家和著名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智媒科技文化研究所”执行所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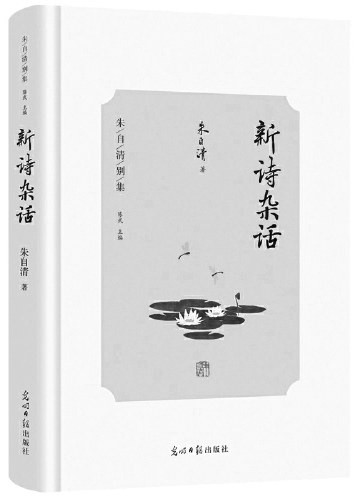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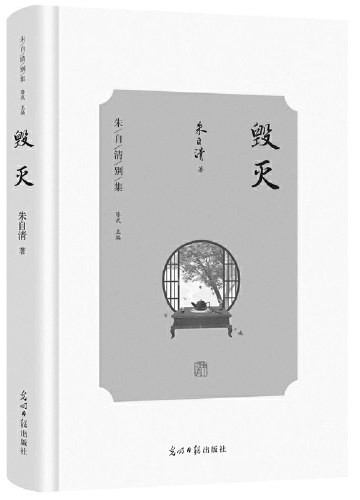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