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门经学是中华文明的文本根据与价值源头,已经非常确凿地支撑国人精神世界和日用生活两千余年。今天的我们注经解经,就学术形式、方法论而言,肯定已经回不到汉唐,也回不到宋明,更回不到乾嘉学派以来的清人那里去了。董仲舒、何休、孔颖达、徐彦、胡安国、高闶、戴溪、庄存与、刘逢禄、陈柱之类先贤能做到的、已经做过的,我们都做不到,不可能也没必要重复他们的学术劳动和成果样态。我们可以做的只是继承他们的精气神,立足自己的时代,而为古老经典注入新鲜的文化生命,增添旺盛的学术活力。这些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春秋经义训”团队研治公羊,专心致志地扑在经学上,尝试开辟一种“现代范式”。所谓“现代范式”,其狭义则是利用来源于西方的学科话语系统,泛指则可以是活在当代的人所展开的相对成熟、定型的经学解释倾向和特点,举其要领则至少可以包括八个方面:
主于《公羊》而结合《谷梁》《左传》。我们的立场在《公羊》,坚守家法师说,但又不拒绝《谷梁》《左传》。儒门十三经,《春秋》就占了三席,可见其地位何其重,分量何其大,作用何其关键。而在现行的春秋学系统中,三《传》各有偏向。《公羊》侧重于书法、辞法、礼法,尤其强调体例,多有“非常异义”,需要读者认真琢磨。《谷梁》主要阐释王道义理,指向明确,直截了当而不拐弯,语言凝练而深得要领,不太繁复。而《左传》则偏于历史叙述,不厌其烦地交代每一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结果,价值似乎中立。读一部《春秋》,相当于读三部经典,我们始终在三《传》贯通中理解孔子的意旨,辨析三《传》差异,最后再返回公羊家的主义坚持和原则要求,力挺《公羊》。
汲取哲学智慧,注重形上提升。这些年来,我们都在提倡并践行做“有哲学的经学”(der die Philosophie absorbierende Konfuz⁃ianische Klassiker),这其实就是一种敞开胸怀拥抱并吸收、融合了源于西方哲学营养的现代诠释方式,这样做至少能够捕捉到经文、《传》文中的每一条义理,深度挖掘经典中的概念、观念,充分展开话题内里,有利于把问题本身掰开来并逐一说清楚,个个讲明白,不无细腻地进行理性分析与形上阐发。既紧贴了文本自身,扣住中心事件不放,又能够上升到纯粹精神的层面予以言说,王法道义揭橥有力;既能够包纳具象,又善于抽象延伸,进而使得我们的经学研究始终不失思想高度。
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训诂、义理阐发四维结构。我们也致力于对经文、三《传》文本自身真伪、形成过程、相互差别及其文字的勘误考异,都尽量做出认真而细致的辨析。孔子著《春秋》,不会浪费一滴笔墨,所以我们在注释经文时也严肃对待了他的每一个文字,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是基本原则。字源追溯,衍文、异文、误刻辨认与纠正,字义挖掘和训诂,以及每一句话意义空间和文明价值的诠释,都尽量做得具体、到位而比之前的研究更富有信息含量。对于经文所蕴涵的王道义理,则竭力做出深度挖掘,揭掉遮蔽,钩隐索微,敞开篇幅,不加限制。即便对于老生常谈的经学故事,也试图阐发出新亮点,让读者能够有新的思想收获。
注重释放经传文本的现代价值。站在21世纪的学术定位上,尝试用现代人的眼光识别并激活蕴藏在古老经典中的自由、权利、民主、法治观念,努力让读经解经活动真正走进现代社会,融入现代生活,呈现其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同时,也可以让经、传、注、疏所伸张的儒家礼法标准与道义要求接受一次时代检验。“郑伯克段”事件中,君臣伦理与兄弟伦理、母子伦理之间的纠结关系,《公羊》“大郑伯之恶”的缘由,皆已经获得重新审视。“赵盾弒君”一案中,完全可以回归事实,分明罪责,而重新检讨作为国君的晋灵公早已有过恶在先,赵穿弒君则是在为民除害。宋伯姬“卒火”中,撕开个体价值与礼法原则之间的矛盾张力,而拷问王后、傅母生命伦理的关系权衡。季札一再让国,虽然成全了自己的个体谦逊“小德”,却输掉了国族之“大义”,而导致吴国政局长时间的动荡不安,因而产生对其还能不能称贤的质疑讨论。昭公出奔的政治流亡事件中,对季平子执政惠民、得民进行了重新考虑,深究君臣一伦中礼制尊尊形式合法性与大夫僭越而获得实质合法性之间的对冲,显然是在为人民利益的真实需要而鼓呼。
解经活动一般都首先必须基于《传》文。为了解释《传》文,则又得《注》《疏》。然而,通读《春秋》经文与三《传》,则不难发现,《传》文经常不能够达到经文的含义,甚至还会歪曲,走进相左、相反的方向。这种情况下,经、《传》得分治,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经是经,《传》是《传》,各解各义。《传》基于《注》《疏》,却又能够跳出《注》《疏》,并且把《注》《疏》看作是既有密切联系,又可以相对独立的两个解释系统,不再要求“《疏》不破《注》”。从哲学解释学的一般理论稍加引申则可知,每一个解释主体对文本的解释都是合法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文字、话语的完全相等的解释,符合本义的解释一直在路上,却始终都到不了目的地。因而《注》未必能够真正抵达经、《传》文本自身,同样,《疏》也不可能完全抵达《注》。与其死“守《注》”而又达不到,还不如大胆而公开地承认《注》《疏》之间的距离。董仲舒的《繁露》、何休《解诂》都只是他俩各自对《春秋》的诠释而已,硬要分出一个谁对谁错则多半是不落好的徒劳,所以,也就不必再让后世学者拿去当作解经千古不易的圭臬了,过分强调遵守则无异于扼杀解释者自己的创造力。徐彦《疏》也未必能够完全与《解诂》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在我们的公羊学研究中,《注》《疏》之间甚至包括经、《传》之间经常被当作各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分别揭示并阐发其学术义理。
不以学科分野为路径去肢解经学,却又能够吸取各学科之养分。学科之分是西方现代知识系统发展的产物,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根本无论归入任何一门既有的学科之中。使用任何一个学科研究范式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春秋》自己的诠释要求。但它又可以被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所审视和研究。我们可以在何休《解诂》关于“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中,挖掘出“五始”的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天文学、本体论、宇宙论、创世论、宗教学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春秋》灾异说中,在旱、不雨、大水、虫、六鹢退飞、西狩获麟、沙鹿崩、梁山崩等事件中,我们一旦借助于天象学、气候学、水文学、水利学、动物学、地质学的透视镜,则肯定会比古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郑伯杀段,但从道德学、伦理学去谴责则是远远不够的。对天王归仲子赗的批评,也不可能只限定于事前认识论上的无知,礼法本身虽然是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但又不失一定的约束力。
从问题本身出发而展开研究,跳出汉学、宋学的区分,既不唯汉学是从,也不独任宋学;既不完全“我注六经”,也没有绝对陷入“六经注我”;既不被书法、辞法、礼法之体例限定死,又不至于在义理世界里天马行空而不着边际。过往的“二分法”解经多半显得苍白而无聊,实际上,对任何一句经文、传文的诠释都应该是兼及性的,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单向度的依赖,并不在意人为的分殊。撇开“二分”思维,直接面对事件本身而进行有意义的挖掘和阐发,该训诂就训诂,该考辨就考辨,该阐发义理就阐发义理,而不会被既有成见所左右,也不会被传统界说所吓到。别让眼花缭乱的各种经学分期说牵着鼻子走,无论刘师培的“四期说”,还是《四库提要》的“六期说”,江藩的“十期说”,皮锡瑞的“十期说”,都只当它们是某种人为划定,实在无谓,而沉浸到具体的经文、传文中去寻找真谛,因而显得扎实有力。以“我注”催生“注我”,以“注我”提升“我注”。对许多公羊经传文本中诸多文字所做的语源学、语用学考察,很见工夫,做得很是漂亮、精彩。
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人、事、物。站在21世纪的历史角度上,开阔眼界,绝不可对波澜壮阔的西方文明熟视无睹,而是采取一种学习、参考的积极态度。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能够发掘中国本土的时间制度,发覆其以生活事件为中心的时间传统,进而阐述中国特有的时间政治与时间哲学乃至创世理念,而与基督教文明的纪元传统形成明显的区别。对于《春秋》中诸多歃血誓盟,能够与西方契约文明相比较、相砥砺,而揭示出上古中国并不以文字条约为最高信用的事实,在礼乐文明昌盛的时代,口头承诺的方式更值得推崇。“获麟”后的孔子,能够自觉编撰“六经”,存亡继绝,有意总结并接续三代文明的先进成果,而在人类文明滥觞、起步、塑形的那个“轴心时代”能够为中华民族开辟、创设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明范式,树立起一面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考虑的理想旗帜,即仁道主义,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们族群存在和文明走向的正义属性,也使我们的族群第一次获得身份上和文化上的双重认同。孔子在那个礼崩乐坏、霸道横行的乱局中,执意要把我们民族引向一条王化正义的坦途,而不是一条打打杀杀、抢夺掳掠的死胡同。所以,我们在解经过程中一边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一边又能够舒解胸襟,坦荡面对外来文明,并乐于接受和消化其有价值的养分。
至于对董仲舒解经文字的重视,对何休《解诂》、徐彦《疏》每一句话都加以征引和诠释而尽量做到一无遗漏,则是我们团队解读《春秋》的一大独到之处,这些都已经在《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序言中有所介绍了,而不再列入“现代范式”。
我们团队在交大举办的“公羊读书班”,从2020到2021历时三年,面向本、硕、博不同阶段的学生,也吸引了海内外许多青年学者踊跃参加。作为《春秋》开始篇的《隐公元年》,由余治平领读、讲解,先后六周课,总共18课时,讲稿文字超十万。而作为公羊《春秋》终结篇的《哀公十四年》则由唐语鲛领读、讲解,虽然只有一次课的机会,但从晚上六点到十一点半,全程精彩,荡气回肠,听得大家沉醉如梦,意犹未尽,初步讲稿就有八万多字。董学有“十如更始”的主张,极力阐明“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原理,则可知阴阳循环、永无止竭是中华文化的创世理念,并也由此而引申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历史哲学和时间传统。读书班进行过程中,我们就有意在将来用心挑选出一些精彩篇章的讲稿尝试以年度为主线而出版“春秋零读系列”丛书,即把《春秋》经传注疏作化整为零的碎片化解读,张靖杰的《庄公四年》,张禹的《宣公六年》,代春敏、Paul Napier的《宣公十五年》,张咪的《襄公三十年》,等等,都很有料,都可以单篇析出而熠熠生辉。至于我们二人的《隐公元年》《哀公十四年》,原本也可以独立成书,但联袂撰作《春秋终始》则显得更有意蕴,纵论麟经的开端与结束,首尾衔接,圆善自成,在实现学术薪火相承、代际赓续的同时,似乎也有意要让儒门圣道能够返本开新,使《春秋》大义运转来去,生机盎然,而“民世世传”之。实际上,在解读《春秋》的过程中,大家也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242年流水账,一年一年又一年,此起彼伏,讲解、写作的任务没完没了似的,看不到一个头;形式单调枯燥,还掺杂着许多重复劳动;讲稿改了一轮又一轮,文字表达越来越有力量,思想高度不断提升,意境渐佳而扣人心弦。而这恰恰就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原色,是人类历史的本来样态。
(本文为《春秋终始:公羊经学研究的现代范式》前言部分,余治平、唐语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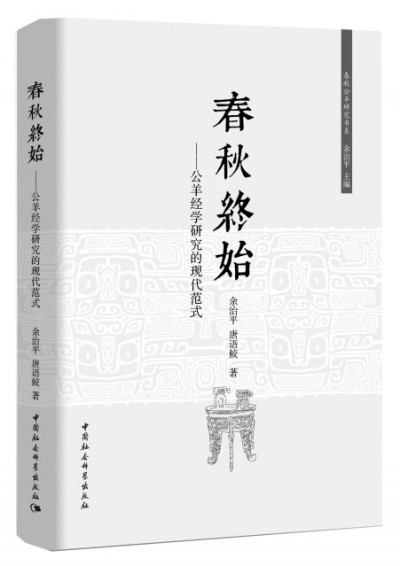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