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煜
近日,读到了王新程先生散文集《大地与尘埃》。
据我所知,《大地与尘埃》的问世纯属偶然。作者写这些文章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纪念,并非为了出版。2020年,母亲离世后,作者痛苦万分,在微信上断断续续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母亲的文字。用作者的话说,写作的初衷“是想把母子同行五十多年的点滴记录下来,把在仓促人生中没来得及跟母亲说的话说出来”。后来,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下,作者将对亲人的感情扩展到对家乡人事物的思念和追忆,陆续写出了后面的篇章。正是这种不带功利的写作,才让笔尖真情流淌,让人读起来如见肺肝。
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虽已告别文青岁月,但仍刻意去搜罗各家散文随笔来读——我希望被感动。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这样的期盼,其实也只剩下期盼了。或许,是我的心变老了,变硬了? 直到读了《大地与尘埃》,我才又对自己的“心”充满了信心。因为,此间仍有让我泪流满面的作品。
一
《大地与尘埃》是一部家族史。这部家族史,并非传统一家一姓的历史,而是写了三家人:父族王家,母党樊家,姑姑冉家。
官渡滩王氏的始祖,本是酉阳冉姓土司的女婿,后因土司遇刺,不得不逃到偏远的官渡滩避难。作者祖父三十八岁谢世,祖母带着作者年仅十五岁的父亲以及年幼的二叔和姑姑生活。期间,二叔曾一度被送给贵州洪渡岩万家抚养,姑姑也差点被人收为童养媳,最后还是父亲将二叔找回家,全家才得以团圆。家族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徐徐展开。
在家族史这部分,重点叙述了三个人物:母亲、父亲和姑姑。
写母亲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作者在第一节中对母亲的身世作了简短交代:生在贫困农家,年幼失怙,成年后嫁给了同样贫穷的父亲。作者对母亲的评价是:“她在土地上的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有点聪明的丈夫,生养了三个让她安心的儿女,其他没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服,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看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官渡滩土地。”
但是,就是这位平凡的母亲,却给了作者极不平凡的爱与教育。作者幼时体弱多病,母亲为了让他更健康一点,竟然哺乳到五岁。在农村大集体岁月里,母亲劳动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把食堂分发的饭团悄悄带回家给作者吃。但母亲深谙慈母多败儿的道理,从来不溺爱孩子,刚断奶就把作者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做错了事也必定责罚。母亲经常教作者做人的道理,叫他要知道感恩,行事公道正派,切不可忘本。
母亲一辈子受苦,早年经历了种种磨难。就在可以安享晚年的岁月,却因误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在医院,母亲非常配合治疗,不管化疗有多么痛苦,她都默默地忍受着。甚至在返家的最后时光,母亲仍然在跟病魔斗争。作者写到:“当疼痛来袭时,如烈火焚身,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紧紧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但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这位刚强的母亲还是在庚子年(2020年)腊月初九日,永远离开了人世。她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搬盘你们了”(“搬盘”为当地方言,意为“麻烦”)。
该书以“父亲是棵树”为题,用第二章来写父亲。母亲像大地一样,给作者以生命,且持续不断地给这个生命以滋养。父亲则像植根于大地的一棵树,为大地也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为子女撑起一片阴凉。父亲还代表眼界和高度,时刻注视着周遭的阴晴变化,他将一众儿女托举到高处,让他们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风景,直至将他们送到自己想象中的远方。
相对母亲来说,父亲的经历也更复杂。少年时期的苦难,将他打磨成一条硬汉,养成了他略显强硬甚至有点霸道的个性。这里面最能表现其雄强本色之处,就是声言要砍杀姐姐第一个男朋友。还有一个细节,也展示了他很“男人”的一面。他每次离家外出,总是沿着河岸一直往下走,从不回头望一眼正在驻足目送他的妻儿,以至于作者至今仍觉得在童年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背影。但是,在这张貌似“冷酷”的脸孔下面,却是满满的温情。作者幼年时跟随父亲贩羊的经历,以及父亲外出赚钱准备姐姐嫁妆的细节,都充分展现了这位父亲的慈爱。
作者并未采取仰视的姿态去叙写父亲,也似乎忘记了“为尊者讳”的古训。父亲不止一次以“霸蛮”的形象在书中出现。比如,写到父亲强硬逼迫姑姑嫁给其表哥的情节,几乎就是在控诉,在声讨。
当然,作者对父亲又是理解和同情的。在作者眼中,父亲是个聪明能干的人,有一身好手艺,还时不时搞点发明创造,有点乡村爱迪生的意思。由于父亲有游走四方的社会经历,其社会阅历自然是众邻所不能及,所以他在官渡滩乃至所在乡镇皆享有较高的威信。加之父亲待人接物非常“仁义”,因此结交了很多有知识甚至有权势的乡村人物。这些都是作者崇拜的地方。
父亲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他所经历的时代。由于自幼贫穷,即使后来家庭富裕了,子女孝敬也颇为丰厚,但他却舍不得花钱,曾多次将孩子们买给他的名贵烟酒悄悄转卖给村头的小卖部。更俏皮的是,他又很好面子,明明把好烟换了钱,自己却又要将普通香烟装到名贵烟盒里,好让人知道他抽的是“中华”。还有一个细节,更是令人心酸。作者和侄子带他去配助听器,戴上之后挺高兴。可当他得知要一万多元的时候,竟然负气冲到马路中央。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四方来车像潮水一样涌来……他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像潮水里的一片叶子,回过头来茫然地望着我们。”最后,作者冲到他身边,攥着他的手。他又像一个孩子,听话地由作者牵着回到了马路边。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位“老抠”,那就错了,因为他平日里可没少周济邻里乡亲。当一位族人因火灾需要重建房屋的时候,他竟主动开口,愿意拿出自己平时攒下来的八万多块钱帮人重建家园。是的,我们不能苛求一位被饥饿加冕过的老人像王子一样体面地生活。
都说岁月能改变世间万物,但人的某些经历却永远地刻在了岁月的骨子里,要想改变是十分困难的。按理说,父亲早已“不差钱”,但他对待金钱却一如既往地“小气”。在这“小气”的背后,潜藏着的却是一种节俭的美德,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珍惜,更是饱经风霜之后的一种条件反射。这种“小气”恰好是苦难颁发给他的一枚勋章,没了这枚勋章,就无法证明他的存在。
该书还有一个特出的地方,就是与写父母一样,同样用一整章的篇幅来写姑姑。由于祖父去世得早,家庭贫穷,姑姑未上过学,一辈子大字不识。在女大当嫁的年纪,一位中学教师看上了姑姑,却被父亲生生阻拦,逼着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姑姑自然进行了难以言表的激烈抗争,但最后却选择了理解和认命。可怪的是,姑姑并未怀恨自己的哥哥,不但帮着哥哥嫂嫂带大了侄儿侄女,后来竟主动承担起侄孙的救护责任。彼时,侄孙得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肠道恶症,全靠姑姑和姑父四处求医问药和悉心照料,才把孩子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姑姑对娘家的奉献实在太感人了,以至于作者在书中感慨道:“有时候我想,我的姑姑和姑父,简直就是为收留我们而存在的。”后来,姑父在帮娘家建房的时候,不幸从三楼摔下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母亲去世之后,姑姑为了照料哥哥,竟然舍弃家业,搬回官渡滩与哥哥居住。这大概就是作者在书中称其为另一个父亲和母亲的缘故。因为,这位姑姑确实尽到了父亲兼母亲的责任,用自己的牺牲守卫着自己的娘家。
二
此书还是一部社会史,一部通过家族史展开的社会史。虽然作者并未刻意去突出人物的时代特色,但却在写事记人的过程中,为我们不动声色地还原了种种社会历史事实,包括普通民众所遭受的磨难,以及当地的民风。
这里面有饥荒年代的痕迹,也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作者对饥荒年代着墨不多,只提到了两处。由于枇杷树皮已被村民剥下吃光,母亲别出心裁,改用柿子树皮来作食,差点噎死了老祖母。与此同框的画面,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作者写到,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种了南瓜等作物,可当这些作物才刚“打胆胆”,就引来了大队干部的巡察,饥民的自救之路就这样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毁掉了。如果没有此类记录,后人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先辈所经历的荒诞历史。
作者用非常浪漫的笔触描述了自己跟父亲贩羊的经历,但这点“浪漫”却差点将父亲送进了监狱。由于父亲提前终止了“投机倒把”的“罪行”,所以并未获刑。但作者的姑父就没有这么幸运,最终因为贩卖桐油被判了三年徒刑。
饥饿是对那个时代鲜明的记忆。作者写到一个细节。母亲炒菜前,先将切成小块的猪肉放在锅底煎一下,等锅底有油星冒出时就赶紧将肉片提起来,留着下次使用。笔者也曾听老人讲过,那年代上街买肉,最怕的就是屠夫给割瘦肉。因为瘦肉不出油,没法用于润锅炒菜。这大概又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吧。
书中也不动声色地讴歌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写父亲的篇章当中,作者以十分轻快的笔调,借写父亲过州府县补桶大把赚钱的喜悦,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发展多种经营的盛况。再后来,不但作者家族得到了巨大发展,所有官渡滩的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可以说,官渡滩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大发展的缩影。
作者对官渡滩风土人情的记写也值得一提。书中记录了大量的民俗文化,尤其是关于禁忌的信仰。作者十五岁那年的退婚,表面上是因不慎掉到准岳父家茅坑里引起的反感,但这种反感背后其实是植根民众心里的禁忌在起作用。作者的父母尽管舍不得放弃这门亲事,但最终还是出于对这种“凶兆”的担心而放弃了“高攀”。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官渡滩存在的语言禁忌。父亲之所以阻止哥哥王琦参军,其实就是对语言的禁忌和恐惧。哥哥考上空军,志得意满,整个官渡滩都为之兴奋。当时家里正好在修造,暴雨将至,父亲让作者去把炮眼给盖上,谁知平时不怎么干活的哥哥居然脱口而出,说“我去堵炮眼儿”。就因为这句话,父亲死活不让哥哥去当兵。因为,在作者家乡,人们相信语言是有魔力的,父亲将当兵、打仗和堵炮眼联系在一起,自然就不肯放行了。书中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这样的民俗资料。
该书还在不经意间提到了农村养老问题。母亲去世后,为了安全起见,作者的侄子给家里安装了云视频摄像头,使得一家老小能够及时了解老人的动态。尽管作者可以在千里之外清楚看到老父亲哆哆嗦嗦地淘米,看到他笨手笨脚地切菜,但却无法给老人以亲情和温暖。透过冰冷的摄像头,我们可以感知老人的孤寂和无奈。是的,不管经济和科技多么发达,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情感交流。
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日渐尖锐。作者父亲曾自提解决方案,说等房子建好后,让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过来与他们夫妇共同居住。这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家族团体整体崩解的大历史面前,在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数十年之后,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养老方案,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该书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主题:仁义和感恩。简单讲,仁义在乡民那里,就是对外施恩;感恩则是对别人施恩的回报。作者父母一生都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知道感恩,也一直在施恩和报恩中循环。当专家们还在围绕《论语》争论什么是“仁”,什么是“义”的时候,偏远的小山村却一直在践行着古老的伦理教条。礼失而求诸野,岂不信然?
最后谈谈该书的语言特色。这本散文集在语言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保留了当地人的方言土语。该书的绝大多数对话,都采用了渝东南尤其是官渡滩的方言。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那热”这个词,如果对渝东南土家苗寨文化缺乏了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个词只是土家苗寨儿女的一个发语助词,并无确切的意涵,更与冷热无关。其他方言,比如“撇火药”“啷个”“么子”等等,都非常鲜活。在全面推广普通话的今天,给方言留一点点空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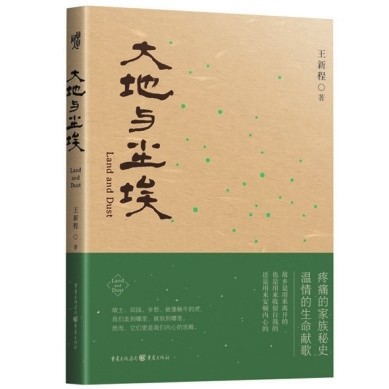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