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霞
2020年9月,在失业焦虑重重围困的情况下,五十二岁的母亲春香终于接受了女儿小满的建议,与丈夫一同自陕西商洛启程,奔赴远在1500公里之外的大都市深圳。尽管母亲此番前来的首要目标无他,只是挣钱,但这段长达三年的同住时光无疑为母女二人提供了一次共同成长的机会。
一、记录:母亲的打工史与生命史
10月,春香入职保洁员。对于这个“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还因患有滑膜炎不便久站久坐的农村妇女而言,做保洁也许是最标准、最合适的答案。
晨光熹微,春香已经着手工作。抹布、拖把、尘推杆、垃圾铲……十多斤常用的清洁工具一股脑儿地装在桶里,她走到哪儿提到哪儿。电梯、楼梯、办公室、厕所……三份保洁工作里,她负责的区域不尽相同,但清洁任务永远只多不少,工作时间往往被细枝末节的流程越抻越长。甲方的投诉、经理的责难更似悬在头顶的利剑,让她难有片刻安心。即便如此,春香还是憋着一口“我怕个屁”的劲头,凭着自己向来引以为傲的“算计”,摸索出一套“飘深圳”的生存法则。她大胆探索起这个崭新的环境,主动与邻居、同事以及其他领域的打工人交谈,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面对职场中的不平等,她敢于反抗,上级当众批评并开除翠竹阿姨一事令她义愤填膺,“如果他要是这么对我,我一定要把他好好说一顿再走,不然这口气怎么出”。只要行得端坐得直,她连督管的投诉也不怕。早些年在建筑工地、矿山、国营农场等地磨炼出的那股柔韧劲,支持着她不断前行。面对保洁这份前所未有的“简单”工作,她从未萌生过退却的念头。
在与深圳磨合的同时,春香不曾忘记与故土亲人的羁绊。她时常梦回田园,但姑姑的离世无疑又向她揭示了一个群体性的悲哀:家乡父辈靠最重最累的体力活营生,挣钱的执念令他们无暇顾及身体的病痛,一直拖到再难忍受,他们才前往医院,而此时等待他们的往往只有死亡。他们像杂草一般生存着,有时一场疾风刮过,便消逝于天地。如今,回归故园已成幻梦,至多为春香提供些许精神抚慰,既已走出,她便要多待几年。未来如何,她的回答是“到时候看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要把根继续往深圳的深处扎,她要挣出那份养老钱。
二、挖掘: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从超级商场到政府大楼再到高级写字楼,春香逐渐在深圳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域。她在巨型城市机器中更新着自己的生命经验,也为女儿小满带来了一个机缘,一个正如小满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的那种切入“底层人民微观生命史”的机缘。
“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来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事实往往是这样,我们一边夸赞保洁员是“城市的高级美容师”,一边又将他们挤压到“城市透明人”的位置。在整个权力系统中,保洁员被安置在最底层听候审判,即使面对不近人情的命令,他们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服从,而几乎失去了表达和争取的权利。除此之外,另一个更令人揪心的真相是,“这种过劳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合谋”。他们选择留下,有的是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有的是像春香一样为了挣养老钱,有的甚至只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来到深圳,是因为这里的冬天暖和,他不想自己冻死街头也无人知晓。即使住宿条件再差、工资再低、条条框框再多,这份保洁工作于他们而言也是必须的,他们要在尚能劳动的日子里,抓住这份“摇摇欲坠的安全感”。
在承认保洁员群体确有难处的同时,小满又不时提醒我们,劳累与肮脏只是他们工作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们的人生还有更多维度。雨虹无疑是保洁员中的“异类”。2002年,原本在餐厅工作的雨虹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一户韩国雇主的住家保姆。后来借着替雇主办业务的机会,她向管理处毛遂自荐,承包下了整个高档小区的垃圾处理。当雇主有需要时,她前去照顾,闲下来时,她就分拣垃圾。很难想象,这个埋首垃圾堆中的女人能说一口流利的韩语,会护肤化妆,会不时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雨虹的目标是干到六十五岁,等到垃圾房有人接手,她也赚够钱的那一天,她要独自前往大理,享受纯粹的自由。
三、审视:“我们有一样的来处”
正如饼干所言:“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和小满这样的白领,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可以不用再整天为吃的发愁。但当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俯瞰,大地上到处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父辈和同龄人。如果从更高的视角看,我们的挣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领域和程度不相同而已。”
高级写字楼超高浓度的竞争氛围中,年轻的白领几乎没有一丝清闲,他们忙于案头,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视厕所为避难所。无论怎样进行暗示,里面的人自岿然不动。春香无法理解年轻人为何如此“钟爱”厕所,而身为局中人的小满明白,厕所是当代年轻人缓冲压力的功能间。在一个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奔跑,才能勉强停留于原地。那些看似摆脱了父辈困境,寻得一份体面工作的青年人,本质上也和父辈一样。他们是城市机器里一颗无休无止的螺丝钉,躲进厕所,成了他们得以喘息的一个机会。
被主流社会放逐的恐惧不是残存在春香一代人身上,时至今日,它仍旧萦绕在青年一代的心头,挥之不去。困在其中,没有人能真正地放松下来。这是小满透过母亲的眼睛,看见的城市生活镜像中的自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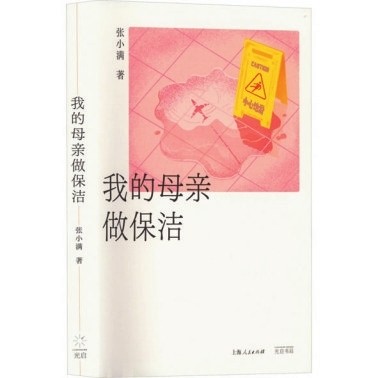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