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进
“刘醒龙地理笔记”系列包括《上上长江》《天天南海》《脉脉乡邦》三部曲,收录作者近10年来行走大地的山水散文99篇,且大部分作品是在高铁上和旅馆里写成的,有感而发,发为心声,虽为短制,却意味深长,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文学报告,也是行走乡邦的山水文学。刘醒龙说:“文学一定要回到第一现场。我自己这几年在外面行走很有收获,比较集中的有走南水北调、走长江,前不久又去南海一趟,每走一次就开一次眼界。”(《天天南海·后记》)这里的“收获”说的就是“地理笔记”三部曲。作者以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笔法,描绘了他眼中的风景和心中的愿景,追寻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给人爱与信念、善与自信、美与创造的精神力量。
面对一条大河,人文行走是一个大词
行走长江,有一种激荡人心的磅礴力量。《上上长江》主体为作者参加报社“万里长江人文行走”活动的所见所感,以及平时“为长江一衣带水的地方写过不少篇章”的散文精选,“弥补了一口气走完长江全线,由于时空限制留下的那些无可奈何的空白”,完成了文学“自己的天命”(《上上长江·后记》)。作者40天走透长江,从通达东海的吴淞口走到唐古拉山下的沱沱河,不是随团旅游式的走马观花,而是一次“人文行走”的探源之旅。
面对一条大河,人文行走是一个大词,只有怀着大词行走,才能在汨罗江遇上杜甫,在醉翁亭遇上王黄州,在和县遇上项羽,在江津遇上陈独秀,在三江源遇上那位坚强的父亲——搀扶着儿子四处找人急救,却隐瞒了自己比儿子更危急的高原反应,还有在通天河畔遇上狼,以及流传的一窝狼崽与100只羊的生命传奇。不经意间与古往今来的人事撞个满怀,拂去时光的尘埃,看透历史与文学的奥秘,体察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况味,情怀也会变得澎湃起来。沿江而上,越走越感动,越走越亲切,越走到最后,越觉得长江就是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灵魂所到达的源头更遥远,因为“除了地理源头,还有科学源头和文化源头”(《上上长江》)。“人总是如此,一旦发现,就会改变。不是改变山,也不是改变水,而是改变如山水的情怀,还有对山水的新的发现。”(《迷恋三峡》)
水是有文化的,自然的进化,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脚印,文明的历程,都可以在长江流域的山水中见识;水是有记忆的,长江流域就蕴含了太多的历史,震撼人类考古学的元谋人在这里被发现,现代史上红军四渡赤水的奇迹在这里发生,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在这里建成,让天堑变通途的长江大桥在这里架通;水是有灵性的,平静澎湃是它的常态,载舟覆舟是它的性能,人类一任性,长江的厄运就来了,长江一任性,人类的灾难就来了;水是无私的,那最早的一滴水不属于它自己,那是献给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的,那是献给风云雨雪飞禽走兽的;水是谦逊的,总往低处流,不会好高骛远,无以计数的一滴滴水汇成一条大江后,才将大海作为最终目标。
山有山言,水有水语。“水做的长江显现出与普通人类似、却又绝对不可能普通的情怀”,是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 面对生我养我的母亲河,每个中国人都会心潮澎湃。“试想长江源头清澈的一滴水,从格拉丹东冰川开始流动,穿过崇山峻岭、水乡平原,直至汇入汪洋大海,其情其景何止妙不可言?”看一眼与长江日夜同在的渔翁,还有从遥远北方飞天而来的黑天鹅,这样的长江比水天一色的辽阔海洋还要美丽,她永远保持着向前向前向前的奋进状态。
大江东去,千古风流,风吹两岸,岁月如歌。通天河边活在岩石上的文成公主,乌江不渡慷慨悲歌的西楚霸王,汨罗江边荒凉寂寥的杜甫墓,江津石墙小院中的“新青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兴衰荣辱的“汉冶萍”,仁可安国的青云塔,冲江河上的铁虹桥,永修境内的柘林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虎族之花,吉祥如狼,不负江豚,黄梅小戏,茉莉江南,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文化。万里长江用每一滴水创造的自然奇迹和人文奇观,无不在给人民启示与警醒。山水以形参道,“问题是我们如何体验、如何学习对它的参悟”(《真理三峡》)。
南海四千里,每朵海浪都怀有千钧之力
泛舟南海,有一种“神奇让人失去想象力”(《我在南海游过泳》)。《天天南海》包括“南海日记”和“海上散记”两辑,其中“南海日记”是2021年6月1日至6月20日期间,作者第三次到南海行走,乘坐“琼三亚运86399”号渔船考察南海的“奇遇记”;“海上散记”是作者第一次、第二次到南海的见闻所感,以及作者第一篇写大海的散文《赫瓦尔酒吧的和声》(1995)。在作者心里,“天底下的海,叫南海! 心灵深处的海,叫南海! 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我有南海四千里》)。
这里是神圣的海疆。我有南海四千里,这里的每一朵海浪都怀有千钧之力,每一股潮水的秉性都是万夫不当之勇。这里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第五兵种”雨水兵,在雨水兵心里,南海天空上的每一滴雨都不是多余的;在中国人的眼里,南海再大再深,每一滴海水都不是多余的(《我有南海四千里》)。渔民出海如同出征,安家就是卫国,卫国就是守卫国土上的一草一木,南海国土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菩提南海树》)。这里有西沙群岛最北端的灯塔,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灯塔本身,白天里高大的灯塔象征中国的身影,夜晚里灯塔上的灯光放射出中国的光明(《有一种鱼叫海狼》)。
这里有奇幻的色彩。船行海上,找不出看不到海平线与海岸线的地方。由近及远,海水从很蓝变成更蓝,又从更蓝变成更加蓝,无法形容南海独有的蓝,或稠密如蓝水晶雕塑,或晶亮如蓝宝石首饰,或结实如蓝玛瑙卵石,或柔美如元代青花瓷。最奇妙的是全富岛上雪白细沙铺成的无人小岛中间竟有一汪水池,那水也是碧蓝的(《全富岛上一棵草》)。这样的蓝色是在地球上看太空的颜色,是从太空看地球的颜色,也是人类命运的颜色,就像生命源自海洋一样(《寻得青花通古今》)。南海蓝,蓝海南,将蓝颜色发挥到撼动人心的南海,是开在人世间的一朵最大的蓝色花(《菩提南海树》)。“对于人的想象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南海的恩典呢?对人的情怀来说,还有什么比南海更能使人心性皈依呢?”(《我有南海四千里》)
这里有奇妙的传说。南海水天一色,变幻万端,正是产生传说的秘境。传说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只有拥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才有资格成为传说。“海南本身就是传说”(《传说不识红树林》),你看那海南岛上的黄花梨、南海岸边的红树林、珊瑚礁形成的鸭公岛、铜鼓岭下的老爸茶,以及甘泉岛上留下的唐宋灶台、宋氏祖居的荔枝树、西沙群岛的北礁灯塔……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平常的生活相隔甚远,看上去互不相干,却往往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说文脉也好,文运也罢,看似虚得不得了,不可能存在,实际上是有迹可循,“久久不见久久见”(《南海蓝之蓝海南》),在传说中看见历史正朝我们走来,又向未来走去。没有了传说,就没有历史,也没有今天和未来。
这里有生命的传奇。树在内陆是最平常不过的存在,但在南海却是生命的传奇。只要问一问南海,就知道在海天之间,有一种珍宝叫作树。大自然在人类由海洋向陆地进化的交接处,安排了一种叫红树林的生物,其主动适应不同环境的绝妙能力,“给人类竖一面镜子”“给人类预设一种密码”,保护红树林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传说不识红树林》)。拥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南海的五棵百年古树,它们是怎样在永兴岛和晋卿岛上活过自己的百年? 在南海能够活下来的树肯定有原因。在南海有一种比天还大的事情叫种树,于是有作家们在赵述岛种下的一片椰树林,这里也是祖国最靠南的一片作家林。选择椰子树不是因为椰子树知道一棵树能够在南海活下来的原因,而是椰子树有让一切小草在树下从容生长的品格。在南海一棵极不起眼的小草,其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一棵椰子树苗,也不亚于那五棵早被当作至宝的百年古树。因而当人们发现光秃秃的全富岛沙滩上突然生长出一棵小草时,那是怎样的生命奇迹。只有“真的能做到如同生长在南海的椰子树,才懂得与任何一朵小花、任何一棵小草共生共荣的意义。”(《菩提南海树》)
从来大海是人师。作者说,“南海在用一种更加强大的能量浸润我的每一寸肌肤,以给我新的温情、新的才华和新的命运”(《蓝洞》),我“用尽全部身心,让每一根毫发、每一只毛孔、每一片肌肤和每一次脉动,通过南海的一滴水、一粒沙、一块礁石、一只在珊瑚树丛中游嬉的彩色小鱼儿,最大限度地与南海好好相处”(《南海蓝之蓝海南》)。“人入南海是换了一种方式的生活暂停”(《大水冲了龙王庙》),告诉人们,“世界上最强大的生命力不是尽一切可能去折腾,而是像大海那样,将真正的伟大安放在肉眼所见的平静之中”(《天天南海·后记》)。
乡邦是吾乡,以文学流传大地
乡邦是吾乡,有一种爱与生俱来。何为乡邦? 生我养我之地是乡邦,高山流水之处是乡邦,哪里有高铁哪里就有乡邦,到过的地方就是乡邦,心到的地方也是乡邦。从东湖梨园的临水小楼里,依稀传出当初水边浅窗内作者纸笔厮磨沙沙声慢;在南京至武汉的G1735次列车上,仿佛听见冲江河水拍打“铁虹桥”的啪啪声响。
《脉脉乡邦》中,记录了作者半个月时间行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见闻感想,倾诉着“何处不乡邦”的脉脉深情。情到深处,作者喜欢用“天”来表达他的最爱与赞美。写二郎小城之山水云雾,醇厚、绵长、舒展、神秘,他将这让人心醉的万种风情,赞为“天香”(《天香》);写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之深秋红叶,奔着秋色而来,片片只只,层层叠叠,团团簇簇,他将这比作高擎“信心与信念”的火炬,惊为“天姿”(《天姿》);写苏北东海水晶之晶莹剔透,包罗了山的大千气象和水的无边天色,仿佛与水晶般通透的童年重逢,他将这无限接近你我的童心,叹为“天心”(《天心》);写胜利小镇沙滩之洁白无瑕,七分像雪,在黄昏下闪烁起天然的灵性,像极光一样将小镇映成了白夜,他说“它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天赐的”(《白如胜利》)。写胜利小镇通往主峰天堂寨景点有一句旅游口号,叫作“胜利通向天堂”,“天堂”一语双关,反映了小镇人笑说生死的乐观心态,是胜利者的“人生境界”。作者说:“天堂本来就是心中熟悉的美丽与灿烂”,而去往天堂的薄刀峰要过十八道关,每一关都仿佛走在刃口上,都是对“信心与信念”的考验(《灿烂天堂》)。不断满足人民对天堂般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站在赣南红土地上的那位将军所开始的比当年红军长征还要艰难的“党性长征”和“人性长征”;正是感动了历史的人民,才有足够的力量“让钢铁拐个弯”,才有京九铁路穿行赣南红土地,在被血与火浇浴和焚烧过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让钢铁拐个弯》)
人民就是天! 高铁让老区人民走出深山,走过贫困,走近幸福,走入新时代。几乎一夜之间,武汉这座城市就成了无与伦比的出行极为便捷的高铁运行中心,其独步天下的优雅气质,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武汉形象,也改变了作者的写作习惯。在心安与平稳的高铁上,作者正好打开电脑,“去时写好初稿,回程时细细改定,一篇短文就写成了”。作者坚信“在中国大地上流传的文学,终将与殊途同归的高铁一样,成就中国气派和中国气象”(《脉脉乡邦·后记》),讲好爱乡邦爱国家、爱生活爱人生的中国山水故事。
召唤孩童,同入文学绿水青山
《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是《乡邦脉脉》里的一篇,写从丹江口水库大坝启程,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程的“一场与山水盟约的长途行走”,是作者追寻丹江的水精灵来一场穿越殷墟遗址、黄河古道、华北平原,来到北京团城湖畔的中华文明探源之旅,也是“献给天下清流源源滋润的这个时代的绿水青山”——作者“太想了解这天河一般流淌的大水除了滋润数以千万计人口的生活之外,还会给京津冀豫地区的生态带来何种变化”。
这篇散文集中体现了刘醒龙“地理笔记”创作的“三层境界”。一是自然地理层面的写境,摹写自然山水之美,是行走大地的山水游记;二是文化地理层面的情境,写发生在大地上的人文风情,是有寻根意味的文化散文;三是生态地理层面的心境,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沉思,是描绘绿水青山美好画卷的生态文学。
山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首《关雎》的第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借山水来比兴的创作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创了中国文人寄情山水的新篇章,结出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颗山水文学的硕果,形成了行走大地、触景生情、托物言志,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现象,也在“性灵说”“神韵说”的影响下,为纵情山水、逃避社会、遁入内心有了可以逍遥的世外桃源。
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母题,不仅继承了中国山水文学的创作传统,而且在创作中使主体与客体发生了本质性转换,如果说传统山水文学的主潮反映了“自然的人化”,那么,与之相比较而言,刘醒龙的“地理笔记”更多书写的是“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作者选择长江、南海、乡邦这三大题材,重点不是要描绘其自然地理风貌,而是更多地从其蕴藏着的文化价值及生态价值出发,从以山水修养性灵走到再以性灵统领山水的新境界,作者直接写自然山水的很少,以山水为话题引线的文化内容很多,因为作者醉翁之意不在山水,在乎山水中承载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以文学的绿水青山见证人与自然的关系,刘醒龙在“地理笔记”里体现了他独特的山水文学观。
一是崇尚水文化。作者生活在“百湖之城”的武汉,又生长在长江边,因而他大声宣告,“天下大同,万物花开,我第一喜欢水”(《上上长江·母亲河》),“每当要在山水之间做选择时,自己总是喜欢选择水”(《天天南海·后记》),只要有水,沙漠中随风飘散的胡杨花絮,就能生根发芽(《脉脉乡邦·走向胡杨》),“人在天界伟力面前第一位敬畏的就是水”(《上上长江·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这也是他的“地理笔记”三部曲都写水的原因。有绿水才有青山,有青山必见绿水。他要“用尽全部身心”来表达“对水和海的喜爱”,“对祖国每一滴水的热爱”(《天天南海·后记》)。
二是提倡一滴水精神。没有长江源头的一滴水,就没有所有长江里的水;大海是“用天下的每一滴水来汇成不可改变的存在”,“不进入大海,就无法理解一滴水。理解了南海的一滴水,才有可能胸怀祖宗留下的南海”(《天天南海·我有南海四千里》);他想把自己做成“一滴水”,因为“心灵通透了,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反过来,汪洋大海也可以看成是一滴水”。
三是重视山水的文化价值。“人文情深,天地当会浓缩”(《上上长江·人性的山水》)。这浓缩在山水间的记忆就是文化。作者说“一直以来,我用我的写作表达着对失去过去文化的三峡的深深痛惜”,并以山水文学的形式提醒人们,“没有文化就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也就等于没有文化”(《上上长江·一座山,一杯茶》)。文化的“自信与信念”是刘醒龙山水文学的灵魂。四是坚持文学要回到“第一现场”。强调“那些不在现场的文字,与海洋远离十万八千里写海洋的文字,肯定不会有生命力”(《天天南海·后记》),这表明了作者深扎生活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以及对文学反映生活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因为在场,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才能做到“人云我不云,人不云了我才云”(《天天南海·椰风铜鼓老爸茶》),才有文学发现的价值和敢于纠错的底气。
五是传递爱的哲学。爱是贯穿所有作品最浓烈的主题,由爱山水到爱山水养育我的乡邦祖国,由爱绿水青山的大自然到爱人生爱社会。做一个有大爱的人,与大江大海的每一棵树、每一粒沙、每一条鱼、每一滴水成为兄弟。“山水有情处,天地对饮时”。在这幅壮美的大自然画卷里,有抒情主人公顶天立地的大爱形象,召唤读者特别是孩子们一同进入绿水青山的文学家园。
作者说,“天下的孩子都有去课文描写的那些奇异地方看看的想法”(《上上长江·天地初心》),这套“地理笔记”就是孩子们课堂外的“课文”,是当代版的“爱的教育”,也是孩子们行走祖国山水的指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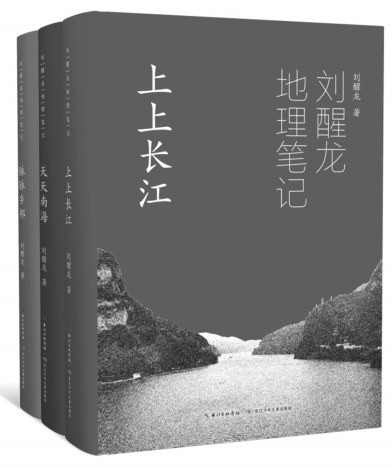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