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名《爱因斯坦陪审团》(Einstein’s Jury: The Race to Test Relativity,2006),考虑到这是作者克雷林斯滕(Jeffrey Crelinsten)在获得博士学位25年之后,对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进行补充修订而成,定下这样的书名,多半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按照美国的情景,出了诉讼,要审案了,会组织陪审团。陪审团静听控辩双方的律师陈述案情并相互诘难,还要不时传唤人证,察看物证。陪审团的任务是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移用到本书书名的比喻中,就是要判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是否为真。
现在当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相对论理论为真(当然仍有极少数人试图推翻相对论),本书作者也没有打算写翻案文章。在这场“庭审”中,作者扮演的角色有时像辩方律师,有时又像旁听庭审的新闻记者,因此作者也陈述了许多“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履行陪审团义务来说可能是冗余信息,但是对于了解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理论来说,对于了解那场持续多年的“庭审”过程来说,仍是有益的。
牛顿为什么不需要陪审团?
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牛顿和他的万有引力理论需要陪审团吗? 答案当然是不需要。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对万有引力理论发起诉讼,更是因为自问世以来,万有引力理论在无数应用中,已经反复证明了它(在适用范围内)的正确性。我们在地球上建造的每一幢房屋、每一座桥梁、每一艘船舰,我们发射的每一颗炮弹、每一枚火箭、每一艘飞船……都在证明万有引力理论的正确,所以人们根本用不着“陪审团”来判断它正确与否。
然而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却需要陪审团,这是为什么呢?
爱因斯坦为什么需要陪审团?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事生非的问题,但对理解本书却很有帮助,也很有启发性。
要论实用价值,相对论根本无法望万有引力理论之项背。正如本书作者在第1章中所说,相对论问世时,“美国人也忽视了它一段时间,但当时大多数物理学家强烈反对它,因为它不实用”——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很难找出相对论的实际使用例证,它只是改变了我们描绘外部世界的图像。
有人将原子弹和核电站当成相对论的实用例证,因为它们符合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E=mc2),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成立的。质能公式确实出现在爱因斯坦1905年的论文中,但引发原子弹设想的是卢瑟福1913年发表的原子模型理论——这个设想最早出现在威尔斯(H. G. Wells)1914年的科幻小说《获得解放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中。虽然原子弹和核电站可以用质能公式解释,但一个事件A发生后可以用理论B来解释,并不意味着事件A就必然是理论B的实际应用(哪怕理论B问世于事件A之前,因为事件A还可以是理论C、理论D……的实际应用),这在逻辑上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因为相对论缺乏实际应用,所以它需要陪审团。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却企图改变世人已经习惯了至少两三百年的外部世界图像,人们当然会对这个理论是否为真产生本能的怀疑,“学术诉讼”就难以避免了。
广义相对论的三大验证
“爱因斯坦陪审团”面临的“案情”,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两个新的天文现象,和一个已知天文现象的新值,这些预言构成了广义相对论的“三大验证”:
1、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新数值。这个天文现象在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中也已得到描述,但牛顿理论的计算值比实际观测值小了许多,所以多年来天文学家们设想过几种路径来解释这个问题。而广义相对论给出的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高度吻合。通常人们认为这个验证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因为此事与岁差有关,而且影响水星近日点进动的因素很多,所以认为此事还需“继续研究”的人也不是没有。
2、引力红移。广义相对论预言:引力场中的辐射源射出的光,对远离引力场的观测者会呈现红移(波长变长)。对白矮星的观测证实了这一点,1960年代在地球上的精确实验也证实了这一预言。
3、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中的时空是所谓平直时空,这种时空完全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时空,和牛顿时空的根本差别,就是引力场对时空的扭曲——只是在引力场比较弱的情形下,这种扭曲并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或被感知。因此广义相对论预言:当远处的恒星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后,它的方向会发生微小的偏折。
要验证这第三个预言,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和麻烦了——《爱因斯坦陪审团》超过一半的篇幅都耗费在此事上了,大批涉及此事的人证被次第传唤到场,还有许多物证也被作者从故纸堆中翻检出来,作为“呈堂证供”。
1919年爱丁顿究竟有没有验证广义相对论有一些进入了教科书的说法,即使被后来的学术研究证明是错了,仍然会继续广泛流传数十年之久。“爱丁顿(A. S. Eddington)1919年观测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就是这样的说法之一。这一说法在国外各种科学史书籍中到处可见,甚至还进入了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中,波普尔(K. R. Popper)在《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一书中,将爱丁顿观测日食验证爱因斯坦预言作为科学理论预言新的事实并得到证实的典型范例。他说此事使他形成了著名的关于“证伪”的理论。爱丁顿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说法,在国内作者的专业书籍和普及作品中更为常见。
这个被广泛采纳的说法,出身当然是非常“高贵”的。例如我们可以找到爱丁顿等三人联名发表在1920年《皇家学会哲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的论文,题为《根据1919年5月29日的日全食观测测定太阳引力场中光线的弯曲》,作者在论文最后的结论部分,明确地、满怀信心地宣称:“索布拉尔和普林西比的探测结果几乎毋庸置疑地表明,光线在太阳附近会发生弯曲,弯曲值符合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要求,而且是由太阳引力场产生的。”事实上,在此之前爱丁顿已经公布了上述结论,在1919年的Nature杂志上连载两期的长文《爱因斯坦关于万有引力的相对论》中已经引用了爱丁顿的观测数据和结论。
之所以要在日食时来验证太阳引力场导致的远处恒星光线偏折,是因为平时在地球上不可能看到太阳视方向周围的恒星,日全食时太阳被月球挡住,这时才能看到太阳视方向周围的恒星。在1919年,要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关于光线偏折的预言,办法只有在日食时进行太阳视方向周围天区的光学照相。
在这样一套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照相、比对、测算过程中,导致最后结果产生误差的因素很多,事后人们发现,爱丁顿1919年观测归来宣布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爱丁顿名头甚大,他自己也以当时英语世界的相对论唯一权威自居。本书作者对爱丁顿并未盲目信从,他甚至认为爱丁顿关于相对论的“早期论述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误导”。本书虽然耗费了过半篇幅讨论爱丁顿1919年日食观测对广义相对论的验证问题,但作者既未明确指出爱丁顿的验证不成立,也未明确担保爱丁顿的验证能够成立。
但是,作者采用“客观中立”的姿态,详细叙述了1919年之后国际天文学界对相对论光线偏折预言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活动,这样的叙述本身就表明了作者的判断——如果国际天文学界认可了爱丁顿1919年的验证,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反反复复不停地验证呢?
在1919年爱丁顿轰动世界的“验证”之后,1922、1929、1936、1947、1952年各次日食时,天文学家都组织了检验恒星光线偏折的观测,各国天文学家公布的结果言人人殊,有的与爱因斯坦的数值相当符合,有的则严重不符。这类观测中最精密的一次是观测1973年6月30日的日全食,得到太阳边缘处恒星光线偏折值为1.66″ ±0.18″。
后来,为了突破光学照相观测的极限,天文学家转而求助于射电天文学手段(观测可见光波段之外的辐射)。1974~1975年间,利用“甚长基线干涉仪”观测了太阳引力场对三个射电源辐射的偏折,终于以误差小于1%的精度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也就是说,直到197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关于恒星光线偏折的预言才最终得到了确证(但本书作者的关注没有覆盖到这个阶段)。
但和1919年那场高调炒作的日食观测相比,后面这一系列工作都很少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是1919年的科学界、公众、媒体,以及爱丁顿本人,共同建构了那个后来进入教科书的神话。
霍金“依赖图像的实在论”
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他始终未能因相对论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以光电效应为理由给了他一个),原因可能与对引力场中光线偏折的最终检验尚未完成有关。缺乏实用价值的相对论,它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是“改变了我们描绘外部世界的图像”。然而对于外部世界图像的这次改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绝大多数人在对爱因斯坦顶礼膜拜的时候,通常是不去思考的。
但是霍金(S. Hawking)可以说是思考过上述问题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有关思考,对于我们评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霍金晚年勤于思考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 他2010年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此书堪称霍金的“学术遗嘱”。该书第三章,霍金从一个金鱼缸开始他的论证:
设想有一个鱼缸,里面的金鱼通过玻璃观察着外部世界,它们中也出现了物理学家,决定发展自己的物理学,它们归纳观察到的现象,建立起一些物理学定律,这些定律能够解释和描述金鱼们通过鱼缸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甚至还能正确预言外部世界的新现象——总之完全符合人类现今对物理学定律的要求。
霍金可以确定的是,金鱼的物理学肯定和人类现今的物理学有很大不同,这当然容易理解,比如金鱼观察到的外部世界至少经过了水和玻璃的折射。但霍金接着问道:这样的“金鱼物理学”可以是正确的吗?
按照从小就由各种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标准答案,这样的“金鱼物理学”当然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与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定律不一致,而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定律则被认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但再往下想一想,我们所谓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只是今天我们对人类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的描述,我们习惯于将这种描述称为“科学事实”,而将所有与我们今天不一致的描述——不管是来自金鱼物理学家还是来自以前的人类物理学家——都判定为“不正确”,却无视我们所采用的描述其实一直在新陈代谢。
所以霍金问道:“我们何以得知我们拥有真正的没被歪曲的实在图像? ……金鱼的实在图像与我们的不同,然而我们能肯定它比我们的更不真实吗?”
这是非常深刻的问题,而且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为什么不能设想人类的生活环境只是一个更大的金鱼缸呢?
在试图为“金鱼物理学”争取和人类物理学的平等地位时,霍金非常智慧地举了托勒密和哥白尼两种不同宇宙模型为例。这两种模型,一个将地球作为宇宙中心,一个将太阳作为宇宙中心,但是它们都能够对当时人们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进行有效的描述,都能够解决“古代世界天文学基本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地点预先推算天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天空的位置(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精度哥白尼体系还不如托勒密体系)。霍金问道:这两个模型哪一个是真实的? 这个问题,和问“金鱼物理学”是否正确,其实是同构的。
尽管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托勒密是错的,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霍金的答案却并非如此。他明确指出:“那不是真的……人们可以利用任一种图像作为宇宙的模型”。霍金接下去举的例子是科幻影片《黑客帝国》(Matrix,1999~2003)——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在这个影片系列中遭到了终极性的颠覆。
霍金最后得出结论: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There is no picture or theo⁃ry-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他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他所认同的是一种“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对此他有非常明确的概述:“一个物理理论和世界图像是一个模型(通常具有数学性质),以及一组将这个模型的元素和观测连接的规则。”霍金特别强调“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在科学上的基础理论意义,他视之为“一个用以解释现代科学的框架”。
霍金这番“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史上的贝克莱主教(George Berkeley)——事实上,霍金很快在下文提到了他的名字,以及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所代表的哲学主张。非常明显,霍金所说的理论、图像或模型,其实就是贝克莱所说的“感知”的工具或途径。霍金以“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的哲学宣言,正式加入了“反实在论”阵营。
这段霍金公案的要点在于:我们今天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并不是终极的——历史上曾有过各种不同的图像,今后也必然还会有新的图像,而且这些图像在哲学意义上是平权的,就好像“金鱼物理学”和人类物理学是平权的一样。
法律事实·科学事实·客观事实
从古希腊的托勒密地心宇宙算起,我们接受过的宇宙图像已经经历了多次改变:哥白尼的、开普勒的、牛顿的、爱因斯坦的……到目前为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宇宙图像,是我们接受的最新一幅。
由于我们相信科学还将继续发展(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所以我们当然无法排除再出现一个新宇宙图像的可能性。至于这个新图像什么时候出现,那是不可知的,也许还要等一百年,也许明天就会出现。
这就直接引导到本书书名的深意了。在司法运作中,陪审团和法官最终判决中所认定的案情被称为“法律事实”。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在很多案情中,绝对的“客观事实”是得不到的。
与此相仿,科学共同体最新认定的那幅宇宙图像(就是爱因斯坦陪审团审议的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宇宙图像),被称为“科学事实”。霍金(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从哲学上来说,绝对的“客观事实”同样是得不到的,我们只能在“依赖模型的实在论”意义上来理解外部世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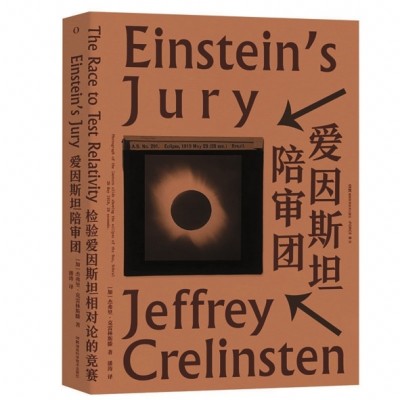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