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我的室内乐作品《广陵之光》在荷兰艺术节演出,我发现担任演奏的德意志室内爱乐 乐 团(Deutscher Kammer-phi⁃harmonie)的双簧管首席格外出色,他的音色透亮、坚韧、清晰而不失内涵。演出之后我到后台祝贺时,看到了这位演奏家罗德里 构 · 布 鲁 门 施 托 克 (Rodrigo Blumenstock)。我 热 情 地 夸 赞他,他特别 高兴。我们谈得投机,双方都表示出合作的意愿,于是乐团经理当场邀请我为乐团写作一首双簧管协奏曲。以这样的方式如此神速地决定一个乐团的委托创作,在我的音乐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罗德里构原籍西班牙,他身上兼有拉丁民族的热情执着和德意志民族一丝不苟的性格特点。为了协助我完成这首作品,他专门来巴黎向我介绍和讲解双簧管特性以及20世纪双簧管演奏技巧的发展与他的绝活,他的现身说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995年7月份我写了《道情》,9月份写作《逝去的时光》。这两部作品几乎是姊妹篇,之所以都有些另类,都那样不顾学院音乐界的规矩,或多或少与这一时期的环境和经历有关。与我同在法国留学的年轻作曲家莫五平于1993年英年早逝,他在最后的作品《凡一》中引用了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的音调,我想以答和的方式,将《三十里铺》作为主要素材用在《道情》中,以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对莫五平的纪念。
当时我住在北京一个小区,朋友帮我借了一架电子琴,我将自己关在小屋里,一工作就是一整天。电子琴不如电钢琴,就是一块板,发出很业余的卡西欧电子玩具的声音。我在这个简陋的工具上设计了《逝去的时光》的和声结构。
写作《逝去的时光》前一年,我联系了马友友,希望他首演这首作品,委托创作的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总裁让·马厄(Jean Maheu)也亲自出面邀请马友友参加,马友友接受了邀请。双方商定于1996年6月在巴黎首演,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乐季册也发布了这个计划。但由于事业途中突然出现的变故,马友友取消了1996年所有的演出,休息一年。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音乐总 监 让 -皮 埃 尔 · 阿 尔 蒙 格(Jean-Pierre Armengaud)询问我,是更换另外一位大提琴家按计划上演,还是等待马友友的下一个档期——1998年春季。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等待马友友。人生苦短,确实有很多事需要只争朝夕,但与只争朝夕同等重要的是最佳时机。在由一位不那么杰出的大提琴家立即首演,还是等待自己钟爱的优秀演奏家首演之间,我选择了最优,而不是最快。而这一等,就是三年! 对于一个心怀憧憬和抱负、急切希望证明自己的作曲家来讲,三年是漫长的。
1998年4月中旬,马友友从美国来到巴黎,住在巴黎一位朋友家里。他性格很是可爱,总是面带微笑,容易交往。但同时,又让人感到礼貌面孔后面适度的距离感。好像微笑只是处世方法,分寸感是明白无误的。
我们私下一起排练了两次。坦白地说,我的涵养比他差得太远。
第一天他给我演奏了一遍,与我所希望的结果相差甚远,“孩子”竟被糟蹋成这样,我心中很是失望,向他一句一句讲解我的原意,并一起逐句过了一遍。排练完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郁闷,怀疑自己的选择和等待,也失望于自己的写作,总之一切变得暗淡无光。夜里,我辗转反侧,像过电影一样回顾着上午排练的场景,越想越坚定,无论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都没有退路,必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迎接第二天的排练。
第二天再见到马友友,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演奏有了明显的变化,心中的希望隐隐生了出来,估计我的脸色也好看了。
第三天是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与马友友第一次合排,马友友带着他的招牌微笑走上台,显得胸有成竹,在排练中俨然成了音乐的灵魂。
第四天,4月23号首演日。上午走台,马友友的表现简直令人惊艳,无论技术还是音乐都让坐在观众席的我跟着他神游,我几近忘记他演奏的是我的作品,像是在欣赏一首很熟悉又完全陌生的杰作。对于经常会在排练时吹毛求疵又自惭形秽的我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晚的首演在香榭丽舍剧院举行。大厅灯火辉煌,法国广播电台总裁让·马厄先生夫妇偕同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夫妇一起出席了音乐会。观众爆满,我的出版商和各方朋友们也无一缺席。
马友友当晚的演奏除了技巧与上午连排同样无懈可击之外,又增加了现场表演的激情和感召力。我坐在观众席,装得若无其事,实际紧张得喘不上气来,苦等了三年的我,要是平静如水就不正常了。这时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些作曲家会在首演现场晕倒,甚至心脏骤停。
曲终,观众疯狂了。我被簇拥着数次上台谢幕,面对观众的起立鼓掌,我激动异常的同时又手足无措,终究是有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以至于慌乱中犯了一个很久都难以原谅自己的错误。我这个大场面的菜鸟,加上平时没有八面玲珑的习惯,在前两次走上舞台时表示感谢的焦点始终集中在马友友身上,而没有注意指挥迪图瓦在另一方向我伸出热情的手。他立即表现出不悦,回到后台后扭头就走,再也不理我。在舞台上谢幕有很多约定俗成,是不能违规的,如何向指挥表示感谢,向独奏表示祝贺,向乐队首席致意,向乐队致意,向观众致意,如何鞠躬,谁先下场,谁在其后,等等,都需要很多经历之后才能游刃有余。
我的手足无措,也被乐队队员看在眼里,当我走到侧幕边,圆号首席过来跟我说,你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在台上显得太谦虚了(être trop modeste)。这句话让我回味良久。我怎么就是伟大的音乐家了? 我太谦虚了吗?
音乐会后,法国音乐版权组织(La SACEM)在剧院大厅为《逝去的时光》首演举办了隆重的鸡尾酒会,出版商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各界朋友和与会者热情的祝贺纷至沓来,让我有点应接不暇。晚上回到家,回想过去飘忽不定的几天的点点滴滴以及来到法国这十几年的各种坎坷与机遇,一夜兴奋难眠。
第二天上午,出版社老板弗朗索瓦·戴尔沃(Francois Dervaux)打来电话,告诉我《世界报》有一篇非常苛刻的乐评。我让他传真给我。
这位乐评人将《逝去的时光》形容成一个“廉价粗俗的冒牌货”。文章没有分析和理论,只是对着一首他不能接受的、与“先锋音乐”格格不入的作品发泄愤慨,同时从字里行间也感受到酸酸的刻薄,对比先锋音乐那小场地、小观众、小乐团,这样一首“垃圾”竟然会引来如此名独奏、名指挥、名乐团,还如此轰动,如此庆典,如此搅动人心(可能对他来说是搅乱人心)。
不过,作为在业内生存的我,昨晚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文章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我感觉被重重地伤害和侮辱了。这是我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让我蒙在那里。一般来讲,拉丁语系国家,诸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乐评远不及英语国家那样活跃,大多数时候媒体对音乐会评论没有兴趣。正因为如此,当有一两篇乐评出现时,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乐评的权威性也更为显眼。以至于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注意到我的专业伙伴、朋友、那些热情支持我的人的态度有微妙的变化。出版商问我:“其钢,是不是应该适当考虑调整一下自己的写作方向?”几乎没有一位朋友站出来跟我说一句支持或温暖的话。这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批判,同学们忽然表现出众叛亲离的冰冷和漠然。
我不能接受文章作者的“政治正确”和高人一等的视角,在他眼里音乐似乎有正确的与错误的、进步的与反动的,就好似苏联时期的某些音乐评论在当下法国的翻版,只不过苏联乐评的假想敌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而法国乐评的假想敌是违背“先锋主义”美学的老朽。身历其中,我感受到法国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自由与民主”,面临的压力虽然不是武力的,但也是官方美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压抑与控制。只有顺从,可以生存,不顺从者,必遭排挤。
一段时间里,我在屋中像困兽一样踱步,反复自问:
为什么我如此用心、如此诚实、如此精心写作,会遭此冷酷嘲讽?
恶毒的攻击与真心的祝贺,孰真孰伪?
为什么法国这个“自由世界”连我这小小作曲家的信马由缰都不能容?
作曲有意义吗?
整整一个多月我彷徨在家,什么都没做,前方变得一片迷茫。
有时我也在安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才十四五岁就遭受众叛亲离的打击,父母亲人均不在身边,那时所面临的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在那个年代,一个“政治生命”宣告死亡的人,无异于“社会性死亡”,前途渺茫。即便那样地残酷,我不也一个人挺过来了吗?相比之下,“美学观念死亡”又算得了什么? 知识分子之间的你是我非,有那么严重吗? 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正在此时,法国广播电台总裁办公室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接受一首新的委托创作,为法国音乐台新创的系列广播节目作一首管弦乐作品。作品必须分为五段,每段两分钟,共十分钟,完成后将在周一至周五每天播出一段,周末时播出全曲,乐曲的文学内容由我决定。我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这个委约在我最沮丧的时候告诫我,道路并非那样狭窄,世界并非那样阴暗,观念并非只有一种,有人始终支持我认同我,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我的追求和水平。
在这种境况下,《五行》诞生了。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写作《五行》,这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呕心沥血之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在压抑之下产生的一部希望之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用这样的歌词来映照我当时的心态一点都不为过。我有一股怒火,有一腔热血向外喷涌。我想尽全部能量表述心中的极致:音色的极致,和声的极致,节奏的极致,织体的极致,配器的极致,结构的极致,细腻的极致,情感的极致。
四个月时间,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踱步、总结、写作、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完全没有说话,只是思考和写作。四个月之后,艾克斯-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大学请我去讲课,到了那里走上讲台,我发现竟然失去讲话的功能,一时失语了。我有点害怕的同时,又有些许兴奋,害怕自己从此失去表达的能力,兴奋自己能够如此专心致志于音乐世界。
《逝去的时光》为我带来思考,《五行》为我开拓更宽的视野。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成为我最为世界所知、最常被演奏也最受欢迎的作品。2018年2月,巴黎爱乐音乐厅为我举行肖像音乐会,由巴黎管弦乐团演奏了《五行》和《逝去的时光》,纪念它们诞辰20周年。20多年过去了,《逝去的时光》早已离开我的呵护,展开自己的翅膀在世界飞翔。
今天,回看当年的消极乐评,我有了更多的坦然和理解,人的认知受限于各种小圈子的标准,我不能苛求。曾经有多少作曲家受到过乐评、权势或观众的不公待遇,但那些振振有词的、不容置疑的、义愤填膺的、“绝对正确”的指责之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历史的沉疴,留下的却是那些“一无是处”的作品。同时,美学的争论,如同作品一样,各有各的追求和爱好,无所谓对错。站在他的立场,不会认同我,我也不会认同他,只要不以指导者自居去排斥异己、打击弱者,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最终不会形成影响。
(本文摘自《悲喜同源:陈其钢自述》,陈其钢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 1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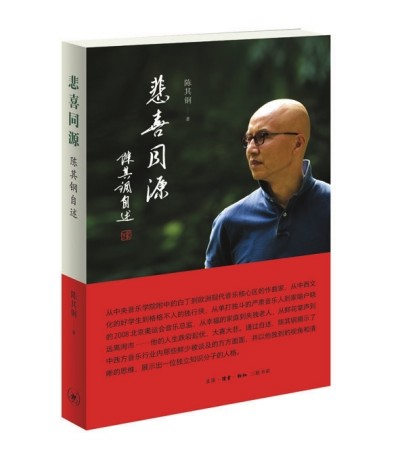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