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淘书、看书、写书、论书、教书,是谓“五书”生活,最扼要地勾勒出我的日常状态。单就看书而言,有几本2023年出版的新书,值得单独拎出来说一说,它们均与人类文明的始源形态及历史阐释学相关。
说到文明的始源形态,自然要高度重视考古学家的看法。近年来,随着这个话题越来越热,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诸多旧书被重新唤醒,生发出新的意义。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书中有两个重要判断,我以为最值得关注。一个是说文明的标志“以文字最为重要”;另一个是说“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两个断语,将整个世界装了进去,内蕴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具体到中国文明,书中同样有两个最值得关注的断语。一个是说:“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这就把中国文明在起源上的基本特征点了出来。所谓古史传说中的反映,我以为《尚书·吕刑》中所谓“苗民弗用灵”应该就是。另一个是说:战国时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这又不免让人联想到鲁迅、闻一多、陈梦家、杨向奎、苏雪林等老辈学者关于楚史与楚辞的相关研判。可以这样说,“巫鬼”正是破解人类早期文明暗码系统的一把钥匙。夏鼐先生讲的是中国,映射的却是全人类。
这样一来,话题便转到了巫师与巫术上来。关于这个话题的相关书籍,着实不少。最新的一种,应该是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主编的《巫术的历史》。这本书不仅从全球视角描述了巫术的来龙去脉,还揭示出许多有趣的人类风俗与禁忌。这些揭示大都可以与人类学家、原始宗教学家乃至哲学家们的论述相印证,当然也可以与中国上古史的情形相参证,因此在有趣的叙事中显影了许多观念世界的母题。
比如“眼睛”,就是上古人类留给我们的一个隐喻性观念暗码。“眼睛”不仅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上古文明遗存当中,而且深深地驻留在人的观念世界。本书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一个习俗信仰就是忌讳“恶眼”。这条禁忌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很普遍。它或视恶眼是一种制造麻烦的因素,或视为凶险的预兆。犹太教的拉比们认为,恶眼相向不仅会导致瘟疫与麻风病,更会导致死亡。所以,既不要以恶眼视人,也要力防恶眼。
这当然是一种观念禁忌,是“眼睛”被社会化之后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虚假功能。尽管是假的,但人们却习惯性地相信是真的。于是,逆着这些虚假功能去探寻眼睛所隐喻的观念本质,人们便找到了哲学的起源。哲学是睁开眼睛的结果,所以笛卡尔说:“没有哲学思维的生活等于闭上双目且永远不想睁开。”人类思想之所以具有统一性,就在于人类拥有同样的眼睛,而且大体在同一个时间段睁开。
当人类开始自觉地观察世界的时候,命名活动便随之而起。本书告诉读者,在古埃及的魔法中,“抹去一个人写下的名字是一种毁灭性的魔法行为,因为如果这个名字不能被说出来,其中的赫卡就会枯竭,此人将会第二次死亡,永不复生”。我们在古埃及以外、比如中国的古书中,不是会读到同样的义蕴吗? 作为魔法师,“除名”是巫师所耍弄的各种鬼把戏中的一种,但是,切不可小瞧这些鬼把戏,因为整个人类正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而且,就在古埃及,法老本人有时即被称为“魔法大师”。古埃及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尝不如此!
但是,鬼把戏终归会破局穿帮,于是专门的思想者兴起,逐步代替巫师,走向了人类文明的中央。据章太炎说,在中国将巫师赶下精神神坛的第一人是老子。换句话说,巫师从精神世界的主流位置退隐之后,人类便进入了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哲学,是相对纯粹意义上的原创哲学。笛卡尔说:“凡对昔日所谓哲学学得愈少者,愈适宜研究哲学。”对轴心时代的思想者来说,所谓“昔日哲学”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少得可怜。因此,在学无可学因而蔽无可蔽的既定状态中,他们得以发挥天马行空一样的想象力,从而创造出人类思想最辉煌的篇章。
那是一种怎样的哲学样态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读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近几年来,这个人连同意大利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一起,成为中国学者走进西方古典世界的两架必经桥梁。通过他们的著作,回过头来,我们会更亲切地认知先秦诸子。比如以师生问答为主的思考方式、不搞体系的著述方式,都让我们感觉中西诸子不谋而合。阿多说:在古代,哲学著作几乎总是回答一些问题,书写情境总是与讲授密切相连。不消说,这会让我们立即想到孔子。
在揭示古典古代精神世界的基本特点时,阿多极其重视阐释学的视角运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重思笛卡尔的名言:“晚近几个世纪以来渴望成为哲学家的人大都盲从亚里士多德,他们往往歪曲其著作的原义,将亚氏纵然复生也不会认为属己的种种观点妄加于他。”多么绝妙的批判与讽刺。但是,哲学阐释上的误解并不减损阐释学的价值,反而突显阐释学立规矩的必要。有了规矩,才能消误解、化歧解而滋正解。
于是,我们需要把目光移向伽达默尔。正是伽达默尔,很思辨地解答了笛卡尔所代表的那种疑问。讲到伽达默尔,中国读者应感谢洪汉鼎先生。几十年来,洪先生一直致力于伽达默尔著作的移译与研究,劳苦功高,成绩卓著。2023年,由他主编的《伽达默尔著作集》出到了第五卷。集中阅读其中的第四卷之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与哲学阐释学相关联,还有一位作为古代思想史家、古典学家的伽达默尔。换言之,还有一位莫米利亚诺、阿多意义上的伽达默尔。
无疑,伽达默尔会论及历史阐释。特别是关于古希腊人是否缺乏历史意识的话题,他从梭伦到访埃及、遭遇历史教训的著名故事说起,表示“这个故事所泄露的东西与缺乏历史感完全是两码事”。如此反主流的观点,不免令我有些诧异。
从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发展态势来说,阐释学的介入无疑在增加。即使在西方,厚厚的《史学理论手册》也算是一部新书。书中说,目前西方史学理论的焦点与范围“更接近于阐释学”。这一断语,也不免令我怦然心动。
能够映射这一动向的例证,可举出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书中明确宣称:“富有意义的历史阐释恰恰是现代历史书写的目的和功能。”从此立意出发,书中讨论历史时间问题、揭示历史主义背后的时间预设、表白康德对历史写作毫无兴趣等等,都值得我们作深长之思。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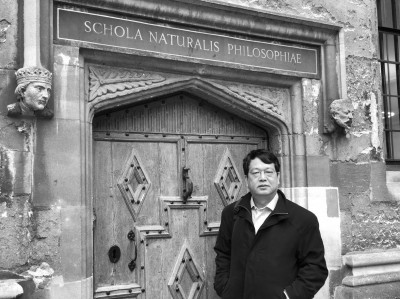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