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是一座蕴含着丰厚思想价值的巨大宝藏,但同时也是一座需要以现代学科工具重新挖掘和整理的掩藏着的宝藏。20世纪之后的中国美学是依据现代学科意识而建立的,从一开始就有着清晰、完整的学科架构。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牢笼天地,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特征,各个学科之间没有相对明晰的边界,全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在一起。学者朱志荣的新著《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必须体现出当代意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第14页),而他这本著作正是在努力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再发现”和现代阐释,力图让这座宝藏蕴含的迷人魅力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在现代人面前。可以说,赋予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以现代学科意识,是这部著作的核心特征,也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
作者将中国古代美学视为一个以意象为中心的潜在体系。他提出,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其整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即为创构意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审美意象构成了审美活动的核心内容,故而中国美学研究也可被视为是一种“意象创构的本体论美学”,应当以审美意象为中心进行分析、阐释和论述。(第201页)
作者在就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和阐释时,一以贯之的是其兼具全球格局和中国立场的研究态度。在美学研究中,朱志荣非常重视中西、古今之间“互相滋养”的互鉴思维。他提出,一方面要“使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中国当代美学学科接轨”,另一方面还需再跨出中国文化的场域,“与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互鉴互释、相互阐发,揭示其中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他强调要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的观念和方法,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入到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以现代理论的特征形态加以呈现”,对之“加以现代化并进而全球化”,最终实现“形成严密的、国际性的话语体系和范畴系统,激活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内在生机”的目标。(第156页)
该著作依据中国传统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对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学理研讨和脉络分析。当代人对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往往在两个极端当中徘徊,一是止步于就事论事的研究,对古代美学的探讨停留在“注释性阐释”的层面上,没超越“跟着说”的局限,二是陷入“六经注我”式的偏颇,脱离古代美学本身客观存在的内在理路及其相关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看似各种“创新”,实则变成一种“自说自话”。故而如何既依循中国传统美学一路发展而来的内在理路,避免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又能立足于当代学科视野,开展创新性阐释且以之构建起具有当代风范的理论,乃是相当考验我们学术智慧的事情。
术语和范畴是方法论研究的基点,作者针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所涉及的具体术语和范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与西方美学术语偏重于抽象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美学术语更具有感性生动的具象特征,是从具体的审美现象中总结和凝练而来,重视审美体验和类比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关注“物我”之间的关系,走的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以意取象的路径。比如“象”(“意象”)、“风骨”“气韵”等,皆来自于主体对自己周边世界存在物的观察与化用,至于更加细化的如“瘦硬”“丰腴”“疏野”“枯淡”等关于审美风格的描述术语,就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与具体可感的审美教育密切相关,包含着一种从感官经验到审美经验再到术语概念的递进式上升过程。作为类概念的范畴,能更具统摄性地指涉审美现象和命题背后的内在规律。有了范畴作为基础,命题就有了依托,再“通过直接陈述或象喻提出美学的判断”,持续衍生出一系列的命题。(第177页)
作者谈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具有“潜在的体系性”,而这种潜在的体系性乃是以相应的哲学范畴体系为基础。虽然由于古代文化的“前学科”特征,这种体系性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实际上它一直以自己的规律表现出来。用作者的话来说,即“有着独特的气质和品格,在它的历史延续性中体现着自身的规律”(第156页)。作者还给出了“艺际交流”的提法,即中国古代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具有互通性,诗、书、画、乐、舞,以及戏曲、园林等门类之间往往会借用对方的术语概念。(第165页)比如“本色”源于绘画而被移用于戏曲,“白描”则源自绘画而被运用到小说评点,这都展现出了中国本土独具韵味的审美思维。让使用者在运用过程中能同时感受到这些术语所蕴含的情景样貌,体会到洋溢于其中的生命意识。
综上,该著作以中西并蓄的开阔视野,在方法论分析框架内,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了富有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细致分析。其秉持着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尊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本身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为我们进一步基于丰厚的中国本土传统去构建当代中国美学贡献了一份力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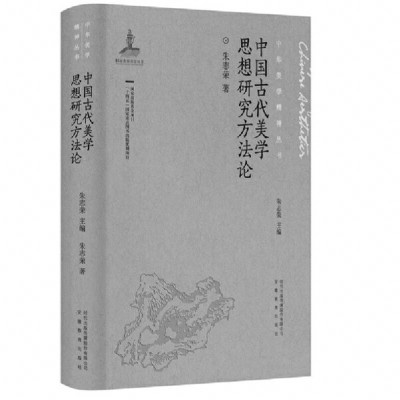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