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点校完稿、正式出版已有一段时间,但我接手之初就有的忐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甚。见到样书的时候,虽有些许激动,更多的还是不安,带着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看的复杂心情,我不断地翻阅,生怕发现问题,却又想找出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处。整个人的状态,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整理第一部佛典之时。
我从事佛教典籍的整理,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足以让人对任何事情放下最初的悸动而以平常心视之。《高僧传》的点校、出版,为何让我又有了自己整理的首部佛典问世时的心态,甚至更甚?仔细想来,原因不外乎三:一是《高僧传》本身影响很大,整理时受到的关注不小;二是已有前辈大家的整理,重新点校压力很大;第三则是“人越活胆儿越小”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高僧传》在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众多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典籍,对这样一部著作的整理点校,自然会引起较多的关注。这对早已习惯于默默“吃瓜”的我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无形的压力。整理古籍首先要有准确的定位,但就《高僧传》而言,受众实在太广,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读者,对整理的总体要求、用字的取舍、校勘记的详略等等,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怎样整理,都不可能出现“一统天下”的本子。众口难调还得调,难度和压力自然很大。整理时,底本的确定、通校本的选择、校勘记的撰写等各个方面,都是反复综合考虑的结果。然而能否最大程度满足读者的需求,我的心中并没有底。
再者,《高僧传》在前辈著名学者已有整理的情况下,我这个无名小卒重新点校,压力倍增。汤用彤先生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接洽华梵,他校注的《高僧传》虽是未竟稿,但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与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种外在条件的变化,《高僧传》虽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但已有的校注本对我带来的那种“影响焦虑”还是颇为强烈。
人们常说,人越活胆儿越小。古籍整理似乎也是如此。记得刚刚开始佛典整理的时候,我总是想着要做出所谓权威性的定本,甚至妄想能取其他诸本而代之。但整理愈多,胆儿愈小。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的奢望。回头想想,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正是当初的我。和硕学大家相比,现在的我仍然还是无知者,但和过去的自己比,多少有所进步,意识到古籍整理的背后其实都是无尽的“深坑”,每一部著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整理者的知识盲区。一些在有的读者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往往会成为埋给整理者的“雷”。因此,在整理《高僧传》时,我内心的忐忑与不安贯穿始终。我知道要彻底消除这种不安,其实并不可能。只有更为审慎地对待整理工作,充分利用E时代的便利,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反复推敲,仔细比勘,尽量融会贯通,综合判定,才是点校过程中减少忐忑的唯一办法。
《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有云:“后晋军出淮泗,陇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之所以如此标点,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淮泗在后赵的南边,陇北在后赵的西边,凡城(今属河北)在后赵的北边。南边的淮泗地区受到东晋的侵逼,西边的陇北受到前凉的侵逼,北边的凡城受到前燕的侵逼,故云“三方告急”。这种理解也有《资治通鉴》等书中的记载可以佐证。此句汤用彤先生点校为:“后晋军出淮泗,陇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其中,“陇比”之“比”为“北”之形误,汤先生在校注中已经指出,而“凡城”则没有加专名线,并未当作地名。有的注译本,标点与汤先生同,把此句翻译为:“后来,晋朝出兵淮水、泗水一带,陇北各城都遭到晋军的侵逼,三方告急,人心惶惶。”由之可见,“三方告急”之“三方”,并没有落到实处。如此标点,恐怕对此句的理解还不够准确。《法苑珠林》卷六一《咒术篇》“感应缘”引《佛图澄传》,周叔迦、苏晋仁先生点校为:“后晋军出淮泗,垄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其中,“瓦城”当为“凡城”之误,但已作为地名而加有专名线,显然有所推进。我在前人标点的基础上,结合《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以淮泗、陇北和凡城为被侵逼的三方,应该更为符合文意。当然,这是一个自认为较成功的例子。
熟悉古籍整理的人知道,校改底本文字,往往要经过反复比勘,要有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我曾经认为,稍有旁证即可加以改动,如今则能不改就尽量不改,有疑处在校勘记中说明。这里举一个例子。卷一一《慧览传》中,底本有“罗浮天宫寺”。此寺名不见他处。作为蜀地的寺名,称之为“罗浮”于理不通,故我根据《高丽藏》《金藏》本改作“罗天宫寺”。这一改动有版本依据,还有《续高僧传》为佐证,《续高僧传》卷六中的释宝渊即为梁益州罗天宫寺僧人。但寺名何以称为“罗天宫”,还是有问题,因为“罗天宫”并不成词,语意不明。“天宫寺”为常见寺名,当时洛阳、江陵等地都有寺名“天宫”者。故我在整理时,怀疑所谓“罗天宫寺”应为“蜀天宫寺”之误,“罗”与“蜀”形近致误耳。称“蜀天宫寺”,就是为了与洛阳之“天宫寺”、江陵之“天宫寺”等相区别故。《释氏六帖》卷一一《静虑调心部》“慧览戒法”条引亦作“蜀天宫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佐证,但毕竟不是直接证据,所以对底本的改动,止步于改“罗浮天宫寺”为“罗天宫寺”,至于应该作“蜀天宫寺”,只是在校勘记中提出。
《高僧传》的整理,主要是在疫情期间进行的。在那段特殊时期,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高僧传》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主要得益于E时代的便利。重要的版本、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通过网络就可以获取。当然,E时代带来的便利,绝非仅限于此。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斗胆作佛教文献的整理,就是因为有数据库资源可以依凭。我读的书不多,如果没有数据库检索,定将寸步难行。但在人人都可以检索的时代,古籍整理中堆砌材料的现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做好材料的取舍,更能体现眼光和功力。这就需要把检索的资料广泛勾连、融会贯通,把相关问题放在更加复杂、广阔的背景多角度观照,切忌断章取义。不仅如此,E时代更需要于不疑之处生疑。这一点,就古籍的点校来说,无论标点还是校勘,无论“校异同”还是“校是非”,都非常重要。比如我把卷五《竺僧朗传》中的“昆仑山”校改为“昆嵛山”,就是融会各种因素之后的综合判定。
如上所述,当初接受《高僧传》点校整理任务时,我就颇为踌躇。这个过程中,也始终充满忐忑。如今出版问世,我并没有如释重负,虽已“堂前拜舅姑”,但内心还满是“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疑虑。毫不夸张地说,点校《高僧传》的前后心态,就是从忐忑走向更加忐忑。现在,唯有期待在读者诸君的帮助下,今后能够不断完善,不断接近自己心中理想的样子、接近读者期待的样子。
古籍整理没有止境,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在历史的长河中,我点校的《高僧传》如果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便利,能够得到部分读者一定程度上认可,我愿足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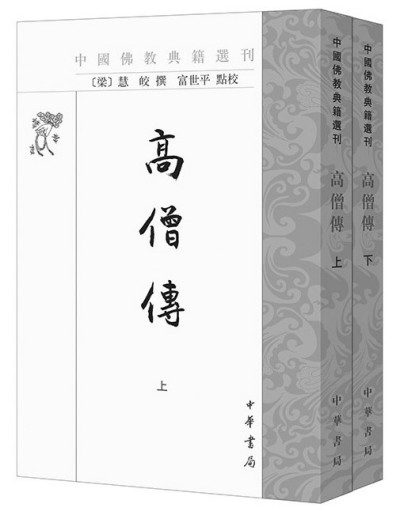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