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本伐
近读王帅新著《读文与读图》一书,其中多有似懂非懂之处,这大概是由于粗略翻检之故;不过即便是细心研读,囿于我现有的认知水平,恐怕也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奥窍。著者曾经就读于我之门下,又曾经与我长期同事,而且20余年来过从甚密,因而他既然有请于我,那我也就只能勉力为文,以表达我的读后之感。
该书读后,自然地引发我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有关图与文的追忆。母亲曾在闲聊中告诉我,我在“抓周”时所抓取者为玩具枪(会发出啪啪声响者),他如铜钱、钢笔、官印、图画书等等均弃之不顾,可见图形、色彩并非我当时的最爱。约略在进幼儿园的年龄,我得到了一件礼物万花筒,其中变换无穷的图案和颜色,骤然像磁石吸引了顽铁般,使我很有一阵爱不释手。那时我并没有进幼儿园,所以图画书接触很少。
至于文字,那是在进小学之前(约摸五六岁),在家中祖辈的督责下开始了识字和写字。对于识字,当时并无兴趣,甚至有点抗拒;然而对于“描红”习字,我倒是相对热衷。现在想来,这抗拒或热衷,也许与有图无图相关吧。即便进了小学,文字的吸引力依旧抵不过踢球、下棋或呼朋引友的玩乐。
对于文字学习的热衷,约略始于小学二三年级时。那时我所就读的武昌阅马场小学离湖北省图书馆(蛇山脚下老馆)甚近,该馆专辟有少儿部,其中出借连环画(小人书),凭《学生手册》,可五人一组借画本10册,由馆方提供小板凳,就地分组阅读,限时归还。记得那时最喜欢看的是西游、三国、水浒和近现代战争题材的画本。为了消灭阅读时生字的“拦路虎”,于是书包中的《新华字典》,便由冷落对象一变而为亲密伴侣。这种对识字的热衷,实缘于故事图画的引发。
记得上初中后便开始埋头于纯文字读本,当然是古今小说之类,甚至包括“三言二拍”。由于多为传阅,借阅时间甚短,以至有一整晚一本书的记录。到了高中,阅读范围开始宽泛起来,对象多为外国名家译本,体裁不仅有小说,还包括传记、回忆录、散文、诗歌,甚至包括哲学入门等。到1966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其后两年的“大批判”中,我所读过者几乎都被盖上了“毒草”的印章。
1968年后的“广阔天地”生活,主要是阅读“天地本原书”和“世间百态书”,不过间或也能暗中传阅《红与黑》等禁书。此期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次由沙洋回汉的夜航船上,我们三五旅伴共读《知识就是力量》月刊合订本。该刊为科普性质,图文并茂,由周恩来题写刊名,创刊于1956年,其中多有苏联优秀科普读物的转载。当我们传阅并热烈讨论所刊载内容时,不意间被某位船员发现,于是叫来一帮人强行收走该书。我们竭力声辩,直至奔向船头向船长索书,然而时间虽耗去二三小时,终究还是抵不过“苏修”二字的罪名。记得事后我向书主说明不能归还的原委时,他竟流露出我有“贪书”之嫌的神情;要不是有三五同行者的证明,那还真可能成为我信誉的污点。
重新热衷于阅读,那是我在1978年开始大学生活之后。当时开放改革的大潮涌起,不仅解禁了大部分书刊,而且还引进、译介了一批外国名著,加之国内作家、学者又有大批新作面世,因此使我的阅读量大增,眼界也大为开阔。尤其当我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后,因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才不得不将阅读的重心转移到专业书籍上来,教育类和历史类书籍便开始不离我的案头了。
就我的阅读经历来看,读图的经历是短暂的,印象是模糊的,在我知识累积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而读文则正好与之相反,尤其在研究高深学术时,若绘图本与纯文本相较,很难说前者便占有优势。至于文本中安插图表和相关老照片的图文结合模式,既是现今的流行,也是我所偏好的;但是否便能依此断定“图胜于文”或“图胜于言”呢? 我依然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从符号的演进历程来看,语言产生的时间最早。最新基因学研究表明,人类在生理上具备说话能力,约略发生在12万至20万年前;若依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的语言系统以衡,当然要晚近得多。图画出现稍晚于语言,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在伊朗中部地区的霍梅恩,一说距今约4万年。不过也有人推断,图画与语言的产生几乎同步,如原始人类随地描画的猎物或狩猎路线图等,只是图形不可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留存下来。至于文字的产生,则更为晚近;最早由苏美尔人所创楔形文字,距今也不超过6000年。依此似可断定,语言和图形只是初级的表意符号,而文字才是相对高级的表意符号。
若就汉字所具备的音(音韵学)、形(小学)、义(训诂学)而言,似可表征上述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历程,即是说文字是语言与图形演进的结果,后胜于前则是历史的必然。文字虽非鲜活、形象,且在很长时间内也只是为小众所掌握;但它就信息传播而言,却是最为经济且相对准确的符号,故国与国之间的盟约、家与家之间的契据,均须“立字为凭”。假如一部史书全用绘画来呈现或诠释的话,即使容量扩增数倍,恐怕也很难求得真切的载录。
诚如著者在本书中所言,现今的童少年乃至青年,无不热衷于读图、晒图甚至“赛图”。手机图像功能的创新,更是满足了这类新潮人群炫酷的需要;加之动漫作品的创作、游戏软件的开发,更是吸引了大批青少年的双眼离开了书本和文字。毋庸讳言,纸质媒介的衰微正如江河日下,电子媒介的兴起宛如旭日东升,在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中,究竟主旨是文主图辅还是图主文辅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依我以自身成长经历和教育的眼光观之,在幼儿园阶段,当然宜纯用图像资料;小学低年级的课外读物,可以是图主文辅,小学高年级则应转为文主图辅;到了中学阶段,无论课内课外,则均应以纯然文字读本为主;假若大学生还沉醉于动漫、镜像或游戏的话,那么其专业成长就不能指望太多了。若就社会大众而言,为消闲而偏爱画面感强、音响丰富电子快餐文化,本为无可厚非之事;然而若想事业有成、思想深邃、涵养厚重的话,那么阅读公认为文字名著,依然应是不二选择。
我赞同著者在本书中表述的基本观点:“‘语·图’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更多情形中,个体求知需要借助二者互释、互补。”可能正是长期对文字的偏爱和畸重,镜像资料才借重科技手段而得以反弹;然而当其张力抵达极限后,文字资料是否也会自然反弹呢? 理智的选择是,为防止某种极端的出现,便应在滑向一端前,便即时加以调适;或者可以这样说,面对当前的镜像热,不宜牵就或再加推助,而应以谨防二者失衡相戒。不知著者以为然否?
本书中介绍了诸多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理论成果。诚如本文开头所言,我并未精研深读,也未曾窥得堂奥,因而难以进行精到置评。不过就我与著者20余年来的交往可知,王帅的学术成长道路快速而成功,不仅已有多部学术专著和成批论文的发表,而且40岁以前便达成了教授、博导的职业追求,称之为“青年才俊”似不为过。尤其当我翻阅过《读文与读图——个体求知的复杂检视》后,更感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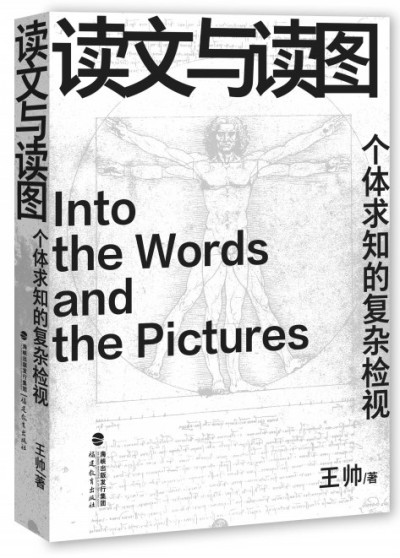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