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廷海
如何从“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视角科学揭示华夏文化以至中国的形成过程,系统阐释在中华大地上呈现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深入揭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基因及其传承脉络,增强文化自信,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王鲁民教授著《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以下简称《塑造中国》)一书,以东亚大陆腹地山河构造为基础,将人类活动遗存主要是设围基址的空间分析与中国古代典籍的历史叙述相互参照,阐述“中国”的辨识与确认、以特定形式为基础的实体“中国”的实现与坚持以及“中国”的再生与转型,揭示了自旧石器时代以至东周以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塑造中国”的历史进程。全书构架宏伟,原创性强,是一部难得的聚焦于国土空间发展与城乡规划历史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一、建构结合实证,自觉而娴熟地运用空间思维展现“中国”的成长
空间认识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遗址是过往人类活动造成的遗存,一定时期考古遗址的空间覆盖范围、关键遗址的分布格局以及遗址分布所呈现出来的组织特征等,都有可能成为了解当时人类空间把握与空间观念的基本线索。这是王鲁民教授进行上古“中国”塑造讨论并取得独到的发现的理论工具。
《塑造中国》的讨论主要涉及东亚大陆腹地及其核心区两个空间层次。东亚大陆腹地大略指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这里海拔多在2000米以下,西高东低。众所周知,“东亚大陆腹地”实际上是中国主要人居地,至今仍以43.71%的国土面积承载着94.39%的人口。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大致指南起钱塘江、北至滦河入海口、东至大海、西至洛阳一带的地面相对平坦的大型区域。这是当今中国最适宜人居的地区,国土规模约占全国的1/5,实际居住人口约占全国的3/5。
《塑造中国》认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东亚大陆腹地,尤其是东亚大陆腹地核心区成为了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的特殊场域,在规模如此宏阔的实体地域中通过遗存的空间分布、设围基址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反映的人群活动,探讨实体“中国”的概念及其在中华大地上浮现、再生与转型的具体历程,在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悠远回响中,追寻先民以特定形式实现以“中国”为核心的秩序塑造和“中国”观念的转型及秩序重整,纵横开阖,波澜壮阔。
二、宏观结合微观,凭借设围基址洞悉族群强弱存亡的总体面貌与细部特征
王鲁民教授具有扎实的营造学根基,对聚落,特别是他所定义的设围基址的结构形态有着独到的见解。《塑造中国》基于系统的考古材料分析,提出上古的那些在使用上受到限制的壕沟和城垣是高规格的、综合性的祭祀权力存在的标识,注意到在东亚大陆腹地及其核心区,此种遗址总是在某几个地方持续地、反复地、成群地出现,而在其他地方则踪迹难觅。所谓持续地出现,是指某一设围遗址在这些地方一经出现,其往往就长达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地存在;所谓反复地出现,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地点总能见到含有壕沟和城垣的遗址;所谓成群地出现,是指在这些地方此类遗址一旦出现,往往就有其他同类遗址近距离相邻地出现,甚至形成规模可观的群体。观察表明,这些地方或是长程河流的入山口或者出山口处,或是这种河道的剧烈转折处,或是与其他河流的交汇处或周边地形突出的地方。古人称这样的地方为“神明之隩”。在主要依托河谷进行交通的上古时代,“神明之隩”是人类实现空间控制的要点,不同的条件造成了“神明之隩”的等级分别。在特定的“神明之隩”见到的设围基址的拥有者,自然是在一定范围的族群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上古时期,设围基址是一个显著的标识,对于一定地区来说,它的存在、规格提升、与之有关的设围基址群的出现和规模壮大,意味着在该地区凌驾性权力的存在、权力地位的提升和相关族群的壮大。反过来,一定地区的设围基址的消失、等级降低、设围基址群的衰落和解体,则意味着该地区凌驾性权力的迁出和衰落,权力地位的下降,甚至是相应族群的败亡。
以此为基础,王鲁民教授指出,“中国”其实就是在东亚大陆腹地诸高规格“神明之隩”中居中的那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神圣性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拥有者所持的祭祀特权或空间控制优势对周边地区的凌驾水平。而“中国”的塑造就是对相应结构及其完整性的揭示与坚持。由于相应结构的“自然”属性,使得它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国土空间观念的依据,并且支持着在十分原始物质条件下的广域权力的形成。
《塑造中国》以设围聚落为凭借,在广域空间中对权力格局特征进行刻画,揭示上古族群强弱存亡的总体面貌与细部特征,将具体而微与面广量大巧妙结合起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新见迭出。
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揭示三代文明的空间构架及早期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属性
对塑造“中国”历程及上古中国空间架构的相对完整和真切的了解,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适当利用。王鲁民教授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提供了大禹以后各王的具体在位时间,对于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记述更为详细,并且每每与考古迹象应和。因而,更多地利用《竹书纪年》并注意其与《史记》等典籍的互补,就成了《塑造中国》得以展开的特点之一。《塑造中国》将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述相互观照,共同支持着全书的展开,结果也简明地体现在书末的三个附表中,即“以《今本竹书纪年》为基础的夏、商、西周年表”“文献所载夏代以前历史事件与空间考古迹象对应举例”“文献记载中的夏、商、西周重要史迹与空间考古迹象对应举例”。这三个附表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文明发展的特别窗口,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全书的核心内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塑造中国》还创造性提出了与中国人居史相关的一系列关键假说。例如,《塑造中国》提出,神圣地点的看守者或许就是最早定居者,这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提出坟墓是西方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观点可以相提并论;《塑造中国》认为,生产剩余和陶器的发明,会降低人们的游动水平,促成更多的定居发生,进而提升人类空间计较的水平;《塑造中国》指出,随着人居由山地走向平原,祭祀场所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相应人群相对强势,设围基址成为旧石器时代的长期使用的特殊遗址的更具公共性的替代,壕沟这种形式一方面使祭祀场所和周边环境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使祭祀场所与特定的山水景观保持着通畅的视觉联系,这种状况应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造成中国人对山水之美特别关切的原由之一。凡此对于相应领域的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长期以来,我倾心于探索中国传统城市及其规划,发现中国古代城市的存在与特征和其所在的地理单元高度相关,与行政体系高度吻合,与交通网络相辅相成,与大国山河相得益彰,共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提供基本的空间支撑,在广域国土空间控制与社会治理中发挥枢纽作用。阅读《塑造中国》,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并领略了一幅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生生不息的壮阔图景。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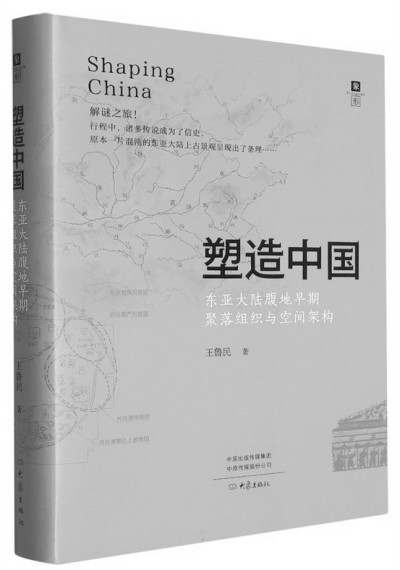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