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秦汉史和“《史记》学”的人而言,位于韩城市南10千米芝川镇南门外、梁山东麓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墓和祠,无疑是一方圣地。司马迁的墓祠,背靠峻拔的山体,俯视雄浑的黄河,满目树木苍翠,尽得天地风水之盛。由山下宽阔的“太史公广场”开始,拾级而上,牌坊、山门、祠门、献殿、寝殿、松柏环绕的墓冢,历历在目;洋溢着敬仰之情的匾额题记,扑面而来:清光绪十二年(1886)“汉太史司马祠”的木牌坊额书,清康熙十年(1677)“高山仰止”的木牌坊额书,祠门之上“太史祠”额书,分外醒目,献殿之前排列有序的历代重修碑记和歌咏碑刻——呈现人望凝聚之重。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前后辉映,人数众多。但是,就墓地规格之高、拜谒者人数之众而言,太史公司马迁独居魁首!
“班马异同”的缘起: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引发的回应
班固曾经从政治立场和维护“汉家正统”的观点出发,对司马迁与《史记》有严厉批评:“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汉书·叙传下》)班固还曾经从学术标准有偏差的角度,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不难看出,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既涉及体例问题,更着重于“思想”与“立场”。有的言辞,相当激烈和尖刻,甚至有“周纳构陷”入人以罪的嫌疑。譬如说,班固指责司马迁将汉王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是在批判司马迁降低了汉王朝的历史地位。平心而论,司马迁写的是“通史”著作,只能以编年为序来安排各个王朝的位置。也就是只能按照“由古而今”的顺序来记叙历史。汉王朝是司马迁面对的王朝体系中最为“晚出”的历史阶段,他把汉王朝的历史安排在秦王朝和楚霸王项羽之后来书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编年纪事而已。而班固却不惜使用带有政治重压的语言,对司马迁展开如此无情的批判,真是令人齿寒与痛惜!司马迁生活在西汉,班固生活在东汉,班固以晚辈的身份如此指责和批判前贤,那么,生活在班固之后的学者,自然就要经过自己的对比和研究来判断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是否可以成立。就此而论,“班马异同”争论的肇始者,就是班固本人。
由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涉及他们两位在历史观和著述宗旨上的诸多不同,因此,“班马异同”之争,延续到了当代,就带有“思想史”研究的鲜明色彩。从而使得这个内涵成为讨论的精华之所在。
“班马异同”的外延:“通史”与“断代史”体例高下之争
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著作”,班固为主要撰著人所完成的《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要分析和比较两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异同”和“优劣”,从史书体例入手展开讨论,自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式。
后世学者,偏偏有推崇“通史体”与褒奖“断代体”的两种学术路数的存在,于是,司马迁和班固所开创的史书体例谁高谁低,也就成了无法取得共识的议题。
宋元之际的史学评论家郑樵,在所著《通志·总序》中,集中阐述了史学的“会通”之义。郑樵力主编写通史,竭力反对断代为书,认为历史犹如长江、黄河延绵不断,如果断代为书将造成“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的状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在评价《史记》《汉书》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尊马抑班、提倡通史而轻视断代史的思想倾向。郑樵指责班固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甚至于说到,如果要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如龙之于猪”。郑樵带着主观偏见来贬抑班固和《汉书》,当然是不公正的。
而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是推重断代史体例的,所以,他对于班固的《汉书》,褒奖有加:“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
平实而论,两种史书体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各有其优点。两种不同的著史体例,都应得到尊重。司马迁以“通史”的视角,把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做了天才的梳理与记述;班固沿用了司马迁的“纪传体”的体例而“断汉一代为史”,推出了第一部“断代史”,后世史家援为楷模,累代继作,遂有“二十四史”的“正史”体系辉煌传世。就此而言,司马迁与班固,于中华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皆有大功。时至今日,如果有谁还试图从“通史体”和“断代史体”的对比来做“班马异同”的讨论,未免不够通达。
“班马异同”的精微:以文字对勘比较撰著能力的高低
这种对比角度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内涵: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记事范围上,有一个“重叠时期”——这就是从西汉高祖开国到汉武帝时代。同样的历史阶段,涉及同样的人物群体、同样的政局演变,《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审视的角度和重点有变化,记事的文字有异同,其中寄寓的史家观点也有差异。对比和玩味其中的差异,岂不是“班马异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自古及今,都有学人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以文字对勘的方式来比较司马迁与班固的异同与高低。值得称许的是:明代学人许相卿完成了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史汉方驾》,将《史记》和《汉书》相同记事的内容,依据文字的异同而排列为一书。具体的“排版方式”是:两书记事文字完全相同的,以大字居中排列,两书文字凡有不同者,则以小字分行夹注的方式左右排列,《史记》的文字居右,《汉书》的文字居左。如此“排版”,把两书的异同,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有“一目了然”的效果。真是难为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书名中的“方驾”,寓意为“并驾齐驱”,表示作者不存主观的褒贬。这是很好的治史态度。
《汉书》写作在后,当然对《史记》的文字有借鉴、有继承、有改写。凡是改写的内容,自然是班固刻意要表达的与司马迁之不同。按照常见惯例,著述应该是后出者转胜,但是,也不尽然。后世的研究者发现,班固所修改的文字,与司马迁的原文相比较,有一部分反而不及原作精彩——当然,这里存在着见仁见智的问题。
以原作的文字对勘,来比较司马迁和班固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异同高低,这是一个多么精微而富有意趣的研究角度!
“班马异同”的讨论,是“《史记》学”的组成部分,历经大约两千年的各抒己见,在历史学界也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这与问题的复杂性相关,也与研究者的立场和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同相关。当然,学界的主流看法,还是客观存在的。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代表性学者徐复观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和笔锋,著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的长文,对《史》《汉》两书的体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较,使人们在全面比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出司马迁、班固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风格。他对两书的文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
史公的文体疏朗跌宕,富于变化,文句的组成较为圆满,篇章的结构线索分明,照应周密;而班氏的文体较为质重简朴,缺少变化,结构的线索不甚分明,文字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史公较精确而能尽量保存历史形象生动的原貌;而班氏渐流于空洞,对人物渐流于抽象化,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
韩国学者朴宰雨有《〈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书,可以视为当代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作。我列出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史》《汉》所显示作者之精神倾向”的目录如下:
一 《史记》变通古今与《汉书》尊显汉室二 《史记》兼尊儒道与《汉书》独崇儒术三 《史记》兼顾民间与《汉书》倾向上层四 《史记》感情移入与《汉书》不失客观这四个“目”,把当代学人“班马异同”研究在思想与审美方面的重点问题,都强调出来了。
学术界对“班马异同”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司马迁与班固的高下对比,也会继续存在,但是,在学术讨论之外,就一般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司马迁的居高之势,却早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站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墓前,目睹墓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盛,这个感觉,油然而生。
我曾经于1982年和2015年两次到访位于扶风县的班固墓。班固,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墓地,就在旷野之地的农田之中,没有任何保护性设施,更不见有何风水优胜可言,也不见后世文人骚客前来凭吊的歌咏碑记,普普通通,宛如一位寻常农夫的归宿之地。特别是回忆起第一次身临其境的情况,如果不是有人解说,我几乎无法相信,沉寂在这里的一抔黄土,居然就是名震士林的班固之墓! 我曾经为班固墓地的荒凉而沮丧,为社会对历史学家的淡忘而不平;而现在,在我第二次拜谒太史公墓祠的时刻,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和班固,同样是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但从墓地的规格高低迥异、人望的多寡悬殊而言,两者对比,不可以同日而语!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何在? 是我当时在勉力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其一,司马迁正直进言而被下狱惨遭“腐刑”的遭遇,容易引发人们的同情之心,由“代鸣不平”发展到敬重和敬仰。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不幸遭遇了“李陵之祸”。天汉三年(前98),勇将李陵出击匈奴,兵败降敌的消息传来,在都城长安立即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在朝廷大臣对李陵一片痛诋的声浪之中,司马迁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推崇他是“奇士”,“有国士之风”,“虽古名将不过也”。
没有想到的是,汉武帝勃然大怒,给司马迁强加上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游说两项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审案的官员,又给他罗织了“诬上”的罪名。结果他惨遭宫刑,对于司马迁而言,除去生理上的阉割剧痛之外,更加难以承受的是心理上的摧残蹂躏。
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想到寄托了自己人生追求的历史巨著草创未就,决意“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著作。“埽除之隶”司马迁把生命的全部活力,都投入到创作之中。发愤著书数年,《史记》是他奔涌的生命、呐喊的灵魂,是他的理念操守、精神寄托。
司马迁直言得罪、惨遭腐刑的经历,借助于他痛切陈词的《报任安书》广为人知。凡是读过这篇私人通信的人,都会对司马迁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这种浓烈的感情,经过积淀和转化,就会成为对司马迁的敬仰。
班固的身世,也有足以令人扼腕叹息之处。他出生于世为官宦的家庭。汉明帝时,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奉命编著国史,“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一百篇。
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大将军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从以上背景来看,班固在官场上的地位,所参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司马迁之上。永元四年(92),窦宪因擅权暴虐致使汉和帝决定诛灭窦氏,班固受其株连而免官。后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享年61岁。班固的结局,就“命丧牢狱”而言,似乎比司马迁还要悲惨。但是,后人对班固的遭遇却没有对司马迁那样的同情。原因在于班固作为窦宪党羽而被处罚,实在是“理所当然”。
其二,司马迁的“民间立场”和批判精神,比起班固的“正统立场”,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敬佩之心。
班固尽管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有所批评,但对《史记》的“实录”精神却是推崇备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论人论史,保持了更多个人的判断,不愿意让历史之学沦为政治的附庸,而且致力于以历史表达对政治的批判。司马迁的这种追求,这种境界,为他赢得了后世的尊重。太史公墓祠所享受的高规格,就是他被后人尊重的物化体现。而班固在过度参与政治的背景之下,他选择的以“历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路径,无法赢得后世的尊重。
站在司马迁墓祠前,目睹司马迁身后殊荣的种种体现,联想班固墓葬沉寂的境况,两相对比,相差悬殊。抚今追昔,深有所得!
(本文摘自《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人文》[增订本],王子今、高从宜、孙家洲、桂维民、张占民著,本文作者孙家洲,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定价:118.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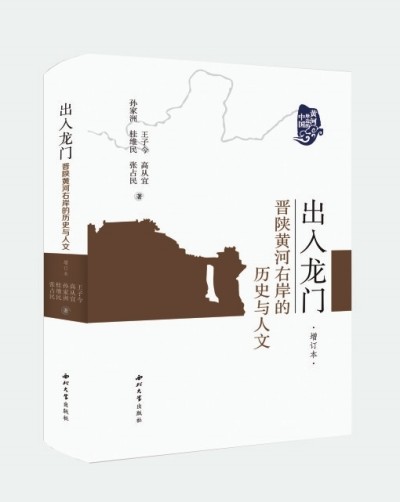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